我国现代美学的三位创导者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政治观点大不相同:王国维是保皇派,辛亥革命之后,还在清室小朝廷里做南书房行走,长期拖着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不肯剪去;蔡元培和鲁迅则是革命派,他们都是光复会会员,从事推翻清室,建立民国的活动。但是,在美学思想上这三位却有一个共同点,即打算通过审美教育来开启民智。从这一点上看,他们都是启蒙主义者。
当然,在具体做法上,也不尽相同。王国维鉴于当时鸦片对于国家之危害,认为鸦片泛滥的最终原因,是“由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在于感情上而已”,所以要禁绝鸦片,根本之道在于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养成国民之知识及道德,尤不可不加意于国民之感情,而引导国民的感情,“则宗教与美术二者是”。他认为,对下流社会,应提倡宗教,对上流社会,则应提倡美术,“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去毒篇》)。而蔡元培则认为美感具有超脱性和普遍性,最易去除人我之见,所以他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说》)。一九一二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时,还把美育列为国民教育五项原则之列,试图利用行政力量在全国推广。虽然他一下台,美育随即从教育方针中被取消,但他出长北京大学时,又在北大建立绘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等,继续推广审美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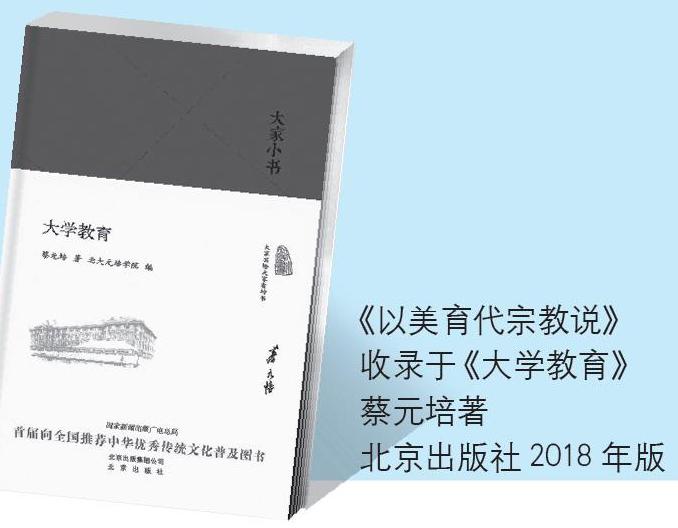
鲁迅弃医从文,就是因为看到国民精神的麻木状态,想通过文艺来改造国人的灵魂,着眼点与王国维、蔡元培一致,其实也是审美教育的一种表述。民国元年,鲁迅应蔡元培之招,到教育部任职,主管图书馆、博物馆、万牲园以及音乐、美术、剧艺等事宜,正是蔡元培审美教育方针的积极支持者与推行者。当他听到美育被取消的消息时,在日记中愤然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1912年7月12日)但他并不因教育方针中删去美育而放弃此项工作,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继续从事审美教育。一九一三年二月,他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除了解释美术之目的与致用外,还提出一整套播布美术的方法,这可视为他推行审美教育的计划书。虽然北洋政府无视于此,这个计划未能推行,但他还在力所能及之处,做了不少美育工作,如考察新剧演出,与陈师曾一起筹办儿童画展等;又凭个人的力量,翻译艺术教育论文、收集研究汉碑拓片、为青年画家展览会目录写序、为画展作评、自己开美术收藏展览会、编印古今中外的版画、提倡新兴木刻等,这些都是审美教育的延续。此外,鲁迅还常在他的杂文中表达美学观点。人们往往只注意其笔锋的尖锐,而忽略其所包含的审美内涵。比如,他在《论照相之类》里讽刺了梅兰芳,引起了“梅粉”们长期的愤慨。其实,鲁迅只不过是借此来批评中国人的某种审美观,即“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而非对着梅兰芳个人。他对梅兰芳艺术的正式评论,则见于《略论梅兰芳及其他》,所论虽然简略,但却点到要害:“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这是从社会史与艺术史的角度,从演员与观众的互动关系,来谈梅兰芳演艺的变化,很深刻,可惜戏剧界并不重视。只有从捧角风气和名伶崇拜心态中走出来,才能领会鲁迅文章的美学价值。鲁迅的许多美学观点,并不以专论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往往隐含在杂文中,与社会批评、文明批评融合在一起,有时并不直接谈美,所以易于为学术界所忽视,如大精神与大艺术、魏晋风度与文章、时代思潮与民族性、静穆与热烈、京派与海派、帮忙与帮闲等,都是重要的美学命题,既贴近生活,又有历史深度,很值得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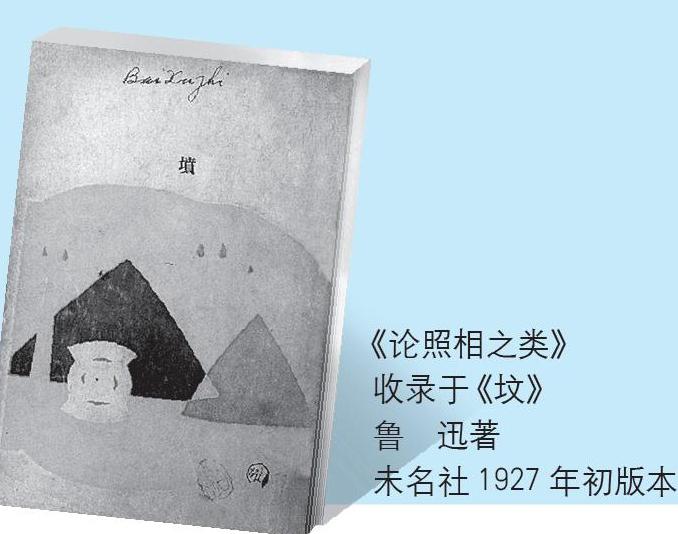
中国这几位现代美学的开拓者,都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显然是受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影响。但他们又都要发挥其“无用之用”,以审美教育来改造国民精神,这看似有些矛盾,其实不然。正如鲁迅在谈到“美术之目的与致用”时说,“沾沾于用,甚嫌执持”,但并不等于美术没有致用的价值,“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何况,德国哲学原本就有很强的现实性,康德这个人看似古板,好像生活在纯思辨的世界里,其实他本身就是個启蒙主义者,他的哲学思想是现实生活的产物,而且对现实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曾引述海因里希·海涅的语意道:“他将康德比作罗伯斯庇尔,警告法国人不要轻视书房里谦卑的哲学家,他在平静和沉默中思考着看来无害的抽象概念,但接着就会像卢梭和康德一样,点燃导致国王人头落地和世界性大动乱的导火索。”(《现实感·哲学与政府压制》)
我国早期美学家这种启蒙性的美育观,为后继的美学家,如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等人所继承。他们也都是抱着启蒙思想来从事美学研究的。朱光潜在《谈美》一书的《开场话》里说:“谈美!这话太突如其来了!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年头,我还有心肝来‘谈风月么?是的,我现在谈美,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紧迫了。朋友,你知道,我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流落在这纷纭扰攘的新时代里面,虽然也出过一番力来领略新时代的思想和情趣,仍然不免抱有许多旧时代的信仰。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宗白华和邓以蛰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宗白华早期曾编过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在他手上,培育出了新诗人郭沫若,他还与郭沫若、田汉合写过《三叶集》,探讨过新艺术问题。在转向美学研究之后,他也总是将艺术问题与人生问题结合起来研究。邓以蛰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为民众的艺术,反对以艺术为消遣,主张艺术与人生发生关系,“鼓励鞭策人的感情”(《艺术家的难关》)。
这样,中国现代美学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这就是它的启蒙精神。

有人针对上面所引的朱光潜《谈美·开场话》中那一段话,认为他只看重艺术性,而忽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所以他的變革办法是用艺术来净化人心和美化人心,这完全是天真的书生之见。这话当然有它的道理,我们不能全靠美育来改革社会,但也不可忽视情感上的潜移默化,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对于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作用。马克思早就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审美不是诉诸理论来说服人,而是通过情感来打动人,同样能产生精神的力量,从而转化成物质的力量。
中国近代革命有三个阶段:器物变革,体制变革,文化变革。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属于器物变革阶段,他们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的确引进了许多西洋的长技以为用。但是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接着而起的是变法运动,这就是体制改革,戊戌变法是其代表,但是维新运动不及百日,就倒在血泊之中。这之后,改革之士就开始思考文化变革问题。中国现代美学的三位开拓者,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考虑到用文学艺术来改造国民精神。大规模的文化改革,则是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之后,还上演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专权等闹剧之后才开始的。可见,从器物改革到体制改革,再到文化改革,是历史的进步。鲁迅甚至说:“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这是基于当时的历史经验才得出来的思想认识,有其深刻性。当然,文化的变革也不可能是孤立的,如果不与体制的变革相结合,也难以生效。
总之,文化的变革,审美教育的启蒙精神,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但是,我们美学中的这种启蒙精神,后来却有所弱化。一九五六年开始的那场美学讨论,对美学研究的推动,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讨论者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本体论上,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的问题是:美在主观?美在客观?美在主客观统一?抑或美在它的社会实践性?而很少触及美的创造和鉴赏的实际问题。这当然有一些不得已的客观原因,但因此却削弱了美学的启蒙性。改革开放之后,重启美学研究,朱光潜马上就注意到美学研究与文艺现状的联系问题,他在为英文版旧作《悲剧心理学》一书的中译本所写的《自序》中,就说:“我一面校阅这部中译本,一面也结合到我国文艺界当前的一些论争,感到这部处女作还不完全是‘明日黄花,无论从正面看,还是从反面看,都还有可和一些文艺界的老问题挂上钩的地方。知我罪我,我都坚信读者群众的雪亮的眼睛。”而李泽厚的文章,更与现实联系得很紧,所以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可是美学界里有些人,却把回避现实文艺问题,当作美学研究的常态。打开国门之后,也是介绍西方理论多,联系我国的审美实际少。在长期闭塞以后,多引进新的美学理论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加以消化,不结合中国的审美现状予以运用,那必然成为脱离实际的空头理论,或者成为望文生义的唬人主义。比如,有人逢会必谈后现代主义,玄而又玄,却说不出后现代主义与我国当代艺术有何关系,因而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这情况,难免使人联想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文艺界的“买空卖空”现象。当时鲁迅曾讽刺道:“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还要由此生出议论来。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坏……等等。”“我想,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三闲集·扁》)
美学研究总是要接触生活实际的,审美教育也应与启蒙精神相联系。我们要从西方美学名词的八卦阵中走出来,要从美学研究的纯理论圈子里走出来,面向生活,面向我们自己的审美实际。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叫作“美是生活”,至今仍值得我们注意。美学如果离开生活实际,失去了启蒙性,也就谈不上审美教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