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独立于长篇、中篇、短篇之外,应该说,是靠了许多人的实践与努力。如果把这个阶段看作是“文体的自觉”的话,那么,微型小说现在面对的则是“文学的自觉”。我们看到,微型小说作家一方面尽可能差异化,做到“同中有异”,另一方面却又最大限度地标志化,实现“我中无你”。安谅即为其中之一。
读懂安谅的微型小说,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然而,要给其准确定位,却又没那么容易。我看到的一些议论要么失之于宽,要么失之于浅。故此,我想冒个险,拿安谅的创作,与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做个比较。也许并不十分妥当,但这样或可更加接近安谅的创作初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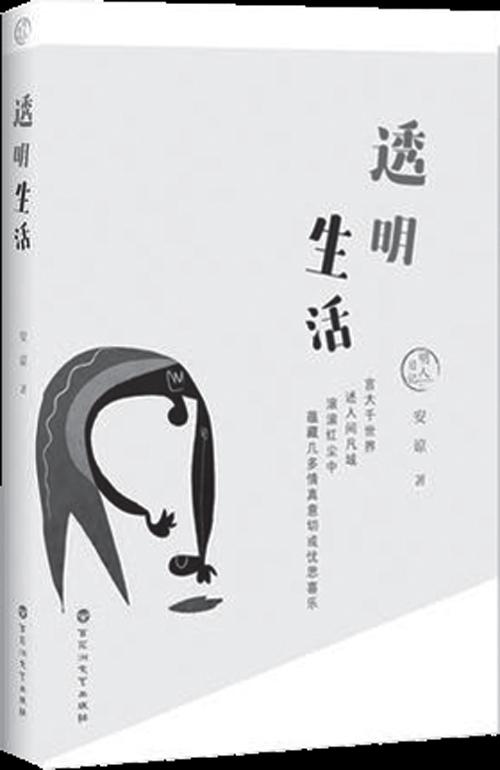 《明人日记:透明生活》 安 谅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 年版
《明人日记:透明生活》 安 谅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 年版这里我想从“共在”“此在”与“我在”三个方面加以述说。显而易见,共在、此在与我在,这三个概念都来自海德格尔哲学。然而,我所谈的是文学而不是哲学,故用意有所不同。所谓共在,是指他人与我共存于世的能力和方式,换言之,即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在共在中体现了共性。冯骥才笔下的周围世界,是“码头”天津卫,而安谅所构筑的,则是“魔都”上海。一南一北,两者都浸染了浓郁的区域文化的色彩。冯骥才说天津“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呆着。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手上有绝活,技压众人,艺压群芳,是俗世中的“奇人”。而上海滩文化却不一样,更多表现为俗世中的“常人”。常人生于斯长于斯,靠的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种“共在”,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体现的是“操心”的“本真能在”。安谅讲了一个故事,说某自助旅行团去欧洲旅游,有个团友购物时不慎丢了双肩包,包里不但有笔巨款,更要命的是还有大伙的护照。情急之下他们找售货员报案,可售货员却爱答不理的。这时,团里的一位小老头只用一招,售货员就立马叫来一伙警察(《摇纸扇的小老头》)。上海人的世俗“精明”放之四海而皆准。
那么,何谓“此在”?需说明的是,“此在”指的是此时此刻的存在,意同“现在”。安谅创作的小说与冯骥才的一样,实际上都有较强的传统时间观念,即仍以“现在”为核心。《俗世奇人》讲述的是过去的“天津卫”,着力点似乎是在“曾在”,然而着眼点却仍是“现在”,是久违了的“现在”。安谅笔下的“明人日记”,也是“曾在”,是消逝不久的“现在”。不同的是,冯骥才的时间观体现为“历史性”,安谅的体现为“历史”。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冯骥才之笔乃像“史记”,而安谅之笔,则更接近于“起居注”。冯骥才为天津卫画像,所取的是天津人的“意志力”。安谅采取的是物质主义,是用细节、色彩、情调来点化上海人的“精气神”。冯骥才想用小说“唤醒”天津文化,而安谅想用小说“呼应”上海文化。是故,冯骥才用的是“回忆”。汪曾祺说:“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而安谅用的是“日记”。回忆的内容由于“除净火气”,似乎更加纯粹,但理想的、浪漫的成分显然更重。日记的内容由于还有“烟火气”,所记录的却更加忠实。安谅用了上海人的“巧思”:一者,形式上的赋能。他把自己的创作归之于“明人日记”,逐日所记、所录,既有深亦有浅;有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但整体上体现的却是“一种本真能在的此在式的见证”。二者,审美境界即寓于平实、平淡、平凡、偶然性之中。虽说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细察之,却也禅意盎然。
安谅小说的一个“显在”,就是“我在”。我在故我思。对于“流俗时间”发生的事,“我”还是有所选择的。所谓“明人日记”,形式上用的是“第三人称”,事实上却是“第一人称”。这与冯骥才的小说不一样,他的视角,基本上都是用“第三人称”。
“第一人称”的第一好处,就是“代入感”比较强,读者会不知不觉地参与作品的索隐与创制之中,比如根据相关作品提供的“大数据”,似可给“明人”画像:明人的身份—机关干部(《你是我的原型》),业余爱好—写诗(《近处的风景》《也许只见一面》),喜欢晚上快走(《步道》),住在浦东某个方位(《你所不知道的故事结局》),等等。至于是否对得上号,则不必深究。
其次,可以自由游走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有时候作者故意设置的叙述圈套,读者却仍然误以为这是非虚构作品。《你所不知道的故事结局》讲的是晚上快走时听来的故事。说有个医药大王,与结发妻子共同打拼事业,公司成功上市后,他却移情别恋,娶了女秘书。几年后这个医药大王猝死,女秘书带着家产嫁与司机。不料司机却甩了她。再后来,司机又结婚了,新娘是谁呢?故事没有结局,却留下一段悬念。我们似乎不必纠结于这则作品是新闻还是故事,抑或部分真實还是全部杜撰,单从叙述学去分析,就很值得玩味:什么是该听到的,什么是不该听到的;什么是想知道的,什么是不想知道的……“在场”与“不在场”,是那么不和谐地,和谐地交织在一起。
“我在”还有一个隐性功能,即我的内心世界,可以毫无保留地呈现给读者。而读者也会想当然地认定,这些呈现是真实的、自然的流露。当然,这个限知视角,也让“我”无法进入“他者”的心灵世界。
概言之,安谅是通过自己的视角,文学性地给我们讲述、展示、呈现今日之上海或当代上海人的故事。
如果说,“共在”“此在”与“我在”给定了微型小说的三个坐标系,那么,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安谅通过自己的作品标识了一个有价值的审美星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