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去年张静蔚先生交给我的《晚清音乐图像—〈点石斋画报〉及其他画报》打印稿竟成为他的遗著,而我承命撰写的序言也变成了对他的怀念,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
张静蔚先生是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教授,曾做过该系的系主任。我和他的交往恰如电光石火,倏忽而逝,但瞬间的照亮已足够我铭记。
通常说来,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和张先生的音乐学相距很远,似不会发生交集。这应当也是我与他很晚才结识的缘故吧。不过,我很早就知道张静蔚先生的大名,因为我对晚清文化研究的兴趣,也包括了现代音乐教育的发生。由此,张先生编选的《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也早就站立在我的书架上。
直到二○○七年春,我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参加“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妇女期刊、新女性与文类重构”会议,撰写论文《晚清女报中的乐歌》时,才真正仔细阅读了这本资料集。当时虽不清楚其编纂过程,但看到其中一些选文的出处,注明所用书刊藏于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以及天津、南京甚至无锡等地方图书馆,已十分佩服编者的眼光独到与搜集广博,其间所包含的艰辛也可想而知。实际上,至今为止,此书仍是中外学界研究近代中国音乐史必备的权威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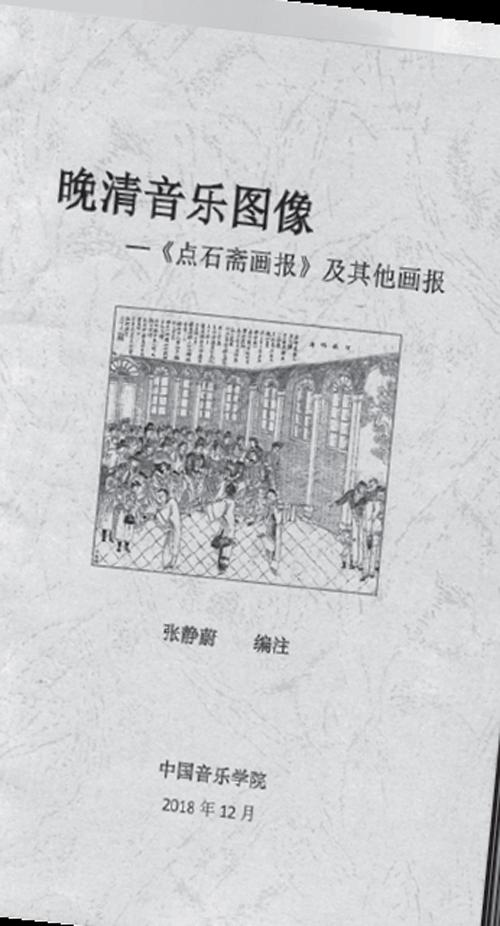 张静蔚遗著《晚清音乐图像》打印本
张静蔚遗著《晚清音乐图像》打印本虽然没有从张先生那里得到亲口证实,我还是可以推测,《晚清女报中的乐歌》才是我与他结缘的真正纽带,因为他指导的学生肖明曾经来我的课堂听讲,并就近代鼓吹女权思想的乐歌论题写信请教。而在我那篇长达五六万字的论文中,除了钱仁康教授的《学堂乐歌考源》,其中引用最多的就是张静蔚先生所编二书,即《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与《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当时为了方便使用,我还专门复印了后书中的附录《学堂乐歌曲目索引》。也就是说,正是依靠张先生多年辛苦搜集的史料,我才能够顺利完成这篇跨学科的长文。
 張静蔚先生讲座
張静蔚先生讲座我的学生李静,博士论文做的是《乐歌中国—近代音乐文化与社会转型》,和张静蔚先生的研究领域贴合,故而比我更早与张先生见面。二○一六年六月,我从北大退休时,李静和她参加的北大校友合唱团同人前来助兴,一起演唱了十首全部采自近代歌集的《学堂乐歌组曲》。视频上传网络与微信后,大获称赞。深受鼓舞的李静于是再接再厉,三个月后的九月二十四日,校友合唱团又在北大图书馆南配殿组织了一场名为“‘学堂乐歌中的少年中国北大讲·唱会”的演出,张静蔚先生也应邀参加。正是在这次活动现场,我与张先生第一次会面。我跟着李静,称呼他“张老师”,他则始终客气地称我为“夏教授”。
虽然是初次相见,但我完全没有陌生感。这固然出于我对张先生著作的熟悉,却也和他待人接物的风格有关。讲唱结束后,张先生和我都发表了感言。不必说,他的评点很专业,不过其间也引发了一件趣事。张先生在发言中提到,他编了一本《学堂乐歌三百首》,是目前收集数量最多的近现代歌曲集。等出版后,他愿意送给在场的听众每人一本。一边说,他还一边举起了带来的稿本。于是,散场后,有一位老人家一直坐着不走,原来她在等张先生送书呢。遗憾的是,这本张先生十分看重的乐歌集最终未能出版,可以预期的小众销量让出版社下不了印制的决心,学界也因此无法享用张先生精心烹制的又一道大餐。
由于事先已得到李静的通报,那天我给张先生带去了新出拙著《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其中收入了《晚清女报中的乐歌》,张先生显然是最合适的指正者。张先生则送给我很重的礼,居然是两瓶茅台。晚上我们去北大中关园的和园餐厅吃饭,本以为张先生要开怀畅饮了,不料他开车来,不喝酒。于是,打开的一瓶茅台和一瓶红葡萄酒,我成了唯一主力。张先生很有兴致地看着我喝,自己只略吃了几口菜,就由学生陪同退席了。
初次见面,张先生的豪爽已留给我深刻印象。同时记住的还有他修长挺拔的身材、修剪得体的银发和优雅清癯的面容。加了微信后,发现他用的网名是大卫,头像是一幅侧面的黑色剪影,惟妙惟肖地传写出张先生轮廓分明的脸型。加之日后聊天,我说起资中筠先生的《有琴一张》(北京出版社2017年),里面收录了她一九八二年访美后,与少年时代在天津学琴时的老师的一张合影,张先生于是随口提到,那也是他的老师。我才可以确认,张先生早年家境应该相当优裕。
尽管此琴非彼琴,但传统文人理想的文化修养—琴棋书画,别的不清楚,起码“琴”之外,张静蔚先生还能“书”。二○一八年八月聚餐时,张先生送过我一幅“丁酉岁末”书写的苏轼《水调歌头》,其所用草书与苏轼词作的旷达适相匹配。整幅字墨酣笔健,一气呵成,甚为精彩。实际上,当日张先生带来了两幅书迹让我挑选,记得另一幅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应该都是他的法书得意之作。我选择中秋词的理由是,“喜欢‘但愿人长久的意思”。只是,张先生并没有如我所愿长生久视,思之黯然。
算起来,我和张先生在“讲·唱会”后见过三次面,吃过两顿饭。见面都是为了《晚清音乐图像》这本书。第一次是二○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张先生送给我四月印出的此书初稿,只有选图和抄录的配文,尚未加解说,《前言》也仅列出提纲。第二次是同年的八月二十七日,我把修订过的初稿本还给他。第三次已在二○一九年,因我三月底要去哈佛大学两个多月,张先生急于将已经写好《前言》、加了注解的二○一八年十二月印本交给我,所以,二月二十八日上午特意开车过来,在我们小区后门外的马路边进行了交接。当时绝对没有想到,潇洒地坐在驾驶座上的张老师,竟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像。
两次吃饭的地点都是在中国音乐学院附近的万龙洲海鲜大酒楼。此处我早前也去过,没觉得有何特别。但与张先生一起进餐时,被他考问,哪道菜最喜欢,方仔细品味。果然发觉葱姜炒肉蟹肉质细嫩,味道醇厚,难怪被张先生评为第一。而且,这家店也被张先生认作京城中他吃过的海鲜做得最好的一家。后来我曾提出在别处、比如我家附近的上地做东,张先生一律不看好,可见其口味之高。张先生其实也善饮,先是由他置备了茅台,第二次我带去了五粮液。有酒助兴,两次我们都聊得很尽兴。
张先生出生在一九三八年,我见到他时,他已七十八岁(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他说话、行事仍然非常率真,绝没有那个年龄段的人常有的世故。他第一次约我吃饭所送的本书初稿,其中除了《点石斋画报》,还从其他晚清画报中选录了若干图像。他坦诚地告诉我,后者基本都出自陈平原的著作《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东方出版社2014年),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授权,允许他在书中挪用,并且反复说过多次。这自然不成问题,只是因出版尚未提上日程,授权书的交付才一再顺延。并且,在此次面谈前,性急的张先生已直接与东方出版社的编辑联系版权事宜。编辑不知张先生的来历,要他直接找我们商量,反倒促进了我和张先生更深入的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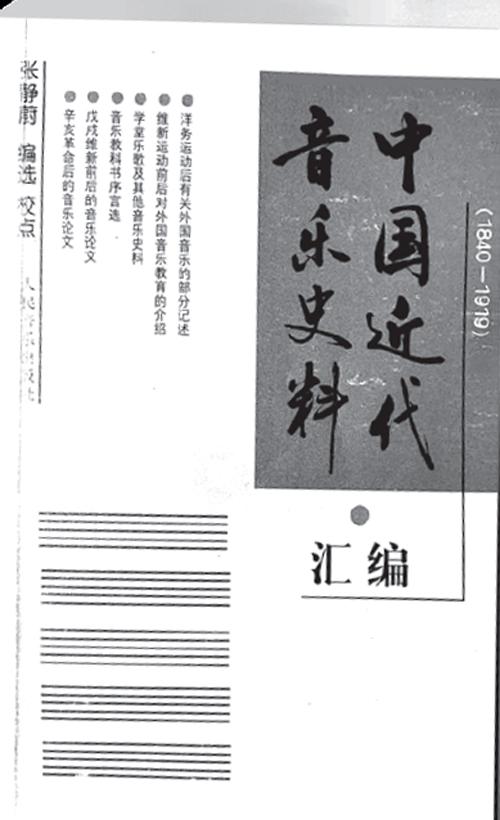 《中國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张静蔚编选校点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年版
《中國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张静蔚编选校点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年版从这件事,我还窥见了张静蔚先生对史料极为尊重的态度。本来,晚清的出版物已没有版权,其他学者使用我们书中的图像资料时,也很少有人会注明。但张先生不同,他把研究者所用的史料与其个人论述同等看待,认为都应当受到版权保护,才会如此惦念不已。这除了显示出张先生做事的认真执着,显然也与其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音乐史料的收集整理密切相关。
毋庸置疑,成名作《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奠定了张静蔚先生在中国音乐史学界的牢固地位,但行内人更为感激的还是此书的前身—由张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亲自抄写、编印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研究资料》(后题作《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三册。在那个专业教材匮乏的年代,这套分为“近代部分音乐史料和论文汇编”(1983)与“五四以来音乐论文选辑”上、下册(1989)的油印本,曾经在全国的音乐史教学与研究中产生过深远影响。
一举成名也使张静蔚先生确定了此后的研究路向,中国近代音乐史料以此成为他念兹在兹、努力不息的终身事业。退休之后,他又积十年功力,编成了《〈良友〉画报图说乐·人·事》与《〈北洋画报〉图说乐·人·事》二书,二○一八年二月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刊行,同年六月第一次聚餐时,张先生即以之相赠。当时曾请张先生签名,但他谦逊推辞,我也没有坚持,因此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
张静蔚先生编注的图说《良友》与《北洋画报》乐、人、事的两本大作,出版时纳入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图像史”丛书。依据丛书主编洛秦在序言中所说,正是张先生的率先成稿,才让这套丛书的出版得以成行。由此可以肯定,眼下这本《晚清音乐图像—〈点石斋画报〉及其他画报》,应是同一思路的赓续之作。而将近代音乐文献的范围从文字扩及图像,确属别具慧眼的突破。我更在意的是张先生借此实现了史料学上的衰年变法,显示了其学术生命力的旺盛。
实在说来,与先行出版的二书相比,《晚清音乐图像》的编注难度要大得多。先说编。一八八四年五月面世、一八九八年停办的《点石斋画报》,由于创刊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最频繁的上海,随处可见的传统社会生活与此地独有的十里洋场风光,均在画家精细的摹写下得到充分展现。张静蔚先生从中精选出一百二十一幅图像,以之构成本书主体,确足以反映晚清音乐文化的变迁。而此画报较早得到学界的集中关注,目前已有多种全套重印本可用。张先生采用的大可堂本(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实为其中最易得到并最好使用的一种。尽管具有如此优势,《点石斋画报》之外的“其他画报”却也不可忽视。应当承认,较之《点石斋画报》,其他晚清画报的资料更难搜集,以之要求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学者显然不合适,因而,张先生的借力陈平原著作本情有可原。何况,在我的建议下,张先生也检视了我提供的全部《图画日报》(1909年创刊),补充了可用图版。凡此,都体现了张先生为充实本书内容做出了最大努力。
至于注解,一九二六年先后创办于上海的《良友》与天津的《北洋画报》,已是使用照相图版的现代画刊,乐人与乐团的活动都更频繁,文字说明也简洁明确,因此,两书的注释与评点相对做起来容易些。而晚清画报中的图像则正如张先生所说,“大都是作为新闻而刊发的”(本书《前言》),此编虽尽力将其分为民俗活动、民歌、民乐、说唱、戏曲、中外音乐交流、教育与新闻等八类,其间纯粹关于音乐的记述仍是少之又少,解说的难度大为提升。加以学界对晚清社会生活与文化,尤其是近代音乐流衍的研究还很粗疏,现成的成果远不敷采用,可以想象,张先生在作注时之举步维艰。但他还是成功突围,将目光集中在重要事件、人物以及他最擅长的音乐演出细节的疏解上。配合图像局部的特意放大,两相呼应,晚清的乐曲、乐人、乐事也得以从纷杂的民俗或时事背景中凸显出来,获得应有的关注。
当然,若以更高的标准来衡量,注解的部分确实还可以做得更细。比如关于西洋乐器的传入、乐队的组建与构成,特别是图画中出现的演出及演奏者情况的介绍等,都可以做文章,也多少都有迹可循。但这些大抵需要从原始资料的爬梳做起,对于已经年迈的张先生,确实不合适提出这样的要求。现在回想,张先生本来可能对我有所期待;或者说,我在这方面本来可以有所贡献。由于我修改过尚未加注的本书初稿,当时,我把那些录自大可堂本的《点石斋画报》图释文字当成了张静蔚先生自己所写,随手订正了若干误字,张先生不以为忤,反而因此一再要我就后来的加注本提出意见。我却未能做到,只是笼统地在微信回应道:“我看了一部分,觉得解说还是应该更凸显您的专业特长。”(2019年11月5日)确实有负张先生的厚望。
不过,当日震惊于张静蔚先生的遽尔病逝,我曾在其微信页面给他夫人孟凡虹老师留言,表示“一定会完成张老师的遗愿”(2020年9月10日),这既指向作序,也包含令遗著以更好的方式出版。在发现书稿中《点石斋画报》的释文全部取自大可堂版后,我以为不妥。尽管张先生认为,此本已将原先的文言文“全部翻译为现代汉语,免去了阅读古文的繁难”(《前言》),我却觉得作为史料,还是应当保留历史原貌。当然,大可堂的改编也有版权,张先生可能忽略了,以为其文字和图像一样,均已进入公共领域。为避免上述种种问题,我与编辑商量后,重新整理、录入了本书所选全部《点石斋画报》图像中的文字,添加了标点。这虽然属于我的自作主张,但相信张先生也会理解和赞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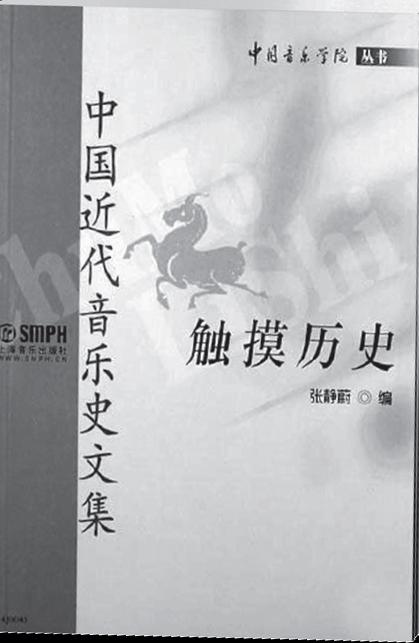 《触摸历史—中国近代音乐史文集》张静蔚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 年版
《触摸历史—中国近代音乐史文集》张静蔚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 年版尽管上文更多表彰了张静蔚先生在中国近代音乐史料发掘与整理上的贡献,我当然也清楚,以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闻名的张先生,其学术成果早已嘉惠学林。从硕士论文《论学堂乐歌》(1981)开始,张先生的名作如《近代中国音乐思潮》(1985)、《马思聪年谱》(2004)、《音乐家李树化》(2004)等,在学界均有导夫先路之功。其论文亦结集出版过,《触摸历史—中国近代音乐史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在学科内享有盛誉。而同样明显的是,张先生的研究厚重、扎實,具有突破力,乃是得益于以坚实的史料为根基。因而,傅斯年那句著名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说法,用在张先生身上正是十分恰切。
我与张静蔚先生交往时日虽短,仍能充分体会其为性情中人,且具有丰富的生活情趣,令人相处愉快。在音乐和书法之外,张先生还热衷于看球赛。二○一八年夏“世界杯”期间,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复发,不能站和坐,仍每日卧看比赛。张先生也爱好旅游。二○二○年七月底,我随陈平原到平谷度假,在朋友圈发酒店周边的照片。张先生看到后,曾两次留言,指点我:“如果时间允许,从湖的北路乘长途车,可到黄崖关长城一游,被称为野长城,即未修缮过的。可以爬一段,也可住下。”“还可以坐长途车再行几公里,可到盘山一游,非常好。乾隆爷说过,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不过估计你们没时间了!”发送时间是八月二日下午四点多。我当晚写微信回复,却自此再未得到张先生的音讯。九月十日在李静的朋友圈,意外地获悉张静蔚先生已于一周前故去,那两段写在朋友圈的话,也就成为他给我的遗言了。
张先生走得还是那么潇洒。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晚清音乐图像—〈点石斋画报〉及其他画报》,张静蔚著,将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本文系为该书所写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