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
乍见翻疑梦,相悲各問年。
孤灯寒照雨,深竹暗浮烟。
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
—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朋友相处,是社会生活的一大内容,是人际生活的重要方面。当然,古今不同,形态各异,但是,重视作为“五伦”之一的友情,一直是我国的精神传统。在我国古代的诗坛上,抒发友情,也一直是热门的创作题材。
古代诗人之所以重视抒写友情,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许多人要谋取出路,势必离乡别井,一人在外,四海飘零,孤独感油然而生,于是,朋友间相互支持,相濡以沫,便成为人生的一大慰藉。加上际遇的穷通,人情的冷暖,只有同在溷藩中打滚的朋友,才最能相互理解。因此,友情是孤寂人生中的甘露,是在人海载沉载浮中可以歇脚的港湾,是在郁闷压抑的氛围中可以透气的窗口。当我们明白友情对于人生的意义,就可以知道我国古代诗坛出现了大量抒写友情诗歌的缘由。
司空曙生活在公元七二○年到七九○年间,和许多大历年间的诗人一样,他在少年时代看到了盛唐繁荣的岁月;刚进入青年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又从此经历社会大混乱、经济大衰退的中唐阶段。司空曙的生涯,主要在这时代的转折点中度过,他和许多诗人一样,惊悚、失落、苦闷、彷徨,乃至于只寻求个人的解脱,抚慰内心的矛盾,于是,创作的题材往往比较狭窄,更多是热衷于描写个人的境遇。也因此,感情真挚,深婉雅淡,形成了所谓的“大历诗风”。司空曙正是“大历十才子”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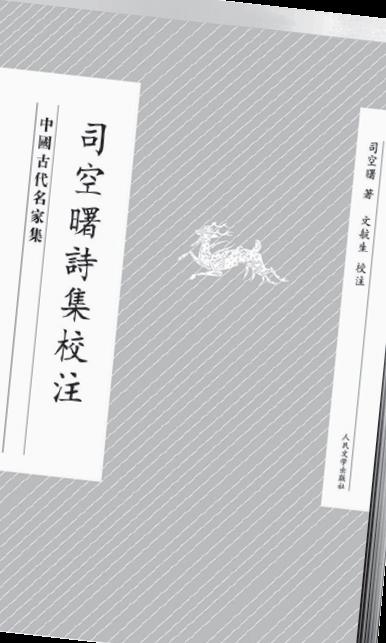 《司空曙诗集校注》文航生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
《司空曙诗集校注》文航生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关于司空曙的生平,我们知道得不多。他为躲避中原的兵荒马乱,从家乡广平流落到江浙一带,居住了颇长一段时间。中年后考试登第,到各地做过官吏,又往往因得罪权贵,常遭贬斥,东奔西跑。《唐才子传》说他“磊落有奇才”,“性耿介,不干权要,家无甔石,晏如也”。看来,他饱历沧桑,感情丰富,常遭逆境却最终能淡然处之,发为诗歌,便显现为情思纠结复杂,而又能以流畅平淡的语言表现出来的独特风格。
有意思的是,在现存司空曙一百七十多首的作品中,以送别亲友为题材的诗,数量竟占近三分之一。这也反映了在动乱时期,文人士子到处奔波,生活很不安定的现实,许多人不得不“却认他乡是故乡”,为了生活频繁地奔走。纵观司空曙写友情的诗作,多数是写别离的题材,也多写得情真意切。可以说,抒发友情,是司空曙平生创作的重点,其中《云阳馆与韩绅宿别》,则是他写得最好,也是最被后人传诵的一首。
司空曙的好友韩绅,有些版本作韩绅卿,据说是韩愈的叔父,曾任泾阳县令。泾阳今属陕西省,云阳是泾阳县中部的小地方;云阳馆,应是这小地方的一处驿馆。本来,司空曙更多的时候在江南一带生活,但也有机会前往当时的首都长安。像三十九岁时,他得悉将被贬到江陵任县丞后,便上长安,登秦岭,写了一首《登秦岭》诗,说“南登秦岭头,回首始堪忧”。泾阳,在八百里秦川的范围里,离长安较近。不知是什么原因,司空曙也到了泾阳,而且在泾阳辖下的云阳“招待所”里,偶遇了韩绅。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这诗开首两句,先叙述朋友从前和别后的情况,似写得平顺闲淡,明代的唐汝询还说,“此诗本中唐绝唱,然‘江海‘山川未免重叠”(《唐诗解》)。他对这两句颇有微词。其实,据说眼睛不大好用的唐汝询,是看漏了眼。从表面上看,“江海”和“山川”确是同义词,但司空曙所说的“江海”,是实写,因为他曾在江南一带长期居留,江南交通多用舟船。看来,韩绅也曾在江南居留,“江海”当是特指他和韩绅分别的地点。司空曙在二十四岁到长安考试落第时,曾说过:“欲归江海寻山去,愿报何人得桂枝。”(《下第日书情寄上叔父》)显然,他说“归江海”就是归江南。至于“山川”,则是泛指。所以,这两句用词,并不重叠。
我们要注意的是第二句,“几度隔山川”,在平顺的叙述中,蕴含深意。司空曙是要告诉读者,他和韩绅,彼此是互相思念的,是希望常能见面的。可是,他们明明有几次本来可以见面的机会,也许,彼此都到了相距不远的地方,却又山川相隔,无法沟通,失之交臂,于是倍感失落。不错,这句诗确实只是平平道来的叙述性语言,却又婉曲地说明相见之难,流露出彼此渴望相见的情感。这就是司空曙用“几度”的缘故。如果用“一去”“从此”之类的词语,便无法传达出这特别的意味。
更重要的是,正在十分惋惜的时候,诗人却意外地在云阳驿馆见到了亲密的朋友韩绅。这清楚地表明,在那被认为是“绝唱”的三、四两句出现之前,司空曙已预先做好了铺垫。也说明司空曙在写这似乎是信手拈来的作品时,在艺术构思方面,是有过全盘的考虑的。
“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这两句确是精彩至极。“乍见”,又是全诗的“眼”,是司空曙写和韩绅相遇的规定情境。如果一千多年前,可以像今天这样,使用微信或者电话相互沟通,约定彼此见面的时间,那么,即使是时常思念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相遇的一刻和相聚的情绪,与司空曙的感受必然完全不同。显然,这首诗,正是环绕在“乍见”的独特情况下展开。而且,司空曙也知道,这次相聚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第二天就要分别,非常仓促,这叫“宿别”。
描写朋友相见一刻,或是别离一刻的图景,往往最能表现和抒发友情的深挚。但司空曙的《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不同于只写送别或者只写相遇的作品,它围绕着意外遇见,短暂相处,而又即将别离的特定情景,抒发悲欢离合的复杂感受。正由于司空曙能在短短的篇幅中,写出故人相聚一刻的百感交集,从而让这首诗成为千古流传的佳作。
司空曙抒写友情的作品,对特定时刻的选择,是很注意的。像他写过“悠悠多路岐,相见又别离”(《送程秀才》),又写过“逢君喜成泪,暂似故乡中;谪宦犹多惧,清宵不得终”(《酬郑十四望驿不得同宿见赠因寄张参军》)等,都着眼于写乍逢乍别的情景。其实,杜甫也曾注意到选择这特定的时刻来抒发感情,在《送路六侍御入朝》一诗中,就写过“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可惜,杜甫对此,并没有进一步展开描写。
图写这次和韩绅见面,首先使用“乍见”一词,而不用“一見”“忽见”之类,这是因为“乍”字的本义,还包含了突然、骤然的意思,并带有意想不到惊愕的意绪。如果换了另外一词,实在无法表现出早就盼望有机会相见,却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忽然见到故人那种惊喜交集的情感。正是这意外的相逢,让他们简直不敢信以为真,反而怀疑这是不是在做梦?所以,不要看轻这似乎很平凡的“乍见”一语,正是它具有爆发性含义,这感情波动强烈的振幅,为下面出现“翻成梦”的异常感受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司空曙处在同一时代的戴叔伦,也写过取材和司空曙极似的诗,题为《客夜与故人偶集》,兹录如下:
天秋月又满,城阙夜千重。
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
风枝惊暗鹊,露草泣寒蛩。
羁旅常堪醉,归留畏晚钟。
 《戴叔伦诗集校注》蒋 寅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
《戴叔伦诗集校注》蒋 寅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这首诗,题目上说到“偶集”,也写到怀疑是否在梦中相见,但它并没有表现出突然相遇的神态,这一来,既没有让人感知到对故人感情的真挚,也没法表达出“偶集”的惊讶。这样,即使戴叔伦也抓住了最能表现友情的时机,却没有惊人之笔,显得平平无奇。相比之下,我们便可以发觉司空曙强调“乍见”的重要性。它既包含了戴叔伦题目中所说的“偶集”,而“翻疑梦”三字,又简洁地包括了“翻疑梦里逢”五个字。更重要的是,有了“乍见”这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语词,便让审美受体陡然一惊,感受到作者和韩绅在初见的一刻,所产生的特殊而又复杂的心态。
亲友之间,意外重逢,翻疑是梦,这也是诗人们常有的情感,但写法各有不同。杜甫的《羌村三首》,写在乱离中他突然回到家中,“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传神地表现和抒发了夫妻之间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忽然见面的情景,感人肺腑。宋代晏几道的《鹧鸪天》“从别后,忆相逄,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细腻地写出了恋人在久别后,相见时感慨而又温馨的场面。但司空曙在写和韩绅意外相遇时,则是“相悲各问年”,他们悲伤地互相询问彼此的年纪,这样的处理,实在高明得很。
上面说过,戴叔伦写朋友“偶集”,只有“翻疑梦里逢”一句,再没有展开。司空曙则选择一个看似平凡的细节,具体地表现他和韩绅见面时的情景。
首先,他写故人相见时的情感,不是兴高采烈地“相欢”,不是执手问候的“相看”,却是“相悲”,这很反常。而且,他们见面后互相询问的,竟是一个看似平常而又让人意外的问题。为什么司空曙只选择“各问年”这一细节,来展示故人乍见之悲?这似乎很矛盾,也很费解。然而,正是这让人意外的问题,让读者感受到这首诗的艺术魅力。
为什么故人相见,首先悲伤地各问对方年纪?想深一层,却一点也不奇怪。这正好表明,挚友分别多年,时间太长久了,彼此的年纪,已记不清了。更重要的是,分别后,多年没有相晤的机会,白发催人老,青阳逼岁除,彼此容颜已改,差不多认不出了。于是,诗人写他们见面时,竟撇开其他话语,只突出选用他们互相询问年纪。通过“问年”,同忆旧容,追怀逝去的青春,感叹世事的沧桑、宦途的险巇,这就是“相悲”的缘因。于是“各问年”,简单的互相询问,包含了多少辛酸!当他们知道了彼此的年纪,往事历历,奔来眼底。显然,这“各问年”的细节,看似平平无奇,其实是在彼此的问答中,牵动回忆,引发今昔对比等种种联想。
在诗中,描写两人相遇的具体细节,是表达感情深化的有效通道。像杜甫在《赠卫八处士》中写道:“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他想起卫八处士,过去只是一个光杆司令,等到二十年后再见面时,看到他儿女成行,个个天真可爱的样子。生活变化的具体细节,便勾起诗人对友情种种酸甜苦辣的滋味。同样,司空曙只写他和韩绅“各问年”,语虽简约,却是内涵丰富而又可以让读者看到具体的情景。他们种种复杂的心理状态,通过简单的话语,也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方回说,司空曙这首诗,“三、四一联,乃久别忽逢之绝唱也”(《瀛奎律髓》)。纪昀还进一步评述:“四句更佳。”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联中所展现的细节,既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心境,又有着普遍的意义。即使在今天,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我们经常看到久别忽然相遇的老同学、老朋友,在聚旧时,也会彼此问起生活的现状,回忆年轻时代的种种往事,在回忆中体味人生,加深友谊。因此,司空曙写的这一联,情意真挚,并且具有典型性意义。
司空曙没有进一步写他和韩绅怎样互相倾诉,而是转过笔锋,直写他们晚上在云阳馆相聚的情景,那就是诗的第五、第六句:“孤灯寒照雨,深竹暗浮烟。”
按理,这诗的颔联,作者直接描写他和故人乍然相见悲从中来的情状,那么,在颈联,应该会从这方面做进一步的发挥。与司空曙同一时代的李益,也写过一首意趣与此相近的五律《喜见外弟又言别》。在写到两人相遇以后,便说“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大家唠叨了好半天,这是承接在见面相认后,顺流而下十分自然的动态。但是,司空曙在写和韩绅“各问年”后,立即打住,接下去写的却是晚上室内外的情景。这一来,在颔联和颈联之间,似乎脱节;而且,在第五、第六句的图景中,也没有人物出现。这样奇特的处理,等于在诗中留下了一大片空白。而这空白,却是不写之写,是我国传统艺术中特有的虚写。
 《瀛奎律髓汇评》〔元〕方 回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版
《瀛奎律髓汇评》〔元〕方 回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版本来,挚友久别重逢,一定有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在相聚后的一段宝贵时光,他们做些什么?是回首前尘?是互相抚慰?是携手长谈?这一切,司空曙都不写,说实在的,也写不胜写。司空曙在创作技巧上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引而不发,只让读者驰骋自己的想象,去感受这对故人久别重逢难以言传的心境。这样做,比直接叙写他们的友情,更能驱动审美客体对意象进行再创造,获得更大的艺术效果。
那天晚上,云阳馆外,天在下雨,滴滴淅淅;客房里,只有一盏孤灯,映照出外面的雨水。在这里,司空曙下一“寒”字,特别能显出他的炼字功力。
首先,司空曙写屋里只有一盏灯。一灯的烛光,不可能是明亮的。何况,他形容这灯,不用“一灯”,而是“孤灯”,强调它是一盏孑立孤独的灯。这灯发出微弱的光波,摇摇曳曳,已经足够表现出屋子里一片凄清的景象。紧接着,司空曙强调这灯发出的光,竟是“寒”的。这“寒”字,用得非常灵活,读者可以理解为它发出的光影,寒浸浸地照见窗外的雨水;也可以理解为孤零零的灯,照见窗外显得格外寒凉的雨水。其实,烛光和雨水的“寒”,也都是屋里的人心底凄寒的折射。于是,尽管司空曙在诗句里,没有写到屋里面有人物出现,但是,在读者的心头,却感悟到在这空荡荡的画面的后面,俨然出现两位故人凄然对坐的模样。况且,这“寒”字,是承接第四句的“相悲”而来的,于是,诗意通体,连成一气。显然,司空曙下这“寒”字,绝非信笔为之,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这做法,就是人们所说的“炼字”。
在诗词创作中,字和句的选择,是很重要的。胡仔说:“诗句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苕溪渔隐丛话》)当诗人把意象化为文字符号,而哪一个符号更能恰切地表达意象,诗人要经过一番选择、过滤、扬弃、确认。这一过程,前人称之为“炼”。炼字,并非追求采用怪僻的词语,而是需要写出新意。清代的庞垲说,能找出“言当前之心,写当前之景”(《诗义固说》),便是炼出了新意。他认为用字用句,凡能恰切地表达诗人在特定情景中的心态,就可以称之为“新”,就是炼出了好句。实际上,他是把“真”和“新”联系在一起。沈德潜也说:“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说诗晬语·卷下》)他所说的平、常、陈、朴,是指寻常的字眼。当其文字组合的意象能出人意料,这就炼出了“新”。人们都知道,王安石写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绿”字很平常,但没有人这样用它直觉地感受春天欣欣向荣的生意,这就是出新。同样,司空曙以“寒”字作动词用,让本来有一丝微弱热力的灯,反照出窗外雨水之寒,照见室内环境之寒,照出两位挚友心境之寒。无疑,这“寒”字,是常见的,却能透露出人物之情、所处之境,这就有了新意,是司空曙在炼字方面的妙着。
“深竹暗浮烟”,诗人写窗外的竹丛,暗暗地浮起烟雾。有些版本,“深竹”作“湿竹”,在没法判断哪种版本才是司空曙原作的情况下,我认为,从对偶句需要工整的角度看,以“深竹”对应上句的“孤灯”,似乎更贴切一些。
按理,在孤灯下,屋子里的人,怎能看到窗外竹丛浮起了烟雾呢?在黑夜里,雨脚如麻,打在竹叶上、地面上,濺出的水珠,也不能形容为烟雾。以我看,这句诗,是写在屋子里两人对坐,直到雨停。这时,窗外不知从哪里飘来一片烟雾,让竹影朦胧。司空曙写他和韩绅乍然相逢,一宿即别,他们共话沧桑,同感往事如烟,前路茫茫。这句诗的微妙之处,正在于诗人以眼中夜雾的暗暗浮起,表现他和韩绅心头上的伤黯迷惘之情在一阵阵泛起。
第五、第六句诗分别写室内与室外两个画面。两幅图景都没有人物出现。但是,读者分明感受到在画面之外人物的存在,感受到一双挚友孤灯对坐、西窗话雨的情感。这一联,就像电影拍摄中出现的“空镜头”。所谓空镜头,是画面上没出现人物,而观众却可以透过画面中的自然景象,感悟到作者或导演所要传达的主观情感。请注意,这首诗,在颔联与颈联之间,已留出一大片空白。在颈联中的两句,又出现两组“空镜头”,这用“虚”的手法,十分奇妙。而以虚写实,重视让审美受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正是我国传统艺术的创作特色。
诗的最后两句是:“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这是“相悲”情绪进一步的贯注。本来,两位故友寒灯夜话,互诉离情,已经很伤感了,但一想到明朝立刻又要分手,恨别之情更让他们倍感伤悲。在百感交集中,只能互相传递酒杯。这离觞,是惜别的酒,又是苦酒。至于在对坐中,他们有没有对话,说了些什么话,司空曙完全没有写,而只以共传离杯的细节,传达出故友乍然相见又即将分手时的惜别之情,其中多少感慨、多少唏嘘,尽在不言之中,让人回味无穷。
胡震亨说:“司空虞部,婉雅闲淡,语近性情。”(《唐音癸签》)司空曙曾任虞部郎中的官职,他的诗歌创作的总体风格,确实多是性情之作,语言优雅而平易,含义婉转而含蓄。《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一诗,最能体现他诗作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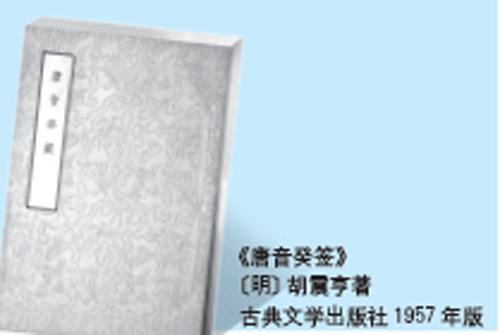 《唐音癸签》〔明〕胡震亨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
《唐音癸签》〔明〕胡震亨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大历年代,才子们的作品,缺乏宏大叙事的胸襟,更多是抒发个人细腻真挚的情怀。在创作形式方面,律诗的体裁经历了长期的摸索发展,诗人们对格律的工整、声调的协调、语言的把握,技巧愈趋成熟。因此,尽管闲淡写来,也显得形神优雅。
李益写过《喜见外弟又言别》一诗: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这诗向来被认为与司空曙的《云阳馆与韩绅宿别》,同是大历时期写离情的双璧。李益写他和外弟相见相别的情景,也和司空曙与韩绅乍然见面随即分离的情况一模一样。至于感情的真挚、语言的平顺、结构的一气呵成而又委婉含蓄,和司空曙的写法也很相近。但仔细分析,这两首诗所表达的情绪,又因亲朋之间的关系和感情的深浅,有所不同。在李益,他和外弟,只是幼时的玩伴,十年离乱,各不相见,谈不上是挚友深交。乍然相遇,在互通姓名后,才想起了旧时的容颜。于是促膝详谈世事的沧桑,也想到天明时又要分手,不禁感慨系之。显然,李益和司空曙的这两首诗,在创作水平上,难分轩轾。但由于他们相见的对象,以及情谊的深浅不同,因而在诗里表达的感情,明显有着不同的分寸。这正好说明,在中唐诗坛,诗人们对语言运用及律诗创作技巧的掌握,进一步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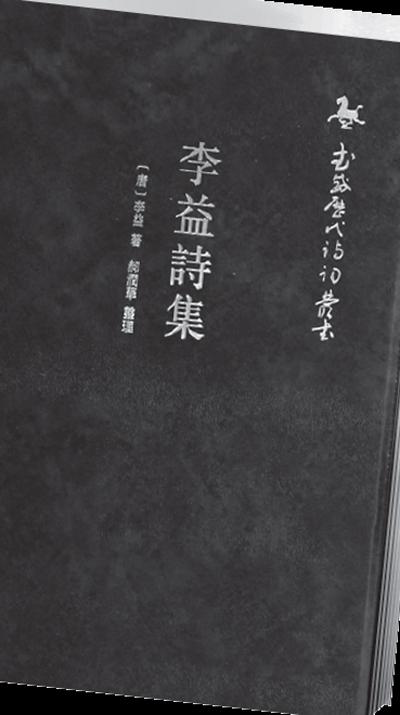 《李益诗集》郝润华整理中华书局2014 年版
《李益诗集》郝润华整理中华书局2014 年版但是,进入中唐时代,在社会生活愈不稳定,政治环境愈趋严酷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颠沛流离。加上权贵争权夺利,主政者频繁更迭,为官作吏的士人动辄得咎。他们既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前景,更看不到个人未来的命运。悲凉之雾,遍及华林。因此,大历才子们的诗作,大都写得流畅而低调,委婉而含蓄。司空曙多写送别之作,正是当时官场状态的反映。比如《峡口送友人》:“峡口花飞欲尽春,天涯去住泪沾巾;来时万里同为客,今日翻成送故人。”又如《别卢纶》:“有月多同赏,无秋不共悲;如何与君别,又是菊黄时。”都写得情调低迷。在《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中,司空曙抓住了与挚友在一天之内乍逢又别、疑梦疑真的特定情景,这一情景最能呈现迷惘悲凉的复杂心态,而他们“相悲”的真情实感,又以凄迷景色为衬托,委婉含蓄地表达出来。可以说,这首诗的风格典型地反映了大历诗坛的特色。
江淹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在过去,亲朋相别,再聚难期,黯然魂销,实在是难免的。不过,在不同时期和在不同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即使同样以亲朋相别为题材的诗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格调。在盛唐,写送别亲朋的诗歌也不少,像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一杯别酒,请元二珍惜故人的友情,并没有多少伤黯的情绪。又像高适的《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无人不识君!”他送给董大的,是安慰和鼓励。如果把这类以别情为题材的作品,和司空曙的这首诗做一比较,很容易看到盛唐和中唐诗坛格调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