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摹仿论》中,德国学者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特别讨论了一个现象,就是欧洲文学创作中文体的雅俗混用问题;还有在这种混用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中的欧洲人所看到的現实是什么样的。所谓“雅”不仅是一种书面语的语体之雅,还意指着表现世界的主人公是英雄、国王、大臣、贵族、神职人员,以及这个由神的空间和人的空间共构的神圣化的世界。而所谓“俗”则意指着一个凡人的世界、俗人的世界、平民的世界。二者在文体上最鲜明的区别就是悲剧和喜剧的对峙。在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中,悲剧和喜剧一方面是文体论意义上的,另一方面更是风格和文化意义上的:悲剧的世界是神圣世界的形式,喜剧的世界则是凡尘世界的结构。二者一方面分野鲜明,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相混合,而这就形成了全书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关键词“文体混用”。在对文体混用的叙述中,奥尔巴赫特别注意的是在雅的文体中,俗的文体是如何重新构建那个雅的世界的,其表现就是日常生活场景怎样成为神圣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让神圣世界获得了现实感、时间感、尘俗感。也是在这样一种思考中,奥尔巴赫将意大利诗人但丁作为全书的枢纽,因为正是“但丁的著作第一次让人们睁开眼睛看到了五光十色的人类现实的总体世界”。

但丁的《神曲》所记录的虽然是人在彼世世界的状态,但那个彼世世界并不是孤立的、不变的。现实世界以各种方式介入到了这个彼世世界中,并在世人面前呈现出了只有现实世界才会有的无数景象,并在这无数景象中发现了人之为人的情感和意志。奥尔巴赫特意引述了游历者但丁(不是创作《神曲》的诗人但丁)在诗人维吉尔的引导下,路过一条燃烧的敞棺夹持的道路时的叙述,这一场景出自《神曲·地狱篇》第十歌。维吉尔解释说,在这条路的两侧,棺椁中躺着的都是异教徒和不信上帝的人,而但丁可以和其中的两个人对话。也是在此,法利那太和加发尔甘底先后坐了起来,和但丁谈天。奥尔巴赫以为,这虽然是一个彼世场景,但无论是法利那太面对地狱时,脸上表现出的不屑而蔑视的神情,还是加发尔甘底听到自己儿子不幸遭遇时的忧伤和痛苦,都是高度世俗化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有的情感。这种世俗化的情绪描写,让一个丧失了时间的空间,恢复了时间的流动性,并让历史的延续成为可能。但丁在这个地方所书写的,绝不是超越凡尘的所谓英雄的颂歌,而是对虽然失去生命,却依然保留着生命意识的人的赞叹。法利那太面对但丁时先问但丁的祖先是谁,以此判断但丁是贵族还是平民;加发尔甘底在看到只有但丁和维吉尔时,不禁流下了眼泪,这是对自己生前未能更好地照顾儿子归多而产生的悔恨。奥尔巴赫由此认为,这种描写,这种对人的情感变化的描写,正是现实世界中才有的,并由此打破了地狱世界中的冰冷和严酷。

《神曲·地狱篇》第三歌开篇,诗人但丁就在地狱之门上写下了一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游历者但丁进入这个没有任何希望的世界,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以直观的形象塑造一个个末日审判的场景,还要在这个没有时间的世界中,塑造一切人的自我完成的样子。奥尔巴赫以为,“两个存身于棺材中的人的存在和此存在的场所虽然是终极的和永恒的,却不是非历史的”。打破这时空凝固性的,就是但丁对现实日常生活世界的把握;也恰恰是这种历史性,让处于绝境中的个体依然获得了鲜明的现实个性。“作为尘世事件标志的焦急和发展已不复存在,然而历史的浪涛依旧涌入彼世,一部分是对尘世往事的回忆,一部分是对尘世现时的关心,一部分是对尘世未来的忧虑。处处是作为形象保留在无时的永恒中的有时性。每个死者都将他在彼世的境地当作自己尘世剧的最后一幕,继续上演着的,时刻上演着的最后一幕。”可以说,诗人但丁借助游历者但丁之眼,将他所看到的彼世世界中的现实世界中的形象,刻印在纸页上,并打破了那句刻写在地狱之门上的箴言,让所有的死者再一次获得了生命。这也让《神曲》成为对人类事件进行大规模叙述的“大型史诗”。也因此,《神曲》虽名曰“神”之曲,但“神”只是终极的象征,“人”才是世界的主角。在彼世世界的悲剧中,时时呈现的是现实世界的喜剧。但丁没有像此前的那些作者,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那样,将一切现实世界的塑造都归为神圣世界的书写结果。但丁看到的是人的世界,并试图发现神的世界中所闪烁着的人的辉光。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赞叹但丁,说他是耸立在历史时间门槛上的诗人!
尽管文体混用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文学中已经出现了,但能将这一混用提高到一个全新水准的,即在日常场景的描述中见出神圣性的,但丁无疑是居功至伟。和但丁相比,写出《十日谈》的薄伽丘将文学俗的一面,即现实的一面、日常生活的一面、语言生活化的一面,发挥得更为出色,薄伽丘“越是成熟,市民性、人文性,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鲜明的通俗性就表现得越加强烈”。奥尔巴赫还认为,“没有《神曲》,《十日谈》永远也写不出来”。因为正是但丁在《神曲》中开创性地对现实世界的描写,使薄伽丘在一个宗教化的世界中书写尘俗凡事成为可能。可与但丁相比,薄伽丘一处理悲剧,就会显示出他苍白无力的一面;同时薄伽丘的写作缺少的是一种对悲剧问题,尤其是对道德问题思考的严肃性。这也构成了薄伽丘写作的致命伤。
奥尔巴赫认为,莎士比亚是沿着这条文体混用的道路继续写作的人,莎士比亚是伟大的,但这位伟大的剧作家却是有争议的。奥尔巴赫的这段话表明了他对莎士比亚的态度:“莎士比亚不仅与平民的情感世界相距甚远,而且在他身上甚至看不到丝毫启蒙主义的先兆,资产阶级道德观的先兆,维护情感的先兆;在他那些几乎一直不署名的作品里,吹出的气息与德意志觉醒时期那些形象身上的大不相同,在后者身上,人们总能听见那个感受深刻、情感丰富的人的声音,他坐在一个老市民的斗室里,为自由和伟大而欢欣鼓舞。”

二
同样是批评,美国学者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在写作《西方正典》一书时,用的是另一套规则。
《西方正典》一开篇,布鲁姆就急不可耐地把莎士比亚塑造为西方文学典范的中心,并且序言之后马上就把他列在了第一位。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就在此。在确立完莎士比亚文学原点的中心地位后,布鲁姆接下来就从但丁开始,按时间顺序讲述西方文学典籍的经典性价值。但丁后面是乔叟,乔叟后面是塞万提斯,再往下就是蒙田、莫里哀、弥尔顿、约翰逊,然后以歌德结尾,组成了著作的第一部分。他们被布鲁姆命名为西方文学典籍的“贵族时代”。接下来就是“民主时代”,那是十九世纪的文学写作;而二十世纪之后则是“混乱时代”,它开始于弗洛伊德。这种时代的命名方式直接来自于意大利人维柯,布鲁姆以此直接表明了他的基本文学态度,或者用一个他并不喜欢的词来叙述,叫“政治文化态度”。同时,这种命名方式也显示出了布鲁姆的历史时间意识:就文学而言,写作就是一个不断衰落的过程,是人物的贵族精神气质不断失落的过程,是从维柯的神权时代跌落到凡人的混乱时代的过程。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人物,无论是哈姆莱特、李尔王,还是伊阿古、麦克白,都是那种精神气质极为高贵的人物,无论其具体的行为德望,“莎士比亚的力量在于,他的悲剧主人公,不管是正角还是反角,都消解了戏剧和自然之间的界限”。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倾心由此展现了出来:为了莎士比亚可以打破文学叙述的时间序列,而所有的文学时间都围绕着莎士比亚展开,由此构成了文学写作的莎士比亚之流—在他之前的不过是为莎士比亚的到来做铺垫;在他之后的,不过是莎士比亚影响的结果。如此钟情于一个作家,甚至不惜曲折文学史,这在文学批评中也是十分少见的。
莎士比亚了不起,在于他创作的陌生性、原创性、内在性、普遍性、多元性……当然结果就是莎士比亚的世界性。在这一系列赞颂中,核心就是“陌生性”,布鲁姆把它界定为“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也因此,后面包括“原创性”在内的一系列词语,都可以视为是“陌生性”在语言上的变体,这个变体的最后结果就是世界性,即举世公认。但在对莎士比亚艺术创作陌生性的论述过程中,布鲁姆却显得有些气急败坏。为了说明莎士比亚的伟大,布鲁姆把几乎所有的诗人作家都贬斥了一顿—好像博尔赫斯除外。即如但丁,按照布鲁姆的看法,但丁“是以原创性、创新性和丰富奇特的想象直逼莎士比亚的唯一诗人”。这意思是但丁当然十分了得,但无论但丁怎样努力,也无法达到莎士比亚的高度。尽管如此,但丁已经是“唯一”的了。所以这句话貌似在夸但丁,但怎么看都觉得有很强的反讽意味在里面。而对于贵族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歌德,布鲁姆评价说,“歌德冒昧地公开嘲笑文体,而且是一种哈姆莱特式的嘲讽”,“歌德自己缺乏某种真正的写作诚意,虽然从另一方面说这种欠缺显得极其(而且有意地)迷人”。第一句是说歌德的写作是一种对莎士比亚的仿冒;第二句就不太好理解了,一方面说歌德的写作缺乏诚意,另一方面又说正是这种诚意的缺乏让歌德充满了魅力。那他到底要说明什么?但无论歌德的魅力如何,都是在莎士比亚之下的;哪怕在当代德国,歌德也不过就那么回事,“英美诗人们仍在不自觉地重复着华兹华斯,但我们很难说歌德在当今德国诗坛有什么重大影响”。

布鲁姆之所以如此,其原因还在于他所斥责的“憎恨学派”。对于何为憎恨学派,布鲁姆的解释是“他们希望为了实行他们所谓的(并不存在的)社会变革而颠覆现存的经典”。而憎恨学派首先要否定的就是莎士比亞,他们似乎对莎士比亚充满了恶意。在布鲁姆看来,这个学派中第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要算是托尔斯泰了,布鲁姆当然毫不客气地用怒火覆盖了他。他说托尔斯泰的著作《何为艺术?》就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序言中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题充斥着低劣而庸俗的生活观念,是达官贵胄的代言人,是蔑视普通民众的。于是托尔斯泰论述中的灾难就此发生了。布鲁姆认为,托尔斯泰虽然批评《李尔王》,自己却最后变成了李尔王,这是对托尔斯泰的绝妙讽刺。在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中,还充斥着一种道德狂热,其目的不外是树立自己的道德权威。至于托尔斯泰所持有的普通民众视点,布鲁姆更是说明,古希腊悲剧不是为大众写的,弥尔顿和巴赫的作品也不是,它们都不符合托尔斯泰的标准,就说明它们不好了吗?随后,布鲁姆颇带有讽刺意味地说,能通过托尔斯泰标准的,一流的作品有雨果和狄更斯的几部,再有就是一些二流的作品,比如斯托夫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来的。
当然,对托尔斯泰的斥责只是布鲁姆主攻的一面,布鲁姆还将火力指向了新历史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来自法国德国的各种批评家。这些文学研究的诸多流派被布鲁姆指斥为“反资产阶级的十字军”:“憎恨学派被其教条驱使而认为审美权威,尤其是莎士比亚表现出的那种权威,长期被当作文化谋略来维护商业化中心大不列颠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一做法自十八世纪迄今延续不断。”这种强烈的愤怒情绪,让布鲁姆对莎士比亚作为经典中心的论述,变成了一场直白的争吵,甚至在其后各章中都可以见到他为莎士比亚战斗的硝烟。而对托尔斯泰的抨击不过是布鲁姆“擒贼先擒王”的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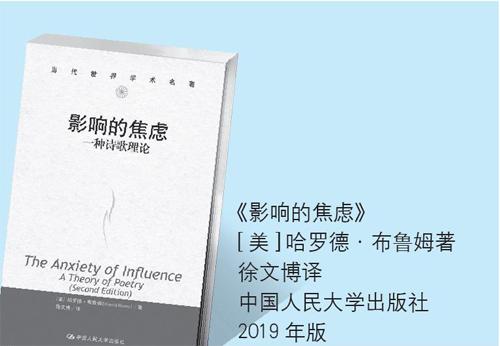
莎士比亚的世界性来自莎士比亚的多元性,布鲁姆认为这种多元性是跨越东西方的,与欧洲中心主义毫无关系,当然更不要扯什么文化阴谋论了!但布鲁姆的矛盾由此表现了出来。既然多元性是莎士比亚写作的基本特质,就意味着对莎士比亚阐释的多元性是合理的,那又何必固守对莎士比亚阐释的教条色彩呢?随后布鲁姆自己又有些尴尬地说出了一系列事实,即莎士比亚在欧洲非英语国家的传播和接受现实:莎士比亚在法国不太受重视,甚至从伏尔泰开始就自觉抵制莎士比亚,虽然其间经历了短暂的莎士比亚热潮,但今天法国从根本上是排斥莎士比亚的。在德国,说莎士比亚有很高的影响是不合适的;在意大利好像好一些,但似乎也就是那么两三个作家;在西班牙,莎士比亚受到了少有的忽略。反而是在俄罗斯,抨击莎士比亚的托尔斯泰,在布鲁姆看来却借鉴了不少莎士比亚塑造人物的感觉。当然,莎士比亚在英语国家中的影响就不用说了。
布鲁姆的“世界性”看来在空间上只局限在了欧美,书名名曰“西方正典”,却大谈“世界性”。布鲁姆说莎士比亚和欧洲中心主义无关,好像有些不大合适。
三
有趣的是,布鲁姆在介绍批评但丁的著名学者时,点了一下奥尔巴赫的名字。当然从布鲁姆的学术视角看来,奥尔巴赫所批评的但丁应该并不让他满意,其直接原因大概是布鲁姆把奥尔巴赫归为T. S. 艾略特写作系列的;而对艾略特的学术思想,布鲁姆的回应是“这些思想令我愤怒,促使我极力反抗”。
仅此而已。
奥尔巴赫写作《摹仿论》时,是身处流亡状态,为了逃避纳粹的追捕,本来在德国大学执教的奥尔巴赫被迫逃亡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他在写作时很多时候没有一手文献,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奥尔巴赫的创作激情。学者萨义德甚至认为,正是这种文献的缺乏反而解放了奥尔巴赫,让写作和批评可以不受故纸堆的影响。而对文本的精深解读,奥尔巴赫则遵守着严格的批评操作程序:紧扣住雅俗混用,将文学俗的一面视为一种积极地建构历史和现实的力量;在文学文本中,发现一个时代人们所“看”到的日常世界中富有活力的一面。这种混用的具体表现,就是它散播在音节、文字、词汇、句法,甚至是方言的使用上。而日常生活场景则时时进入文本的世界,向世人展示不同時代中人们的生活气息。这就是奥尔巴赫所说的“喻像”世界的一面。文学终归是对现实的模仿,但奥尔巴赫跳出了柏拉图模仿说的局限性—奥尔巴赫承认自己对模仿的认识来自柏拉图—而赋予了模仿以更加丰富的内涵。即从写作是对世界的模仿,转变为写作是怎么样模仿世界的。这种转换,让模仿(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获得了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即使是在壁垒森严的中世纪宗教世界,都可以发现尘世的形象和精神,顽强地生存于写作中;也是在尘俗之中,人们精神世界中乐观而积极的一面得以呈现。
萨义德从自己的文化观点,即知识分子恪守边缘性身份政治的立场,认为奥尔巴赫的写作“是想从现代性碎片中挽救感觉和意义的一种尝试。在土耳其流亡时,奥尔巴赫就从这种现代性碎片中看到了欧洲尤其是德国的衰落”。萨义德这种本雅明式的末世救赎论的解读,让奥尔巴赫的写作染上了弥赛亚推迟降临尘世的悲观情绪。但在阅读《摹仿论》的各个篇章时,这种悲剧感却并不明显。相反,恰恰是在日常世界中,也就是在普通人的世界中,奥尔巴赫发现了世界的希望所在。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种尘俗世界的赞叹,即如批评但丁,在奥尔巴赫充满激情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到他对尘俗世界中普通人的肯定,“他们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个尘世-历史生活的世界,一个尘世业绩、奋斗、情感和激情的世界,即使是尘世舞台本身也几乎不能如此充分有力地展示他们”。可以说,恰恰是在现实世界中,在普通人的激情奋斗中,奥尔巴赫发现了一种为萨义德所忽略的对世界肯定的精神、救赎的精神—对彼岸世界的想象之所以有力量,恰恰是因为有现实世界的支撑!
奥尔巴赫的这种写作精神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另一种现实的“喻像”:身在流亡之中,而心怀归国之情;反抗着所谓“神圣世界”的不公正,而渴望着尘俗世界的重生!
但这种精神气质,显然是布鲁姆在写作《西方正典》时所没有的。对欧美文学经典的阐释,布鲁姆并没有遵循什么严格的批评程序,基本上是兴之所至,笔随心想。虽然紧守着“陌生性”等概念,布鲁姆的文本跳跃性很强,多年来的阅读和思考让他对写作驾轻就熟;同时年事颇高,资历颇深,也让他毫不忌惮他人的所思所想。因此,无数作家和批评家都纷纷“中枪”。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西方正典》就不是写给学术界的,它面对的是那些“普通读者”。这与布鲁姆几十年前写作《影响的焦虑》时完全不一样。《影响的焦虑》上来先介绍术语内涵,制定批评规范,紧接着就在第一章提出了影响文学批评史的“误读”理论,随后各章的批评就一直“误读”了下去。但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已经不顾及什么误读不误读了,有时甚至感到文字颇为负气:“无论何人,不管怎么说,莎士比亚就是西方经典。”那意思是你奈我何?我就这样了!
布鲁姆《西方正典》中正文第一篇的名字就叫“经典悲歌”,一种末世论的气息扑面而来。事实也是,布鲁姆难掩他对现实的失望:面对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文化变迁,文学写作在不可逆转的边缘化潮流中,只能凭借“经典性”苦苦支撑其价值的合法性。而各色文学批评理论更是纷争四起,千帆竞发。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就认为,文学批评的兴盛,正是文学衰落的标志。布鲁姆眼看自己的很多学生也蜕变成了“憎恨学派”的一员,失落和不满自然在所难免。而阅读自此就沦落为一种“孤独”的精神体验,“经典”的价值也成为个体感受“焦虑”的过程;文学审美则收缩为纯粹个体的事情,和他人无关。几十年前的《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曾将诗的影响定义为诗歌强者相碰撞的结果,那种挑战艾略特批评秩序的“弑父”激情火光四溢!但在《西方正典》中,老迈的布鲁姆开始维护自己的批评秩序了,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影响的批评家,应该体验到了被挑战的悲凉!
布鲁姆虽然也在文学写作中肯定了文学俗的一面,比如他将莎士比亚的所有创作另起一名为《俗曲》—恰与但丁的《神曲》相对;他也肯定了但丁的写作中,充满了世俗的精神气质。但从根本上,他并不认为这些作品是为“俗人”创作的。他借威廉·黑兹利特对莎士比亚《科里奥兰》的批评表明,诗歌难以将人民的事业纳入其写作秩序。布鲁姆似乎没有看到文学写作对精致性、经典性、审美性不厌其烦的追求,恰是其失去现实性、尘世性,乃至人民性的起因。布鲁姆的“误读”理论是从读者出发的,但其阅读操作规范却是背离读者的。而文学写作一旦失却其读者,失却现世的风尘烟火,文学写作的根基又将何在?
同样是犹太人的后裔,奥尔巴赫出生于富有的商人家庭,最后走上了拥抱肯定文学现实性的道路。布鲁姆声称自己是制衣匠的儿子,最后传承了马修·阿诺德的衣钵,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精英政治的坚定捍卫者。在这一点上,布鲁姆应该是对的:一个人的审美趣味确实和他的家庭出身没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