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重读陈建华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年),深感这是一部优秀的明代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著作,而且由于集中到一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地区,并以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分析基础,就比一般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著作更深刻、更生动,也更富启迪。许多年以后,陈教授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的开篇也夫子自道:“我博士论文做的是明代江浙地区的文学,做文学的地域研究很有趣,也很有价值。”并说:“在我的笔记本里还有不少这方面的课题,却没有继续做下去。”这里提出的“文學的地域研究”,窃以为基本可以有效避免“地域文学的研究”的身份代入感和方法民科化,即一味鼓吹自身所在地域的文学及其历史的辉煌成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宏观的文学的历史)。而其未能继续做下去,颇为遗憾,好在陈广宏教授“继续做下去”了——近作《闽诗传统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学的一种历史省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而我更感兴趣的,乃是陈桥生博士新出的《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从来讨论岭南古代文学,对于唐代以前,或语焉不详,或干脆从张九龄说起,虽然显系失当,应该也是无计可施——对唐前岭南文学的探求研究,无论努力与方法,都太嫌不够。而从岭南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角度,此一阶段,意义或许更大。考古研究表明,史前文明岭南独立发展,“在新石器时代是自成一中心,有光辉的历史,起于当地,源远流长,与黄河、长江流域各文化中心相比,互有长短”(曾昭璇语)。进入文明时代后,很长一段时间仍是独立发展,建立了不少土邦小国,苏秉琦先生曾说过岭南有“自己的夏商周”,但真正有文字叙述的历史,也可以说真正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主要还是始于秦征南越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讲,此后广东文学或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岭外入中国”——岭南融入中华文明,或中华文明扩展至岭南——的历史,征伐、迁徙、宦游、贬谪都是重要的触媒,特别是作为书写文明大大滞后于中原的岭南,外来的力量更是不可或缺,在唐以前更是成为书写主体。而张九龄之所以能“横空出世”,也正缘于其成长地始兴与内地密切交流所形成的深厚的文化积淀。但是,这是怎样一种文化积淀,又是如何形成的?陈桥生《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主要从文学的角度,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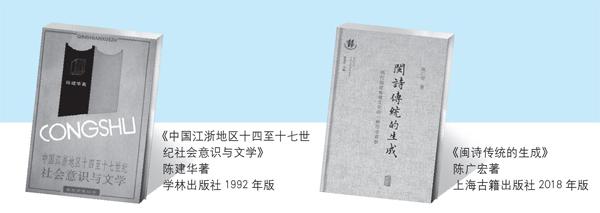
比如该书第七章“始兴在南朝的迅速崛起”,先特别讨论了范云(451~503)的个案,通过诸多流官谪宦的共同努力,以及范云的典型示范,不仅将岭南创作融入了永明诗歌的主流之中,更以《三枫亭饮水赋诗》(三枫何习习,五渡何悠悠。且饮修仁水,不挹邪阶流)等最早吟咏岭南风情的佳作等,形成后世足资取径的文学积淀。这是“岭外入中国”的一种文化形式。而岭外入中国的另一种形式,则是借由“中国”之人的栽培而进入“中国”,并在政治文化上占有一席之地者。再如号称“南天一人”并入传《陈书》的侯安都(519-563),便助推始兴的发展达至前所未有之高度。侯安都早年曾被始兴内史、南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萧子范辟为主簿,后“招集兵甲,至三千人”,追随陈霸先起事,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并在陈武帝陈霸先驾崩后,果断拥立文帝继位,居功至伟,影响深远。特别是在京都建康招集文士品评诗赋,一争高下,不仅有功于南朝文化的发展,当然更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岭南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而所招聚的文士如阴铿、徐伯阳等,不少都是刚刚经历侯景之乱从岭南回到建康,沾被着岭南文化的雨露,把岭南与首都建康的江南文化自然紧密地牵连交融,无形中更有力地促进了岭南文明与中土文明的沟通对话,从而推动着整个南朝文学的融合发展。因此之故,屈大均《广东新语》“诗始杨孚”条在追溯张九龄之前的岭南诗史时,便对侯安都的招聚文士之举给予了“开吾粤风雅之先”的高度评价;也正是因为有了侯安都等人的开风雅之先,才可能在盛唐出现张九龄这样的本土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
当然,更早承担始兴这一角色而且地位更为重要的,当属岭外入中国的第一个交通重镇和文化交流中心——交州州治和苍梧郡治的广信(封川);直到唐以前,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是海洋的世界,番禺(广州)固为一都会,文化却未有相应的昌明。故屈大均《岭南新语·粤人著述源流》正是从广信的陈元说起:“汉议郎陈元,以《春秋》《易》名家。其后有士燮者,生封川,与元同里,撰有《春秋左氏注》……始则高固发其源,继则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风余泽之所遗犹能使乡闾后进若王范、黄恭诸人,笃好著书,属辞比事,多以《春秋》为名。此其继往开来之功,诚吾粤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须知,无论陈元抑或士燮,他们虽生于封川,但都无不是中原移民的后裔;这种中原文化的岭南在地化,是岭外入中国的另一种形式。
再往前推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的合浦与徐闻(两港相距甚近),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朝贡贸易以及作为最早的南贬的集中地——从来贬谪之地,终须有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及相对健全的行政机构,才足以安置贬谪官员——更多地与中原保持着文化的交流往来,“传闻合浦叶,远向洛阳飞”,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又因海上丝绸之路首发港的原因而有谚曰:“欲拔贫,诣徐闻。”史上有名有姓的首贬岭南的官员——西汉末京兆尹王章,虽死于踏上贬途之前的狱中,但家属却照贬合浦,并在其妻子的率领下,借其地利,通过两年的经营,“采珠致产数百万”而“荣归故里”。在这些精彩的故事背后,陈桥生总结说:“抹去历史、个人的恩怨情仇,流徙所及,便是文化的流播所及。流徙者以其满腹的才华,就像一座流动的图书馆,被迫迁徙到了帝国最僻远的文化角落,愈行愈远,无远弗届,譬若阳光,不遗忘任何一个角落,譬若文明的种子,播撒一路,从而在荒远的土地上也开出鲜丽的花来。”
陈桥生的论述还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传统的中原文化以外其他各个区域,莫不存在一个先后次第的“文化入中国”过程;“粤越一也”,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过程中,后来成为新的文化中心的江南,曾经也是与岭南一样的断发文身蛮夷之地,却后来居上,成为新的文化中心。而晚近以来,岭南也渐渐有成为新的文化中心的契机。如陈寅恪在读了陈垣推荐的岑仲勉的论著后说:“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稍后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写的审查报告中所述,“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可谓对此的补证——晚近的岭南,正处于这种吸收输入外来学说而又不忘民族本位的枢纽地位,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对此实早着先鞭、论证甚力。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张君劢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中坚分子之推移与西南之责任》中,更直接提出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与时次第为文化中心之说;朱谦之、郭沫若也都有近似的说法。而陈序经的《东西文化观》《中国文化的出路》等著作,则可谓对梁、陈诸家之说的理论化系统化的阐述,认为输入西来新知的东西文化问题,其实正是南北文化的真谛。也就是说,我们所争论的以岭南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实可转换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南方文化的成长,一面接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一面接受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进而影响着北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形成一种非常重要的良性互动关系,不断促进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与时俱进。
其实诚如葛晓音教授在序中指出:“作者同时又特别关注了岭南文明如何反过来渗透、影响于中原文明。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是贯串全书一条鲜明的主线,也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创见所在。”循着陈桥生的论述,我们发现,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渐渐地更多地表现为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互动。特别是在明代以后,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地域文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参见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这种区域间文化的共生与互动,显得尤为重要,深具意义。偏居一隅文化相对落后的岭南,从明初以孙蕡(1337-1393)为代表的“南园五先生”开始,在广州南园结社唱和,开创岭南诗派,一跃而成为国中五大地域流派之一,不仅建立起了岭南文学发展的自信,更确立了岭南文学的新传统——后世稍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多集于南园,且每以“南园后五先生”“南园十二子”“南园今五子”等相称,以示文脉相承,岭南文学,自此渐由附庸蔚成大国,如康熙时主盟诗坛的王士祯说:“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当代文史大家谢国祯也说:“广东地方虽然僻远,但文化极为昌明。在崇祯间,陈子壮、黎遂球、陈邦彦、欧必元等人,以文章声气与江南复社相应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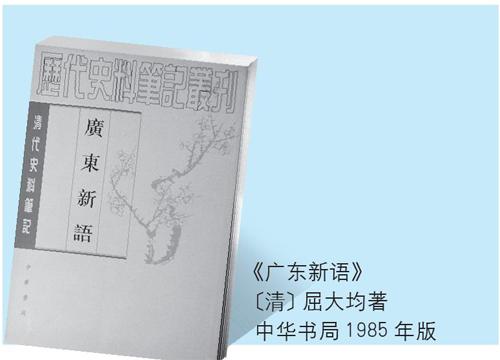
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岭南文学的这种发展,与江南文学的共生互动有莫大的关系,也可以说主要渊源系于江南。今人常引洪亮吉论清初岭南三大家诗句“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表称岭南诗歌的中原传统,窃以为纯属误读;王士祯既已指出岭南诗歌“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邓之诚也说:“大均与江南畸人逸士游,未改故步,佩兰与中原士大夫游,俊逸胜而雄直减矣。”这种雄直、古雅的传统,正沿自南园诗派及其首席代表孙蕡——“五古远师汉魏,近体亦不失唐音”(朱彝尊语),也正与相对软媚的江左也即吴中诗派相区分,而更接近以其师宋濂、刘基为代表的奇崛雄肆、驾宋元而上的浙东诗风。孙蕡师事宋濂,最为虔敬,如在《送翰林宋先生致仕归金华二十五首》中说:“二十余年侍禁闱,趋朝常早晚归迟。春坊一掬临分泪,记得垂髫受业时。”今检《宋濂全集》,诸生之中,孙蕡也是向宋濂献诗最多的,达三十一首之多,尤其感激宋濂的另眼相看青眼有加:“门生日日侍谈经,独向孙蕡眼尚青。几度背人焚谏草,风飞蝴蝶满中庭。”岭南文学的江南渊源,于此可见一斑。更有意味的是,从此之后,岭南作家交游,多尚江南,且每以蒙受教诲、品题等为荣,即便到了清代,岭南文化已经相对昌明,仍复如是。比如大名鼎鼎的屈大均,因先后得到两位文坛盟主钱谦益与朱彝尊的奖掖而感念不已,同时也倍感自豪:“名因锡鬯起词场,未出梅关人已香。”后来江苏吴县人惠士奇雍正间提学广东六年,岭南诗人何梦瑶、劳孝舆、罗天尺、苏珥等入署从学,人称“惠门四子”或“惠门八子”,蔚为文化盛景;阮元总督两广创辦学海堂并亲任山长,网罗张维屏、谭莹、陈澧、朱次琦等俊彦,更是极一时之盛。
但是,以江南为师,并不妨碍坚守自己的特质。在明初岭南五子的作品中,大量反映岭南风物的诗篇,就是一个象征。对此,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总结道:“百川东注,粤海独南其波;万木秋飞,岭南不凋其叶。生其土俗,发于歌咏,粤之诗所以自抒声情,不与时为俯仰也。”(《征刻广州诗汇引》)借此更可发展到互为师表的境界:“三吴竟学翁山派,领袖风浪得两公。”(屈大均《屡得友朋书札感赋》)钱仲联先生的研究也作如是观。如说“清中期广东诗人黎简,受浙派的影响,反过来他又影响浙派”(《钱仲联讲论清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良性互动的区域间文学生态,应当值得关注和思考。事实上也日渐引起关注和重视,二○一九年先后在粤沪两地举行的“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论坛,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体现。推而广之,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岭南文化与荆楚文化、齐鲁文化与中原文化等之间是怎样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共生互动形态?而这种共生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极有助于打破地域文化研究的地域桎梏,成为中华文明的岭南研究、江南研究、齐鲁研究、荆楚研究等的推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