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1962-2008)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1962-2008)华莱士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谈到,他们这一代美国小说家在面对消费社会和媒体文化的态度上,与传统小说家很不一样:他们将电视、电影、广告等流行文化视为浪漫主义作家看到的山川、河流等景观。不过,华莱士也清楚,这种类比的内涵是不同的。当代社会的自然是人造的自然,在这种自然之下炮制出的情感模式也是人造的。娱乐刺激欲望,欲望期待娱乐,两者形成闭环,构成一种瘾症。在闭环中犁开一条精神裂隙,并从中引发出绵密的思索与描写,向来是华莱士的拿手好戏。华莱士孜孜不倦地在各类文体中书写这种瘾症,最终将写作也变成了一场瘾症。短篇小说集《遗忘》就是对此类“精神癮症”做出的阶段性探索成果。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华莱士将目光对准了当代美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一块斑块。这块斑块阻塞感官体验,隔绝交流,使人陷入痛苦、困顿、烦闷之中。他将这块斑块命名为“遗忘”。
“遗忘”并不等同于“忘记”,两者虽然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对经历做出的一种反应,但“忘记”是漂白过去的过程,而“遗忘”则是忘记的结果。甚至,“遗忘”是人在屏蔽、定格空间时,不自知地体会到的持续昏迷感与沉睡感。华莱士把“遗忘”视为当代美国人精神生活的症状来写,写它如何形成、怎样表征,又是如何让人深陷其中不愿解脱,并指出可能的救赎之道在何处。结合华莱士的“三位一体”才华来看,“遗忘”既是知识的考证,也是精密的演算,甚至还是纷繁复杂的思辨。评论界一致认为,理解这部小说集中的“遗忘”主题,离不开隐藏在其中一篇名为《受难频道》的短篇小说中的一句话:意识是自然的梦魇(A consciência é o pesadelo da natureza)。这句话来源于罗马尼亚哲学家E. M. 齐奥朗的《眼泪与圣徒》。
齐奥朗追随尼采在《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中有关圣洁与强力意志之关系的洞见,想要通过《眼泪与圣徒》一书,探索“一个人是怎样弃绝自己并走上成圣之路的”等问题。齐奥朗在书中坦言,所谓圣徒身上的“圣洁”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它在“温顺之下隐藏的自我膨胀之谵妄,它那以美善来掩饰的强力意志”(参见《眼泪与圣徒》前言,商务印书馆2014年,以下引文亦同)。由于齐奥朗秉持“格言是瞬间的真理”的信念,《眼泪与圣徒》亦是用格言的形式写成的,而所谓的“瞬间”则是剥离语境,体现真理“在场感”的跳跃性论述。因此,要想理解华莱士在《遗忘》中引用的那句话,需将语境还原出来。

华莱士所引用的那句话,来源于齐奥朗对叔本华的论述:
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场梦是对的,但他不去培养幻觉反倒加以责难是错的,因为他这样就等于在暗示可能有更好的事物超乎幻觉之上。只有迷狂能治愈我们的悲观主义。生命若是真的,会让人无法忍受。若是一场梦,它将会是一种魔力与恐怖的混合,我们将欣然自弃其中。意识是自然的梦魇。
在这段话中,“迷狂”一词值得注意。“迷狂”原指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出神”状态,引申为处于情感或情绪中的自我分离状态。显然,在齐奥朗看来,“迷狂”介于“无法忍受的生命之真”和“魔力与恐怖的混合的梦”之间。但是,迷狂是一种意识吗?自然又是什么?梦魇又当何解?这一部分隐藏在尼采的《道德的谱系》中。
尼采虽然没有在论述该问题时明确指出“自然”是什么,却提到了有关“驯养动物”的问题。他指出让动物做出“承诺性的举动”是与“自然”相背离的。所谓“承诺性的举动”指依靠记忆,对某种行为进行刻意且无意义的重复。出于动物本性而言,这显然不是“自然”的状态。那么,反推之,所谓“自然”就是非刻意的、不知其意的、无法辨识是否在重复的浑然一体状态。在齐奥朗看来,“意识”来源于“慵懒和自由”的时刻:“当你躺在地上伸着懒腰,眼睛盯着上方的天空,你和世界之间的隔阂就像一条缝隙一样打开了—如果没有这条缝隙,意识就不可能存在。”如果说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原初状态,那么,意识显然是身心分离的状态,两者显然是对立的。但是,两者又是如何与“梦魇”产生联系的呢?在尼采看来,人会将过往的经历、体验犹如进食消化一样摄入意识,但在此之前也将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意识的门窗暂时会被关闭起来;不再受到我们的低级服务器官与之周旋的那些噪声和纷争的干扰,意识获得了一些宁静,一些白板状态(tabularasa)……”因此,这套阻碍程序具有悬置记忆的功能。换言之,这套机制就是遗忘。
遗忘是“门卫”,是“心灵的秩序”,是“宁静和规范的守护者”,与人的幸福、欢乐、希望、自豪感以及现实存在感相关,一旦失灵,人就会患上精神上的“消化不良”。正是在这点上,齐奥朗指出,叔本华的“错误”就在于:过往的经历之痛在“遗忘”机制失灵的情况下,绕开了“门卫”而进入意识之中,由此,不仅意识成了自然的对立面,而且也因为痛苦,转变成了“自然”的梦魇。这种状况无限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所言及的“痛苦是意识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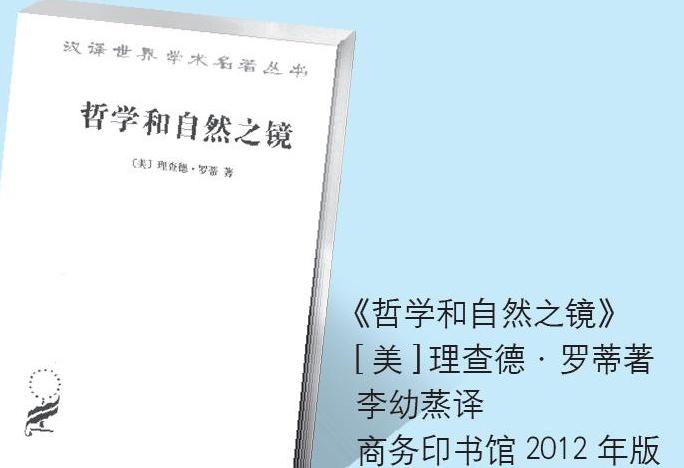
回到《遗忘》来看。华莱士在这部作品中显然发现了“迷狂”与“遗忘”之间的关联,两者都是一种身心抽离的状态,迷狂是宗教语境中上帝的临在,遗忘则是世俗语境中抵抗痛苦的机制。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遗忘”非但没有承担起合格的门卫职责,将痛苦阻挡在外,却因为“抽离”状态本身,使个体徒有脱节的悬置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充盈着的不再是尼采所言的强力意志,而是加倍的痛苦。简言之,华莱士所要写的就是当遗忘成为一种新型的痛苦,当悬挂于意识之前的那一汪忘川之水被污染,意志被虚无间离之后,当代人所经历的精神梦魇。遗忘催生梦魇,梦魇折射遗忘,这两面互相映照的镜子树立在意识之前,折射出人的精神以迭代的方式逐渐缩小。这种迭代感恰恰是当代美国人精神世界的动态萎缩。
《遗忘》共收入八篇小说,每一篇均包含固定的对立设置:孤立的外部环境和闭塞的人物内心。在华莱士的笔下,生活像是一场颠倒的鲁滨孙的故事,不再是鲁滨孙沦落孤岛,而是孤岛随时降临在人物身上,“遗忘”成了这片孤岛上唯一的景观。围绕着“遗忘”主题,并参考齐奥朗及尼采的潜在文本,读者不妨按照以下顺序进行阅读:《哲学与自然之镜》是对“遗忘”主题的最初构建;《灵魂并非一间铁匠铺》是承接;《黏糊糊先生》与《受难频道》可对照来读,两者都是对主题的展開;同名的《遗忘》则是对主题的深入描写;随后,《另一个先锋》展现的是“遗忘”的另一面;最终,在《灼伤之子升天记》和《美好的昔日霓虹》中,华莱士提供了极具个性化的对“遗忘”问题的解决之道。

《哲学与自然之镜》的篇名取自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同名哲学论著。华莱士早期痴迷于分析哲学,在小说和非虚构创作中屡次提起哲学论题。仅从这篇小说所呈现的效果来看,华莱士企图将哲学式的思辨引入日常生活,并企图让读者相信,在整部《遗忘》中,所有的故事并不依托情节走向给出“真相”,而只是呈现语言与人物意识的纠缠。故事展开在固定的场景内:叙事者和母亲乘坐公交车去拜访律师。叙述者喃喃自语,道出了贝克特式离群索居、诅咒人群的人物内心世界。由于这位酷爱养蜘蛛的叙事者的疏忽,所养的蜘蛛给母亲及周围邻居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母亲因为一系列近乎荒诞的遭遇,在脸上留下了一个永远呈现惊恐状态的表情,它奠定了整本小说集呈现出的人物处境:外部环境的创伤在人物身上留下的固定惊恐状态。此外,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小说里的一个细节,叙事者会将“蜘蛛”和“人类”统称为“样本”(specimen)。尽管叙事者声称“血浓于水”云云,但这个不带情感的称谓折射出人物身上抽离情感、抽离世界的观察视角,这种视角又不断受到周围各种声音的挑衅,反过来激发出人物内心对周遭世界的嘲讽乃至不适感的恐惧。整套人物与环境的法则构成了一个螺旋结构,不断绕开母亲受创,理应受到关爱的事实。

灾难侵入人身,化为永恒的恐惧,人物抽离情感,陷入孤绝之境,由《哲学与自然之镜》奠定的叙事模式随即由《灵魂并非一间铁匠铺》承接,并提升到另一层境界。小说的场景比较简单,主要由内外两个空间展开。外部空间是一间正在上“公民教育”课的教室,一位突然陷入癫狂的教师在黑板上一遍又一遍地写下“杀了他们”这几个字,引起了学生的恐慌。叙事者“我”和其他三名学生莫名其妙地被“固定”在了教室里,成了“被劫持的四个人质”。相比其他三位同学,叙事者本人特别容易被教室外的事物分心,甚至在整个事件中,他的思绪一直飘荡在外。小说的内外场景并没有形成对抗,华莱士在这篇小说中也没有让场景来催生人物的行动,而是围绕着人物此时的经历和分神的思绪展开深层次的架构。主人公的思绪并非漫无目的地展开,其蔓延的内容就像多格漫画一样,沿着教室窗户上的防护网格延伸出多条故事线来,各条故事线中的内容无论处于梦境还是现实,看似毫不相干,但都可归总为一种受难叙事模式,烘托出一种被意识之网牢牢捆绑的逼仄感,就像《哲学与自然之镜》中那位母亲脸上永久留下的惊恐表情一样。华莱士在这部小说中突出了烙印在人意识深处的受难伤痕,这些伤痕犹如漆黑的缝隙,不断向外涌动出摄魂的气息。主人公确实具有强大的“遗忘”的意志力,能够轻易把由失控的老师所引起的紧迫场景抵挡在外。但这种分神,任由思绪蔓延开去所展示出的内容,并不能帮助人们脱离险境,反而让人们更深地陷入了意识恐惧之中。反讽的是,对于主人公来说,“遗忘”反倒成了刻意的“回忆”。于是,在这部小说中,人们遭遇到了环境和意识的双面夹击,现实中难以逃遁的平面性恐惧催生着内心几何性恐惧。华莱士回应着齐奥朗的命题,赋予恐惧以立体空间感,一边是逐渐失控的环境中的危机,一边是人物看似缓慢,但实则步步深陷的意识旋涡,将失控的意识当成了自然加倍的梦魇。此种状态,套用华莱士喜欢用的语调,或许可以称之为:意识是自然的梦魇的平方。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人物内心和周遭环境的双重恐惧呢?这种恐惧是否只有在存在主义式极端的“境遇”中才能产生呢?显然,华莱士更善于在日常生活的波澜不惊中发现人物内心的震爆。读者可以发现,在华莱士的短篇小说中,人物并非百分百处于安静而幽闭的环境中,其小说的内部环境往往喷涌着纷繁复杂的声音。这些声音在《哲学与自然之镜》和《灵魂并非一间铁匠铺》中更多地呈现为人物意识和环境声的碰撞,甚至,通过华莱士的笔触,读者还可以分辨出这两种声音的远近,读起来更像是环境和人物在声音中展开的对手戏,其戏剧感来源于受难与恐惧之间的张力。
与之相比,在《黏糊糊先生》和《受难频道》这两篇小说中,华莱士有意识地削弱了先前几部小说所呈现的极端戏剧张力感,转而展现出类似“情景剧”般的场景,突然拧开了声音控制的旋钮,从而涌进来了更多、更嘈杂的声音。在这两篇可对照阅读的小说里,声音可分为三种。其一是“可听见”的声音。两篇小说都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职场活动,无论是《黏糊糊先生》中“产品试吃会”上的尔虞我诈,还是《受难频道》中传媒产业里的飞短流长,华莱士用几乎令人感到晕眩的笔法,极力描绘人物间毫无意义的废话、客套话、冷笑话、离题话,乃至自取其辱的调情话,从而搭建起一个无法从中逃遁的巨大声场,这种巨大的声场仿佛一张张会说话的隔音软垫,悖论性吸收声音,并加倍吐纳出声音。另一种是“可看见”的声音,这一点在《受难频道》中尤为明显。华莱士极有耐心地标记出每个登场人物的穿着品牌,从锐步、斐乐、缪缪、高缇耶、布拉赫尼特,到三宅一生、普拉达、山本耀司,等等,所有职场中的人哪怕不开口,也会呈现出一派视觉意义上的喧哗。服饰不仅体现着人物向外标榜的身份和等级,而且还向内构成了反讽的效果:无论品牌贵贱、职位高低,所有人都在废话连篇中实现了平等与民主。这类由听觉和视觉所激起的无意义体验,激发出第三种声音:脱离意义的感官骚动。《黏糊糊的先生》中出现了对市面上各类蛋糕成分的分析,其架势不亚于一场有关高糖、高脂肪产品的帝国扩张动员会。这款受测蛋糕之所以被称为“重罪”,是因为它含糖量极高,对食用者的健康构成了一场重大灾难,但这种灾难显然是以一种味觉享受加以讨论的。无独有偶,同样的场景也在《受难频道》中出现。所谓的“受难频道”是一个专门靠展现人们在战争、事故中的受难场景为盈利点的栏目,几经发展之后,它从单纯的静态图片连播模式,拓展成了动态影像的展播,甚至一跃成了现场直播节目。在小说发展到高潮时,这档节目甚至要直播一个人的拉屎实况。读者在较早的篇幅中就已经得知,这位靠拉屎来制造艺术品的艺术家,其实是受到了他妻子的怂恿和包装,把幼年时未经正确引导的如厕训练落下的难言之隐,假借艺术之名,转变成了一场噱头。因此,“受难频道”也正式转变成了消费灾难的流量产品。
在华莱士笔下,声音不再是人物在空间里传播信息的载体,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感官符号,一种传递意义的形式。只不过,所谓的“意义”吊诡地变成了一种“剥夺”,也就是说,当“剥夺意义”反而成为唯一意义的时候,声音就变成了华莱士在心中的“全然的噪声”:
每一件特定的事物,每一次经历,以及某人在面对该关注什么、该表征什么,该与什么东西产生联系、该怎么做,为什么要做等等问题时呈现的沸腾的静态。
“沸腾的静态”遵循资本的逻辑,成为流动的商品,这个主题一再出现在消费文化的批判中,本不足为奇。华莱士在这部小说集中透过这一层逻辑,描写“沸腾的静态”渗透入人的意识深处的状态。整部小说集都在描写的“遗忘”其实就是“沸腾的静态”,它展现的是当代生活中,弥漫在现实中的各类噪声,它通过各种形态让人沉迷自身,脱离环境,屏蔽他人,是当今社会中剥离宗教意味的“迷狂”。
更可怕的是,一旦噪声形成,就无法抑制。在同名的《遗忘》这篇小说中,“噪声”突然升了级,不再是声音,不再是视觉,也不再是感官欲望,而成了一种意识层面的笼罩。这是一出由打鼾问题引起的家庭闹剧,本该属于私密的噪声的鼾声,引发的是夫妇两人内心深处的焦虑和不信任感。两人均否认对方听到的是事实,妻子认为丈夫的鼾声实在恼人,而丈夫一口认定自己根本没有睡,两人为此去了心理医生那里做所谓的“睡眠实验”一探究竟。在试探的过程中,文中隐约透露出丈夫似乎对继女还怀有不伦的企图。最终,整篇小说突然在妻子醒来的场景中结束,读者会发现,这一切原来可能就是妻子所做的一场梦。梦境,睡眠,现实与幻想的真假难辨,噪声已不再仅仅体现在意识层面,而且还弥漫进了人物的潜意识。鼾声并不能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存在,它以更为复杂、更为绵延的思绪,响彻在另一个人的睡眠之中。表面来看,这是意识和潜意识关系的颠倒,亦即,一个人在梦境中催生了另一个人的睡眠,但实际上,华莱士揭示出,无论睡眠还是清醒都无法达到遗忘,这是一场擦拭遗忘的叙事,扑朔迷离的现实被挤压出意识追踪的范围,无意识领域成了一个永久定格隐痛的场域。
同时,“沸腾的静态”不仅蔓延在空间中,还会潜入时间中。在《另一个先锋》中,华莱士向读者展示了一出人在时间中遗忘自身的悲剧。这部小说依旧架构在“封闭场景中产生噪声”的固定叙事模式中。小说从一开始就迅速将读者拉入了一个“不可靠叙事”的迷宫里:
然而,先生們,我恐怕得说,我记得这个孤例是我一个密友的熟人大声告诉我的,这个人说他自己是在某次出差途中,在一趟高海拔的商务航班上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这则“劝谕故事”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经过了四重转述的故事(“我”听“我的密友”听“我密友的熟人”在商务航班上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一则故事),从一开始就迅速将故事的叙事时间打乱了。这则所谓的“劝谕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原始部落中天赋异禀的孩子,他身上显然具有村民所不具有的近代科学知识。他一开始还在帮助村民解决实际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可到了后来,村民开始问一些有关私有财产、资源整合、人的存在感等问题,通过解答这类问题,孩子迅速获得了“神力”,直到有人提出了扩张整个村落的问题,孩子不知道回答了什么,导致这个人陷入了疯癫,由此引发了村民的恐慌。与此同时,另一个村落的萨满巫师前来试探这个孩子,并指出这个孩子之所以受到村民的爱戴,是因为村民并不知道孩子所知道的“知识”。孩子在解答的过程中,教会了村民,村民也有了从天真到经验的转变。这样一来,村民会很快不再理会这个孩子。萨满的话一语成谶,这些有了私有制概念,懂得了劳动获取尊严的村民们果然嫌弃起这个整天不用干活就可以获利的孩子,决定不再供奉他。最后,这个孩子就孤零零地在村子中央忍饥挨饿,最终村民离开了他,将整个村落也付之一炬。毫无疑问,萨满提出的问题的实质,归根结底是由一种超前性所导致的,只不过借助“知识”的形态,这个孩子过早地承受了加冕于时间之上的王冠,领先于他所处的那个原始时代。可是,这顶王冠封存了孩子的心灵,也固定了孩子的成长,他无法形成自己的意识,而顺理成章地依靠知识变成了权力的符号。参照齐奥朗的话来说,当意识不再是卫兵,而自立成王的时候,一切痛苦就成了固步自封的孤独暴君,它以凯旋的姿态,沉浸于自我的权力中心。时间的失序会让痛苦产生逸乐。就如同这则经由多人转述,时间混乱,真假难辨的故事一样,讲述故事的形式本身也在传递宣泄故事的快感。通过这一篇故事,华莱士点明了“沸腾的静态”的完成形态:人在甜蜜的痛苦中迷失空间感知力,并吞噬一切时间的体验,“遗忘”由此变成了在痛苦中享受痛苦的逸乐。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那个孩子最后之所以能够忍饥挨饿,靠的就是圣徒般承受痛苦来抵达心底密契的状态,这是对齐奥朗的《眼泪与圣徒》的最深刻的戏仿与回应。从另一方面来说,村民最终选择离开村落,并将村子一把火烧尽,本身就是一场遗忘的仪式—将超前于时间获得的一切,复归于时间,他们不愿承受痛苦,也不愿承担权力带来的毁灭,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法,也不愿意享受痛苦的逸乐,宁愿甘于自然、原始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一则“劝谕故事”,孩子成了一件具有训诫意味的祭品,在那上面,孩子既是沉溺自身的主体,也是被忘记的对象,它永恒地固定其中,成了“忘却”的过程和结果。
封闭的自我承受着意识和无意识的噪声所带来的痛苦的逸乐,这就是华莱士勾勒出的遗忘,也是沸腾和静态的辩证关系之体现。沸腾是欲望的显现,静态是包含快感的静候,就这样,外在的“灾难”和内在的“瘾症”就处在了同一纬度。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徒有自由和悠闲的外表,内心却难掩崩溃的实质,他们被固定在封闭的空间里,也锁定在意识之中。面对这一切,华莱士在《灼伤之子的升天记》和《美好的昔日霓虹》中,提供了极具理想色彩的解决之道。这两部小说都包含一种潜在的温度。因为家长的疏忽,一个不幸受难的孩子因烫伤医治不及时而去世了,华莱士在这个篇幅最短的小说最后留下了温情的一笔:“孩子的身体膨胀了,走了出去,预支了一生的工资,过上了无拘无束的生活。”而在《美好的昔日霓虹》中,读者很快就会发现,那位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个骗子,并无法在他人心中改变自己的人,早已自杀而亡,留下给读者看到的,其实是类似遗书般的文档,这个文档被一个叫作“大卫·华莱士”的人在校友录上看到。两部小说都描写了死亡,这倒不是如一些批评所言,描写的是死亡成了解决烦恼的最终方法,而是一种“对话”,与意识的终结的一场对话。所谓的“霓虹”,华莱士在文中通过注解做出过解释:
所以,不仅你的整个人生,还包括人类的每一个个体,在能想象到的可用来描述和说明的生活中,都有一闪而过的时间,它就像企业标志和那些窗户都非常喜欢使用的霓虹灯,它们围绕着草书字体,以字母的形状呈现,这些霓虹灯以类似冲撞和死亡之间实难计量的一瞬,印入你的脑海。
所谓霓虹般的“印入脑海”,其实就是一种对抗遗忘的方式。文中的华莱士,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作者本人,而文中那个人物也多少具有华莱士的影子,那么,这部小说就成了作者华莱士与原型华莱士,通过书写小说的形式打了一次照面。在《美好的昔日霓虹》的最后,轻触过“死亡”的华莱士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他更真实、更持久、更多愁善感的那一部分勒令另一部分保持沉默,就类似这样,平视着它的眼睛,几乎很大声地说道:“别再说话了。”
这一场“照面”类似孩子的“转世”,其本质就是一种与自我的“对话”。如果说以“沸腾的静态”为表征的遗忘来源于不可避免的伤痛,并在人们心中遗留永恒的惊恐,而这种惊恐还会以各种感官的符号性,占据人们的空间,潜入人们的时间,搅乱意識与潜意识,从而成为一种喧嚣着的虚无状态的话,那么,“对话”则是从“沸腾”的状态中筛选出个体真正需要去面对的内容,并将“静态”复归于个体在意识领域的平静,当“遗忘”有了实质的内容和平静的状态,它才真正有可能成为意识抵抗痛苦的力量。
当然,读者仍需关注的是,华莱士书写这部小说集的时间段也是美国经历最惨痛的恐怖主义袭击,并迎来所谓“后9·11”时代。在这期间,华莱士没有像乔姆斯基、鲍德里亚等人那样展开对恐怖主义的追溯,勾勒当代人认知图景的崩塌,也没有像他的好朋友弗兰岑那样去直接描写中产阶层恩典的谢幕,而是直抵人们面对灾难时的意识深处,呈现出美国人身处后现代社会中早已有的意识恐怖。因此,整部《遗忘》也对应着时代的主题。当外在的恐怖主义与内心深处的恐惧不可避免地相遇时,华莱士也通过小说递交了一份抵抗“沸腾”、打破“静态”,让个体通过“遗忘”来重塑面对自我的方式,他与尼采、齐奥朗一样,都在用一种“否定”的方式建构一种“肯定”的力量,都在用绵软的方式建构强大的力量,也都在用“遗忘”来记住自我与时代的定位。
最为关键的是,华莱士作为一位小说家,曾在告别世界四年前,通过写作与自己展开了一场超越时间、超越遗忘的对话。至少,他曾经这样试过。
二○二○年,于杭州良渚
《遗忘》,[美]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著,林晓筱译,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