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写曹操将刘备唤至府中,“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此节通常简称“青梅煮酒论英雄”。可是“煮酒”何意?是把青梅放在黄酒或白酒中煮吗?这个疑问藏在心里很多年了,去年读程杰先生的《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才弄明白。原来“煮”字不是动词,而是形容词。青梅、煮酒是两种食物,青梅是下酒物,煮酒就是一种酒。将“煮酒”理解为给酒加热,是误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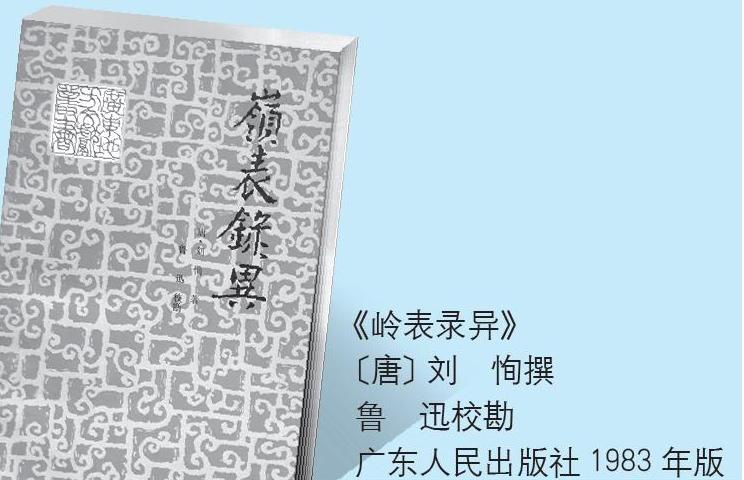
宋代的酒主要分为生酒、煮酒两大类。杨万里《生酒歌》云:“生酒清于雪,煮酒赤如血,煮酒不如生酒烈。煮酒只带烟火气,生酒不离泉石味。”这说明生酒是白的,煮酒是红的。煮酒多于腊月酿制,然后通过加热蒸煮来杀菌,封存起来,其法或始自晚唐时期的岭南一带。南方天气热,酒熟则易败,就把酿好的酒装入陶泥酒瓮中,以火烧之,杀菌封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煮酒。其法见载于《投荒杂录》《岭表录异》等唐代文献,而大盛于宋。一般情况下,煮酒开坛的时间在旧历四月初,恰与青梅初成的时间接近。古人所饮之酒,度数较低,所以不用许多肴馔,常用水果下酒。鲍照诗云:“忆昔饮好酒,素盘进青梅。”那么青梅佐酒,至少在南朝就已成风气了。除了青梅,甘蔗、黄柑亦可充下酒之物。
青梅的食用价值很高。《尚书》中已经有了“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说法,把盐、梅等视之。古人食用青梅,除了佐酒,还喜欢蘸盐。陆游诗云:“苦笋先调酱,青梅小蘸盐。”“梅青巧配吴盐白,笋美偏宜蜀豉香。”“青梅旋摘宜盐白,煮酒初尝带腊香。”(以上三例,均见程杰《论青梅的文学意义》)这也让我想起周邦彦的名句:“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这句子的遣词和意境皆极美,可是与“吴盐胜雪”有何关联呢?我猜人们吃橙子,是蘸盐吃的。宋人曹勋有一首《鹧鸪天·咏枨》,也谈到吃橙子要蘸盐:
枫落吴江肃晓霜。洞庭波静耿云光。芳苞照眼黄金嫩,纤指开新白玉香。
盐胜雪,喜初尝。微酸历齿助新妆。直须满劝三山酒,更喜持杯云水乡。
“枨”即橙。这大概吃的是苏州太湖的洞庭柑橘,唐以来即是贡品。明末的歌谣里说:“细茶出在六安州,洞庭西山出蜜橘。”西山的蜜橘、橙子,自古有名。橙子经霜才好吃,故此词一开始写橙子的产地与时令,要突出“晓霜”和“洞庭”,次写其色、香、味,则着眼于人,着眼于那个剥橙子的女子。“黄金嫩”写橙子的色,“纤指开新”则是说剥好的橙子留下了那个女子纤纤玉手的香味,用盐蘸一蘸吃了,那种微微的酸味不仅无害,反而更令女子娇媚了。有这样的女子来劝酒,自然要大醉一场了。曹勋是宋徽宗宠臣之子,后来与徽宗一起被抓到北方,逃回后以使臣身份多次往返宋金之间,曾把宋高宗赵构的母亲韦太后接回南方。杨万里的诗里赞美他“长揖单于如小儿”“功盖天下只戏剧”,功成之后“笑随赤松蜡双屐”,恐怕是别有寄托。其词存世不算少,除少数有悲慨语,多是咏物赏花词,喜堆垛,少生气。他还有一首《浣溪沙·赏枨》:
禁御芙蓉秋气凉。新枨岂待满林霜。旨甘初荐摘青黄。
乍剖金肤藏嫩玉,吴盐兼味发清香。圣心此意与天长。
这首词也写到了吴盐与食用橙子之间的关系,只是格调要差一些,漫溢着宠臣气息。宋人写女子手剥橘橙,多抓住半开未开的那个瞬间—所谓“纤指破新橙”也,再加上想象,其中似乎有点小套路。东坡有一首《浣溪沙·咏橘》:
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
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
这首词要比曹勋的那首好多了。特别是“香雾噀人惊半破”这一句,写得够细够真,“噀”字体物精微,点点滴滴的汁液如在目前,而“惊”字摹人心理,非心思细腻者不办。把橙子掰开或切开的时候,橙子本身会迸射出许多细微的汁液,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香气清芬,越是鲜嫩的橙子越是如此。只是吃橙子蘸盐,吃橘子为什么不蘸呢?可能是因为橙子太酸了。
青梅味酸,容易倒牙,“梅子留酸软齿牙”是也。《调鼎集》里说,嚼胡桃仁即可解之,不知确否。除了佐酒,青梅亦可作弹丸,可腌卤糖拌,可做酱,可泡酒。青梅产于南方,青梅酒自然也多见于江南或西南。第一回喝青梅酒是在云南,四个人夜饮,喝了七斤半,两个喝得酩酊大醉,两个在醉与不醉之间,从此知道青梅酒之厉害。去年五六月间,有位同事帮我泡了一坛青梅酒,底酒用的是牛栏山高度酒。两个多月后,我们拿了一瓶去丰盛胡同小饮,醇美异常,只是火气稍重。若能放上一年,风味更佳。日本的熟青梅酒,酒味醇正,唯度数较低,不能令人過瘾。台湾有一种用青梅腌制的豆腐乳,风味有其独绝处。

我们喝酒,我们食用青梅,我们阅读,却常常和古代之间隔着日常生活的裂隙,只能靠想象力和知识建立碎片之间的关联。我们在误解里理解,在有限中想象庞大的真实,在一点点小小的收获里欢欣,然而所写下、所了解的一切只是碎片。
二
前年友人曾送给我四五只黄澄澄、外形酷似柚子的东西。我用清水洗净,放到窗台上,回到家总能闻到一股清芬之气,淡淡地萦绕在室中。这便是香橼。
香橼产于闽、粤、滇、桂等地,性喜温暖潮湿气候,又称枸橼。嵇含《南方草木状》云:“钩缘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胡人重之。极芬香,肉甚厚,白如芦菔。女工竞雕镂花鸟,渍以蜂蜜,点燕檀,巧丽妙绝,无与为比。泰康五年,大秦贡十缶,帝以三缶赐王恺,助其珍味夸示于石崇。”晚唐刘恂《岭南录异》也有类似的说法。二书均记载今两广一带风物,“钩”字或系“枸”字之误。枸橼一物,原产域外,“胡人重之”“大秦贡十缶”云云,表明这种水果在当时是稀罕物儿。此物松江、嘉兴、湖州等地并有产,当即寒舍庋置之物,只是由于地域气候水土的差异,云南、四川一带的枸橼,形状、大小均与吴越所产有异。
生食香橼,奇酸无比。我曾剖开一只外皮干枯的香橼,尝过内里依然新鲜的果肉,是真的酸。据说,枸橼酸就是依这水果的名字命名的,南北朝时古人就用它来沤制葛麻,如今在食品、化妆品等行业中更是有着广泛的用途。不过,善吃的国人早就发明了食用香橼的好方法。《齐民要术》引裴渊《广州记》说它“味奇酢,皮以蜜煮为糁”,注家以为这个“糁”字指的是“蜜饯果食”,是有道理的。直到现在人们依然用香橼的果皮制作蜜饯,用糖蜜渍,别有风味。我曾经在网上买过两罐蜜渍香橼,味道有些单一,加工的方法则与古相似。据说有些少数民族制作的香橼蜜饯,甚至可以保存一两年,是宴会上一道精美的甜点,或许保存了更原始些的工艺。香橼也是食疗佳品,中醫认为香橼可以平肝舒郁,下气消食,化痰止咳,还可以解酒,所以一些食疗的方子会用到它。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一位同事的朋友从云南寄了一箱香橼来,一只只黄间青绿,清芬喜人,个头比我原来所见还要大些。云南香橼可切片食用,香气很淡,口感不像其他瓜果那样清脆。据说当地人会沾蜜而食,可以治疗咳嗽,还有人以香橼烹茶,大概也是取其药用价值吧。用香橼、柚子皮制作食物,在南方似乎比较普遍。《闲情偶寄》中提到一种香橼露,在米饭中加上一点,“食者皆诧为异种”,然不知其制法。同事花椒是江西人,前段时间他的母亲寄了一罐辣椒干渍柚子皮来,那味道劲辣实足,食之难忘。加工的方法,是先把柚子去皮,接着用开水泡,然后用水漂,再用开水泡,冷却后拧干,不要使之碰到生水,备料完毕,加入大蒜、生姜,再放干辣椒,加入生抽腌渍即可。其风味要胜过蜜渍香橼。
除却食用价值,香橼的佳处在于观赏与闻香。西晋时期人们已经注重香橼的香气,唐宋时此风已盛。《本草纲目》引苏颂《图经本草》云:“虽味短而香芬大胜,置衣笥中,则数日香不歇。寄至北方,人甚贵重。”《证类本草》也有类似的话,大概是从唐人那里抄来的。明人甚重水果闻香一事,吴中尤盛,常常在厅堂卧室摆放香橼、佛手等芳香水果。文震亨《长物志》云:“香橼大如杯盂,香气馥烈,吴人最尚,以磁盆盛供。”还有更讲究的,如《遵生八笺》所说:“香橼出时,山斋最要一事,得官哥二窑大盘,或青东磁龙泉盘、古铜青绿旧盘、宣德暗花白盘、苏麻尼青盘、朱砂红盘、青花盘、白盘数种,以大为妙,每盆置橼廿四头,或十二三者,方足香味,满室清芬。”文中提到的香橼,更有可能指的是佛手,不然的话,二十四头香橼摆在一起几乎像座小山,还不得把瓷盘压碎了。仔细看一下明清仕女图,便可以发现摆放佛手是那时的一种风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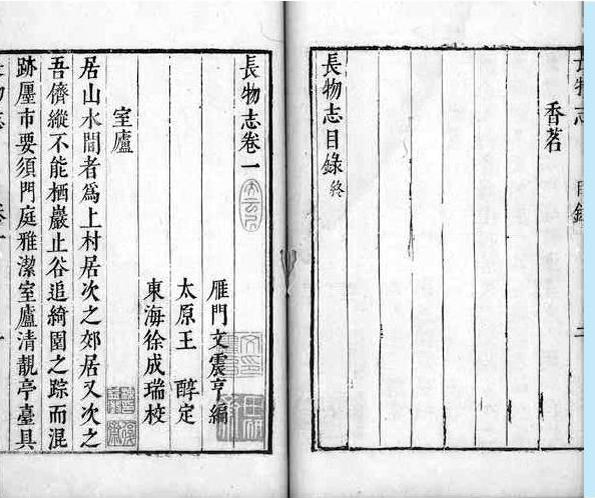 《长物志》,明末刊本
《长物志》,明末刊本香橼的花于五六月间开放,细密嫩白,香气“酷烈甚于山矾”,而果实硕大,所谓“素花开细细,芳实影团团”也。其种植场所,或在亭前,或在阶侧。陈贞慧《邱园杂佩》云:“自变乱以来,佛手、建兰、茉莉,五年不至矣,间有非山人寒士所得昵。余庭畔香橼数株,每当高秋霜月,赭珠金实,累累悬缀,不下四五百球,摘置红甆,幽香一室,凡吾之襟裾梦渖,皆是物也。以不用钱买,余得以分赠亲知,一时沾沾为贫儿暴富矣。”陈氏以为香橼韵致远胜佛手,香气“蕴藉耐久”,他的赠人佳果,不仅手有余香,也暗含了故国之思。
香橼可以食用,可以闻香,可以寄托故国之思,但对于它树干中隐秘的血液和果实中孤独的酸涩所知甚少。我们要走过很多地方才能走近它,要跨过时间的河流才能勾连起那些记忆的片段。

三
那条断头路上有一棵树,一树繁花,一树孤独。
那是一株木芙蓉,有五六米高,数百朵白色、粉红、深红的花朵缀满了花枝。平生看过的花很多,常常感动于它们的美或伤感,这一树花却让我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强韧的力。种树的人没有想到,本是寻常灌木的木芙蓉会长这么高,把它种在了墙角,贴墙贴得太近了,根本不能舒展它的根与干。有天晚上,我用手机的电筒光仔细地看它,才发现它长在一片宽可一米的狭长而逼仄的空间里,根部丛生着五六根粗壮的树干,除了两枝以外,皆被锯断。那一刻,我的心里似乎发出了一声惊呼。这棵木芙蓉却不以为意,硬是紧贴着水泥墙,伸展着繁茂的枝叶。主干向上伸展,但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电线,于是主干被砍掉。它的侧枝向西面伸展,遇到电线杆的阻碍,为了不使其搅扰电线,侧枝被狠狠地沿着墙头拉下来,向下低垂着。东边的侧枝,正对着路灯柱,也被锯断,整齐的锯口还很新鲜,一架梯子仍留在原处。这是一条幽僻的小路,却常有那种车厢很长的大拖车或大货车停靠,司机们跷着腿耍手机,对着满树繁花视而不见。
木芙蓉属木槿属锦葵科,自古以来似乎就不太受人重视。在那本杂凑编次的《花史左编》中,明人王路很不屑地说:“槿篱,花之最恶者矣。”大概是花色浓艳、插种甚易的缘故。王路虽然征引了《成都记》中“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锦城”的记载,但他很有可能没有见过木芙蓉,不知道木芙蓉有草本、灌木、乔木之别,对相关花事的知见也很有限,也不可能知道木槿是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国花。《花史左编》引了王安石的那首《木芙蓉》:“水边无数木芙蓉,露染胭脂色未浓。政似美人初醉著,强抬青镜欲妆慵。”《半山集》中此诗属于下品,落入美人喻花的俗套。柳宗元的《木芙蓉》要好得多:“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风露繁。丽影别寒水,秾芳委前轩。芰荷谅难杂,反此生高原。”这首诗应当作于贬谪永州期间,天地万物在孤寂者的眼中都被象征化了,木芙蓉只是一个聊供驱遣的符号,不俗之处在于它的“孤秀曾无偶”以及“谁能政摇落,繁彩照阶除”的清孤之美,在于它的“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的安穷自守、不妄自菲薄,在于菊花落尽之时拒霜而放,而不是像荷花那样身处繁华之地、炎热之时。
自秋徂冬,我常常在晚上独自去看那株木芙蓉。人们常说木槿晚上就闭合了,木芙蓉到了晚上依然盛开。它的花儿先是白的,渐变为粉红,再变为深红,皆为重瓣,大概是那种比较稀有的“三醉芙蓉”。站在树下,彷徨左右,迷离于大地的风、月光、诗与现实之间,仿佛可以听见那不可听之物,看见不可见之物。在这个大都市里,我们看到太多的树被砍掉了主干,苟且地发出旁枝,太多的花草靠装饰虚假的自然获得了生存空间,只有被观看、被砍削、被规定才能生存下来。一棵树、一朵花或一个人,皆是观念的产物,而非如其所是,“就像一条船在夜里/从海边拖走然后就不见了”—并非真的不見了,而是被修改了本质。甚至我有一种错觉:那棵木芙蓉就是一株现代柳宗元,一株华莱士·史蒂文斯—也许是最近在读后者诗集和传记的缘故。在许多人眼中,史蒂文斯在商界和诗歌界都很成功,似乎从容游走于二者之间。但是在保罗·马利亚尼的那本最新传记The Whole Harmonium中,那位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和大律师证书的持有者本该前程一片光明,但是一九○三年至一九○七年之间他在纽约的生活几乎可以用梦魇来形容,失业、困顿、抑郁几乎让他想用一把手枪结果掉自己。他一心想从事诗歌事业,却被自己的父亲粗暴制止,他想追求的女孩也被父亲嘲讽,他克制自己的欲望考取了律师证书却只能浑浑噩噩度日。坚硬的现实和未知的黑暗砍削着他,就像砍削一棵树。那段艰辛的生活,一直隐藏在他的日记与书信里,要一个多世纪时间流逝才被我们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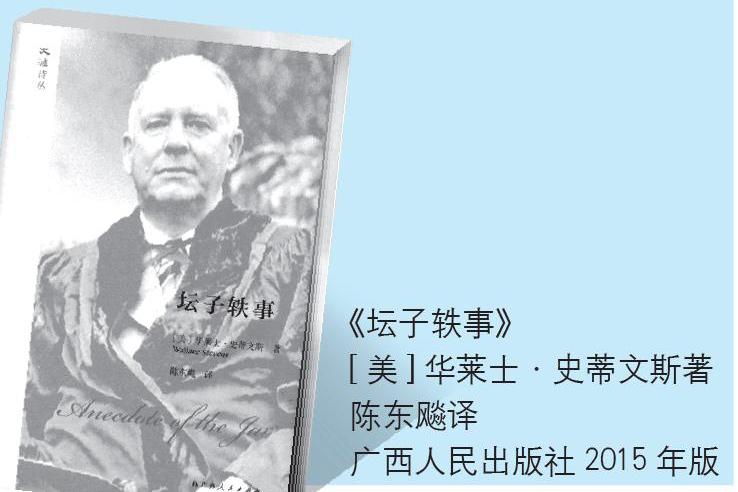
“人要有一颗冬天的心/来打量霜和盖着/雪壳的松树的枝干。”史蒂文斯在那首著名的《雪人》中写道。每个人都会迎来自己的冬天和雪,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电线、墙、锯子和梯子。或许可以说,柳宗元和史蒂文斯遇到的其实是同一场雪和同一棵木芙蓉,有的只是时间和地点的差别而已,自由的灵魂总是试图怀着冬天的心超越现实。
木芙蓉用花朵虚构现实,诗人则用想象力和词语。
四
每到春节,我总要买上一两盆水仙。去年的水仙尤其茂盛,有单瓣的,有重瓣的,密密匝匝开了两大盆,绿的叶子,白的花,黄的心蕊,和红色的盆子搭配相宜,很是壮观。据说养水仙要加矮胖剂,不然就会疯长。我厌恶各种药剂,不肯添加,只想让那两盆水仙由着自己的性子长,结果长得枝叶高大。起初还是挺直的枝子与花苞,开后不久便弯了下来。惋惜之余,只好将那些弯折的花儿剪下来,插在瓶里,居然也可以看上一段时间。也许我养的那两盆水仙是长得最恣情纵意的。
十几年前,我在莘庄的疏影路上住了四五年。“疏影”这个路名很美,得之于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周围还有几条路也是由这两句诗得来。过春节的时候,我爱买一两盆蜡梅,放在阳台上或桌子上,于是整个冬天便弥漫着蜡梅特有的香气。我对蜡梅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记得小时候父亲养了一株蜡梅,枝叶都不是很美,也无人把它当回事。到了冬天生了火炉,便把它搬进屋里,春节前后开花,真的是像蜡制品一样,晶莹黄润,香气扑鼻。故乡无梅,我以为古人所说的梅花就是这一种,自然是误解。然而在上海买的蜡梅只能活一个冬天,花期一过,便渐渐枯死,或者虽然活着,第二年也不再开花,不知什么原因。莘庄的梅园是有名的,我也去看过几次,像是圈养的,不够自然。我素来厌恶《病梅馆记》所说的那些病梅,也不喜欢那些过度修剪的植物,总觉得莘庄梅园的梅花比不上邓尉山的梅花—那些花缘山而栽,上下高低,偃蹇起伏,更为顺适其性。
疏影路上没有梅花,却有一棵高大的蜡梅。有一年冬天,我坐公交车上班,但闻得香气蓊蓊郁郁,回转身来,才发现有棵高大的蜡梅,平时竟从不曾留意。那棵树被两三米高的墙和房屋封闭起来,中间的空地仅有五六平方米,完全没有被人修剪过,各种枝条尽情伸展,叉叉丫丫,繁密异常。花盛时,馥馥郁郁,黄灿灿的,香味传得很远。枯萎的花,一半落在墙外的马路牙子上,一半落在墙内,寂寞地萎落泥土,化为春泥,滋育老树。《花史左编》云:“(蜡梅)凡三种,以子种出,不经接。上等罄口,最先开,色深黄,圆瓣如白梅者佳,若瓶一枝,香可盈室。楚中荆襄者最佳。次荷花瓣者,瓣有微尖。又次花小香淡,俗呼狗英蜡梅,开时无叶,叶盛则花已无。”那似乎是一棵罄口蜡梅。
每到冬天,一二百米外都是蜡梅的香气。最近重新去了一趟疏影路,乐购搬了,几家熟悉的餐馆也没有了。时间很紧,没来得及看看那棵蜡梅,不知道还在不在。
我常常想,这世上并没有绝对抽象的绝对之物或纯粹的存在,“棕榈站在宇宙的边缘/风在枝叶间缓缓移动/鸟儿垂下火焰的羽毛”不过是对纯粹存在的虚构,我们拥有的永远只是关于记忆、阅读、气味、视听的片段或碎屑,但它们往往比宏大的体系更真实。如同蜡梅、木芙蓉、水仙花、香橼一样,我们试图在现实的圈囿与弃置之中突围,在误解中突围,在寂寞中突围,在碎片里铭写废墟的完整和永恒,在自由的想象、写作、考据中拼凑出理念的花园—这是一种本能的原动力。
令人沮丧的是,那棵开满繁花的树前几天再次被锯断了,被拉到地面的那巨大的枝干被锯断,旁逸的斜枝被锯断,五六个锯茬白得耀眼。只有那向上的弱枝保留下来,在寒风中冷漠地摇动,但依然有两三朵花寂寞地开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