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应物像
韦应物像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滁州西涧》
在文坛上,很少为了一首诗,争夺冠名权而打起笔墨官司的。唯有韦应物这首《滁州西涧》所说的“西涧”,到底属于什么地方管辖,却引起了争论。王士禛说:“西涧在滁州城西。”不过,他也说:“昔人或谓西涧潮所不至,指为今六合县之芳草涧,谓此涧亦以韦公诗而名。滁人争之。”(《带经堂诗话》)据闻就在前几年,两个邻近的州县,也因为韦应物所说的那条西涧,到底应隶属哪县哪区管辖而争论不休。
我没有到过滁州,更不知道这涧在什么地方。不过,小时候,倒知道滁州的风景不错,因为背诵过收在《古文观止》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名篇说:“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我不知道韦应物所说的那条西涧,是否就是欧阳修所说的“酿泉”?就这诗的命名来看,所谓西涧,不过是说它在滁州的西边,也许是一条连名字都没有的溪涧。在唐代,这溪涧还可以行舟,可以通往附近的河流。但它应与“酿泉”有所不同。“酿泉”之侧,“有亭翼然”,欧阳修可以在那里请客饮酒。但韦应物所说的西涧,却是比较荒凉的去处。在涧边,还有野渡。到如今,沧海桑田,这山涧不知是否存在,但千百年来,滁州早就被一诗一文擦亮了招牌,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史上的异数。尤其是韦应物的诗,区区二十八个字,描写的又是野外一处很普通的溪涧,竟能起到如此轰动的广告效应,吸引了历代众多的诗人墨客,这实在匪夷所思。正因如此,更值得我们认真探索它的奥秘和艺术价值。
《滁州西涧》是韦应物的代表作,这首诗,似乎写得闲散平易,但韦应物一生,却过得很不平淡。他出生于公元七三一年,卒于七九一年,经历过唐玄宗、肃宗、顺宗、代宗等帝王执政的年代。这一时期,政治气候风云诡谲,社会动荡,更是唐王朝由盛变衰的历史性时刻。
据知,韦应物出生在贵胄之家,《旧唐书》说:“议者云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在世家光环的照耀下,韦应物在十五岁时,便当上唐玄宗的御前侍卫,一直当到二十岁。这段时间,他显赫得很,也荒唐得很。据他后来回忆:“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更可恶的是,他还“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他赌博淫邪,为非作歹,连他自己也承认是个骄横霸道的恶棍。可是,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垮台,树倒猢狲散,他便哀叹:“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逢杨开府》)他的生活,一下子从天上跌到了地下。
社会和命运的巨变,让韦应物的人生观、价值观起了彻底的变化,他很诚恳地说:“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并后悔“读书事已晚”,决定“把笔学题诗”。后来,他写诗的兴趣一发不可收,竟成为著名的诗人。宋代的评论家范季随说韦应物的诗:“清深妙丽,虽唐诗人之盛,亦少其比。”(《陵阳室中语》)促成他思想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正是在安史乱中和乱后,看到了人民生活的痛苦,看到了“空城唯白骨,同往无贵贱”(《睢阳感怀》)的惨况,感受到了“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廣德中洛阳作》)的凄凉。这让他遽然梦觉。火与血的经历,唤醒了他的良知,洗涤了他的灵魂。其后,他做过几任地方官,看到了人民被压迫、被欺凌的种种情况,也常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却反受到权贵的诽谤和迫害。他几次辞去官职,退隐不仕,但有时身不由己,被命复出。传统拯民于水火的理念,以及生计的困窘,让他一次又一次踏上官场。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他被任命为滁州的地方官。
韦应物当官,是比较注意亲民的,他说自己:“出入与民伍,作事靡不同。”(《答畅校书当》)在滁州,他当了一年多的刺史,也想有所作为,但看到景象荒芜,无能为力:“风物殊京国,邑里但荒榛。”(《答王郎中》)他看到了人民艰苦地耕作,仍是“仓廩无宿储,徭役犹未已”。他知道这很不合理:“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总结了自己一生为官种种不堪的遭遇,只能悲叹:“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吏,能够认识到俸禄来自民众的供给,这样的反思实属深刻和难得。他一直想为百姓解决困难,却一直受到诸多掣肘。他想过甩手不管,又不忍拂袖离开。总之,长期以来,他想退隐不仕,希望身心宁静,远离尘俗。而现实的处境,又让他身不由己,进退两难。
《滁州西涧》一诗是韦应物在出任滁州刺史时,或任满赋闲在滁州稽留时写的作品。
诗名“滁州西涧”,写的也是西涧的景色。在滁州,韦应物是经常到西涧的,也写下不少和西涧有关的诗,像《西涧即事示卢涉》《西涧种柳》《乘舟过西郊渡》《再游西郊渡》《简寂观西涧瀑布下作》等。有些诗,还写到他在西涧的活动,像“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观田家》)、“日夕临清涧,逍遥思虑闲”(《郭区言志》)等。看来,他对滁州城外的这条西涧,是有着特别的感情的。
现存韦应物的作品近六百首,然而千古以来,最为脍炙人口的,却是《滁州西涧》这首似乎是纯粹描写西涧的风景诗,而且似乎是写得萧散冲淡、语不惊人、区区四句的七绝。
这首诗,以四个画面描写滁州西涧的景色。按理,西涧应有许多景物可以描写,例如附近的瀑布。在《寄全椒山中道士》一诗中,韦应物还提到“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落叶满空山”之类,起码这里有的是飞流、云树、岩峦、空山、落叶。但是,当韦应物描写西涧的景色时,他首先着墨的,却是涧边的幽草。幽草不是鲜嫩优美、青翠欲流的小草或芳草,而是生长在涧边芦蒿之类的野生植物。它们密麻麻、绿油油、乱糟糟,自在地茁长成活。它自生自灭,并非有人着意栽培。西涧岸边,有浓密的幽草掩映,显得宁谧疏放,自在自然,让周遭充满着泥土气息的野趣。

老实说,溪涧之边,幽草丛生,这景象十分平常,况且,韦应物也没有着力刻画这幽草的形态,只用一个很普通的“生”字,说明幽草的生长和存在。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这首句之首,作者即下“独怜”两字。“怜”,是怜爱、喜爱的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强调,这“怜”,是“独怜”,是他唯一的排他性的钟爱。在这里,韦应物面对这很平凡很自然的客观景象,却鲜明地强调自己的主观感受,这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且,这诗的开始,即以“独怜”领起,它便贯串全诗,表明诗人最喜爱的,正是诗中所提到的种种图景。
诗的第二句是“上有黄鹂深树鸣”。诗人写黄鹂鸣于深树,至于这里的树是什么树,他没有说,只说这里有一大片树林。浓密的枝叶,成了黄鹂的安乐窝,可以任由鸟儿得其所哉,自然鸣叫。它们是怎样“鸣”,诗人也没有写。但他特别点出,这鸟儿是黄鹂,也另有一层意味。在《听莺曲》一诗中,韦应物曾写道:“流莺日日啼花间,能使万家春意闲。”流莺是指黄莺,黄莺即黄鹂,显然,韦应物一向觉得,黄鹂的啼唤会给人“春意闲”的感受。而且,鸟鸣则山更幽,黄鹂的鸣声也衬托出西涧的幽静。
这一句,写的既是一幅涧岸的图景,而又和上句有着联系。因为诗人特意在这句之首,点出“上有”两字,这表明“黄鹂”的“深树鸣”是在涧边幽草之上。于是,西涧的景色,上上下下,连成一片,从而透露出整条西涧幽闲宁静的意蕴。再者,从黄鹂的“鸣”,韦应物也透露他在西涧观望景色时,还是晴天。因为只有在晴天,鸟儿才会啼鸣。总之,诗人不着痕迹地表明:下雨前这里静悄悄,他在这里从天晴待到夜雨。
这诗第一句和第二句,有什么独到之处吗?老实说,没有。韦应物只是以平易的笔墨,描写滁州西涧很平常的景色。如果要说这两句诗有什么值得咀嚼之处,就在于诗人首先就声明,他最喜爱的,恰恰是这里最普通最平易的郊野风光。
第三句,诗人把笔触转到写涧水:“春潮带雨晚来急”。春天,潮水涨满,加上阵阵的雨,天上的雨水和涧里上涨的潮水汇合起来,水势更大,水流转急。这时天色已晚,四下昏暗,周遭一片寂静。而雨声水声,哗啦啦地直响,打破了昏夜里无声的寂静,却又让人感受到这杳无人迹的西涧,显得更加寂静。请注意,韦应物在这幅雨中西涧的图景里,以“晚来”亦即以昏黑的夜色为背景,又以“急”字描写水流湍急的状态。虽然也和上面写到的涧边草生、深树鹂鸣一样,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但是,由于诗人以“急”字形容涧水的流势,而不用“晚来涨”“晚来畅”或“晚来满”之类的写法,这一来,西涧的夜晚,在寂静中,又带有空漠、凄清和不安定的气氛,呈现出另外的一种野趣。
元代的杨载在《诗法家数》中指出:“绝句之法,要婉曲迴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又说:“至于婉转变化之功,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这是杨载总结前人创作的经验之谈。这说法,类似所谓“起、承、转、合”,它无非是指主客观事物的矛盾必然有开始、发展、转化、结束这几个阶段。绝句虽然是短诗,也要表达诗人思想感情以及观察事物视野转变的过程。否则,一览无余,缺乏变化,必然让人感到乏味。这就是杨载所说,绝句的第三句应“要婉曲迴环”的原因。
韦应物在《滁州西涧》的第一、第二句,写了西涧的静态。在第三句,诗人便转过笔锋,突出描写这条西涧的动势。那春潮,夹着雨水,汹涌而来,让人看到那股不可遏止的动力。在“带雨”和“晚来急”的气氛中,让审美受体听到雨声沙沙,看到流水滔滔,而四野无人,只剩潮声、雨声,格外显出荒野的空寂。特别是,韦应物把“急”这一入声字,用于句末,“入声短促急收”,在声调和语势上,都会给人增添强烈的动势而又萧瑟幽冷的感悟。可以说,这是诗人以动写静的一幅图景。
据《唐诗品汇》引述谢枋得的意见:“‘春潮带雨晚来急,乃季世危难多,如日之己晚,不复光明也。”谢枋得这穿凿附会的看法,受到了许多人的讥笑,甚至被认为不懂诗,是在痴人说梦。当然,把韦应物对景色的描写,牵强地和政治扯在一起,实在荒唐可笑。
但是,我认为,谢枋得注意到“春潮带雨晚来急”这幅画面,它所描写的景象和作者流露的情绪,不同于这首诗前边的两句,不能不说他独具只眼。不错,这《滁州西涧》的第三句,和第一、第二句一样,都是写西涧的景色,而且这一切也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但是,写涧中潮水、带雨急流,确和前面两句那种幽静宁谧的描写有所不同。纵观韦应物的诗作,他是写过对夜雨的感受的,像《幽居》说:“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这种写夜来听到绵绵春雨的心情,与“幽草涧边生”“黄鹂深树鸣”的韵味就颇切合。然而,韦应物在《滁州西涧》的第三句,写的却是潮急雨骤,分明是另外一番景象。这一点,连批评谢枋得的沈德潜也是觉察到了的,他也认为《滁州西涧》:“起二句与下半无关。下半即景好句。”(《唐诗别裁》)其实,这诗的第一、第二句,怎能与下半“无关”?沈氏的评说,当然是片面的。但是,沈德潜毕竟看到这诗上半与下半有不尽相同的一面,这也不能不说他颇有会心。我认为,如果把这首诗的几个画面,视为诗人只为写风景而写风景,看不出他在写景中抒发感情的复杂性、多样性,反而是比较浅层的理解。
在春潮带雨、溪流湍急的情况下,韦应物引出了第四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句诗,历来被人们传诵,备受赞扬,但对它的理解并不一样。也许,一些人未必理解韦应物描绘这幅画面的真谛。不是传说有人把这句诗作为画题,让画家们去畫吗?于是,有人画了一条船,船头有小鸟站着,表示船上没有人,所以鸟儿可以在船上歇息;又有画家画着船上有人,这人是舟子,他斜躺在船上吹笛,表示无人需要渡河,舟子闲得无聊,便吹笛自娱。据说,后者强调“闲”的画法,更受到人们的嘉许,认为它符合画题的神韵云云。当然,如果单抽出这句诗,孤立地作为画题,画家和评论者着眼于“闲”,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把韦应物《滁州西涧》整首诗所要表现的意趣联系起来,那么,强调无人,或者强调悠闲,却是胡扯。
要知道,韦应物写“野渡无人舟自横”,是“春潮带雨晚来急”带来的景象。它的前提,是夜雨连绵、潮水湍急。野渡,是荒村的渡口,本来就很冷落,没有多少人来往。在雨中的夜晚,没有人冒雨出行,那系在涧边的野渡用以载客的小船,更是无人问津,连撑船的舟子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于是,这空无一人的小船,便在河溪上受到涧水的冲湍,横在溪涧中,晃晃荡荡。不错,表面上,这种景象是“悠闲”的。但是,在暮色昏暝,夜雨连江,独有这只空荡荡的小舟,在水面上横过来,横过去,可怜巴巴,任由风吹雨打。显然,与其说它单纯地表现“闲”,不如说,它在摇晃中又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和萧瑟清冷的情调。
这首诗的前三句,如果从摄影的角度看,韦应物的艺术构思也是微妙入神的。他入眼的前三幅画面,都是滁州西涧的全景或中景。而在第四句,却出现“舟自横”的特写镜头,这也怪不得人们对它特别注意。在夜色迷蒙中,一条无人的小船,横躺在溪涧中,随着潮水摇荡,这画面确实很能表现出荒郊野趣,也从来没有诗人捕捉过这样独特的画面。
问题是,为什么韦应物会特别喜爱并且着意描写滁州西涧这种野趣,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思考。
在第四句这最受人注目的诗句里,“舟自横”的形象又是其中点睛之笔。试问,潮水急涌而来,势如奔马,那无人的小舟,怎么没有被冲走,而是自己“横”在水中呢?这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在下雨前,舟人是把船的一头紧系在岸边。当受到潮水冲碰,水势时急时缓,小船也就靠在岸边摇来晃去,没被漂走。从对岸看过来,它不就是“横”靠着吗?一是舟人把船杆竖直,固定在河床中,用绳索绑住船舷。这样,潮去潮来,小舟依然独自“横”在水面上摇晃。总之,尽管春潮汹涌,这空无一人的小舟,没有随波逐流。看上去,还颇似悠然自得。当然,无论小舟是怎样地“横”,它也绝非横亘不动,而是在水面上摇摆不定。这句诗,紧接着第三句,也是以动写静,进一步描绘滁州西涧呈现出自然而然的野趣。可是,在昏黑的夜色里,在渺无人迹的野渡,在春潮的推涌中,这小舟无人料理,孤孤单单,可怜巴巴,任由颠簸,又让人在寂静中,感觉到它的无奈与无助、孤独与凄清。
以上四句诗,是各自独立却又互相联系的画面。在第一、第二句,韦应物写白天涧边之景,第三、第四句则是写晚上涧中之景。这种种景色,有所变化,是郊野寂静的自然生趣的概括,诗人以淡淡的笔触写来,就像在读者面前铺开了一幅水墨画,正如清代黄淑灿说:“闲淡心胸,方能领略此野趣。所难犹在此种笔墨,分明是一幅画图。”(《唐诗笺注》)
确实,以“闲淡心胸”看待事物,是韦应物表现思想感情重要的一面。我们发现,他的诗作往往喜用“自”这一辞语。像“百草无情春自绿”(《金谷园歌》)、“芳树自妍芳,春禽自相求”(《拟古诗其二》)、“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见《咏声》)等。所谓“自”,有着自然而然的意味。凡属顺应事物自身的发展,没有人为的、刻意的追求,就是他说的“自”。《滁州西涧》写幽草在涧边生长,写黄鹂在深树啼鸣,写春潮带着夜雨在流湍,包括“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一切,是郊野中自然地表现出的生态和环境,诗人把这些画面组合起来,表现出郊野天然的、自由自在的意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野趣”或“天趣”。
不过,《滁州西涧》这首诗独特之处,是作者在闲淡心胸中,又流露出一丝无奈的情怀;在描写自由自在的景色中,也表现出一些并不自在的痕迹。韦应物在写了滁州西涧各种空寂的景象以后,把目光聚焦到“野渡无人舟自横”之句。那无人理会的小舟,在幽涧里不得已地打横浮着的画面,便隐约地透露出诗人心中不自在的愁绪。由于“野渡无人”,一舟自横,这“自”字,便隐含着独自、孤独的韵味。不错,小舟横浮,似也悠然,但是,它在春潮夜雨中,被系在岸边,固定在涧中,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状态。在韦应物看来,不系之舟,才是最为自由自在的,他说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又说过:“为报洛阳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所谓“扁舟不系”,语出庄子:“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列御寇》)韦应物所艳羡的人生状态,是能像没有被束缚的舟船一样,随意浮游。因此,他在滁州西涧看到那小舟被系,不为人用、独自横着的情景,其实是另一种孤寂无聊的野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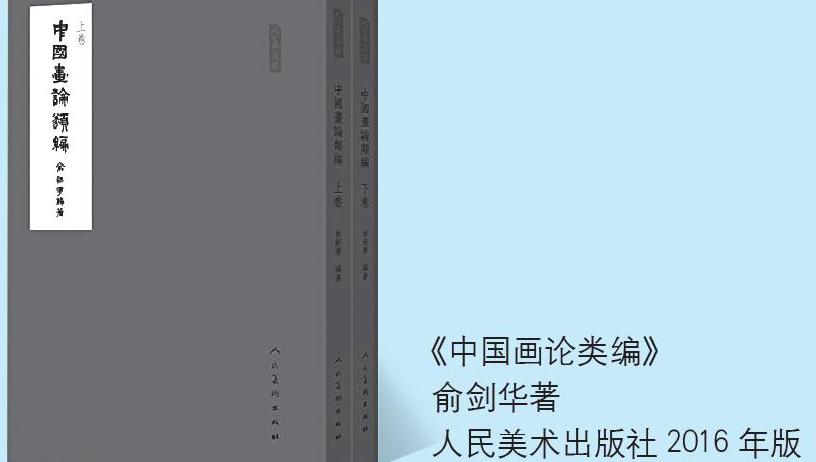
韦应物以冲淡的笔墨,不加雕琢地描绘滁州西涧的画面,这是许多人都能领会的。其实,这首诗的艺术构思,又是精妙入微的。作者在第一、第二句,先在读者面前铺开西涧的静景,再在第三、第四句,以动景来表现西涧的静景,两种不同静态景色的结合,构成了《滁州西涧》这首诗独特的意境。特别是,诗人以雨夜潮急的背景,衬托那在涧中无人自横的孤舟,这静景又融入了冷意,耐人寻味。据知欧阳修也很喜欢这首诗,甚至在《采桑子》一词中,还照搬其中的一句:“残阳夕照西湖好,花坞苹汀,十里波平,野渡无人舟自横。”我们很难说欧阳修的词写得不好,但袭用了韦应物的这句诗,韵味则大异其趣。在夕照中,在花光苹影里,岸阔潮平,那船儿横躺在镜子般的湖水里,只显出西湖的优美。把这样风雅的图景,说成“野渡”,实在不很贴切。由此可见,只有把《滁州西涧》的前三句,和“野渡无人舟自横”联系起来,才能够理解这首诗独特的意趣。
《滁州西涧》是一首山水诗,写的是自然界的风景。自然界形体、线条、色彩所呈现的审美形态,是客观的存在。但诗人选择什么角度,观察什么事物,如何展开视野,如何理解客观的自然景色,却和他主观的思想感情有关。简言之,山水的客观形象刺激了人的大脑,启動了情感之泉的阀门,触发了贮存于上皮细胞中的文化沉淀。刘勰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石涛也说:“山川使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余也,余脱胎于山水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神遇而迹化也。”(见《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53页)作画与写诗,道理是一样的。诗人写景物,不能不受自然界客观形体线条颜色的制约,同时又以自己的心境观察自然界。因此,在诗人笔下的自然界的形象,往往是他心境的投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