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雨果·克劳斯的出生地,比利时的布鲁日
雨果·克劳斯的出生地,比利时的布鲁日雨果·克劳斯(Hugo Claus,1929-2008)的小说《比利时的哀愁》,中译七百五十八页,一部“史诗”级别的大厚书。第一印象是结构好像不那么考究,让人觉得是在翻阅刚从作者的手提箱里取出来的厚厚的一大沓札记。作者像是出于纯粹的写作冲动,记录童年和青春期的往事,叙述和笔调似乎少了一种腾挪变化。
小说分成两部:第一部的标题是“哀愁”,共分二十七章,每一章都有标题;第二部题为“比利时”,不分章节也不加标题。为什么第一部分章节加标题而第二部不分章节也不加标题,原因是不清楚的。就叙述本身而言,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看不出什么区别;这就更让人觉得这种前后的处理有点像是出于权宜之计。
我怀疑,雨果·克劳斯是仔细琢磨过小说的结构问题的,可能是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案,就只能这样来写了。或者说,诗人和小说家不同,诗人在更为精致的体裁中耗费心血,写作散文时反倒倾向于自由而质朴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结构上往往不那么精心。但更恰当的解释或许是,诗人雨果·克劳斯像《天使望故乡》的作者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沉溺于五彩缤纷的印象和细节,怀抱书写一方世界的冲动和野心,没有耐心去等待和谋划,便鼓起修辞的风帆、激情的炉火,在汪洋的记忆中载浮载沉,几乎被海量的细节所吞噬……
 雨果·克劳斯(Hugo Claus,1929-2008)
雨果·克劳斯(Hugo Claus,1929-2008)是的,雨果·克劳斯就是比利时的托马斯·沃尔夫。他是一个吞噬生命的人。
《比利时的哀愁》写的是“二战”前后的比利时,比利时弗拉芒语区,主人公路易斯生活的小镇瓦勒,路易斯外婆家的小镇巴斯特赫姆,还有他的寄宿学校所在的西佛兰德省,等等,套用福克纳的话说,作者写的是地图上邮票那般大的故乡(比邮票其实小得多呢)。那还是教会控制国民教育的时代,是四轮马车和蒸汽火车并存的时代,是小镇的风俗尚未被发达的通信技术稀释而全球化的微风已经吹拂的时代……简言之,是凡事都从乡土社会的窥视孔瞭望,但年轻人开始喜欢美国的电影和爵士乐的时代。诚如少年主人公从寄宿学校回到家乡瓦勒小镇时的感受:
路过菲利克斯的理发店时,他走得很快,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会不会有脸上挂着剃须肥皂水的高嗓门大猴子冲出来和你握手,打听学校宿舍和妈妈的一切可能的私密信息。在宏泰斯,一个纺织厂老板家门口的篱笆边上,他尽可能地跳到高处,往花园里看去。在屋顶平台上躺着一个女人,直接躺在地板砖上。她就戴了一顶草帽,挂着一串珍珠项链,此外一丝不挂。……他穿过了彤杰斯大街,这里住着靠国家福利生活,把所有的钱都花在酗酒上的一群无赖,女人们抱着长满疥疮的孩子坐在门槛上。这条街居然离圣安东尼教堂这么近,真是永恒的羞耻。那些人只要不是受到警察追捕,根本就不会踏进教堂。路易斯嫉妒地看着四处飞跑,嗓音成年人般粗哑,耳朵和睫毛里粘着煤炭的男孩儿们,他们正在踢一个用纸和细绳做成的球,一边大声叫嚷着骂人话。虽然他知道这是重罪,可他还是远远地望着他们,让自己感染他们的罪……
我们在阿兰-傅尼埃的小说和费里尼的电影中也见过此类场景,它们是从作者记忆的宝库中提取的,含有童年的被囚禁的意识,以及伴随这种囚禁感的微微開启的一瞥。故乡的一种含义也就体现在这里:所谓的“重罪”之感或秘密的犯禁也都是发生在一家三代人的祖屋周围,在“父母结婚、自己受洗的教堂”的阴影底下。成年人的罪孽带有孩童色彩而孩童的罪孽则是永恒的返祖现象,构成一座微型的亚当和夏娃的乐园。仿佛时代的灾变和战争的风云永远都是外来的—拿破仑的骠骑兵或纳粹德国的坦克师,突然间跨过金色画框的国境线,要将这幅田园小镇的风俗画撕个粉碎。
在评论雨果·克劳斯的一篇文章中,库切认为,这位比利时作家的诗歌创作具有“独特的荷兰式视域”。文中定义说:
他秉承罗尼穆斯·博斯的精神,思考被践踏的祖国,回到充满童话寓言故事和格言式谚语的中世纪末民间想象力,博斯也正是凭借这想象力来建构他眼中的疯狂的世界。
库切在文章结尾处又修正道,虽说雨果·克劳斯的诗风“清新而尖锐”,但他不是“伟大的讽刺家或警句作者”,而是“以才智和激情的非凡糅合而瞩目”—这个修正是必要的,使得定义趋于精准了。上述评价如果移用到雨果·克劳斯的小说创作上,也应该是贴切的。我想略微展开解释一下。
 《比利时的哀愁》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 2020 年版
《比利时的哀愁》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 2020 年版所谓的“荷兰式视域”,是指专注于风俗和日常生活的视觉呈现。这一点正是《比利时的哀愁》的特质。这部小说丝毫不像罗尼穆斯·博斯的“寓言画”,画上骷髅成堆的恐怖,那种末日的死亡景象,总之是颇为怪诞和刺激的。《比利时的哀愁》不具有“寓言画”的超时间的性质和怪诞讽刺的色彩。它是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的风俗画,嚣骚、幽默、乐生、坦诚,是描绘“二战”前后弗拉芒语区的一幅历史长卷。
小说以战争为背景,却不写大事,不侧重悲剧。我们看到小镇的众生相,婚丧嫁娶、饮食男女,和别处似乎并无差别。我们看到修女主持的寄宿学校,男生的秘密社团“使徒会”;我们看到路易斯的祖父家和外婆家,布尔乔亚市民每日上演的剧目,包括战时的表现,透出张爱玲所说的那种“兴兴轰轰”的劲儿,在“被践踏的祖国”,他们打牌、吹牛、通奸、吃喝、恋爱、争吵……我们看到,在一幅人物众多的大型风俗画上,每个人物都是主角,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每个故事都像雨点落进大海,加入循环。这幅日常生活的画卷是一种巴洛克风格的描绘,信笔挥洒,泼辣生动。海量的细节令人沉溺。叙述如此丰富,富于谐趣。语言和结构并非如我们第一印象所认为的那样有欠考究,而是像鲁本斯的巨幅画作,斑斓之中有着细致浑厚的肌理。
二
这部描绘特定时代和风土的巴洛克风味的“成长小说”,让人想起“二战”后涌现的一些创作,也都采用家族编年史的框架,如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萨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等。在这些长篇作品中,孩童的视角被置于一个突出的位置,显得有些过于早熟和孤独,这一点迥异于传统成长小说的模式;它是受到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对成人世界采取一种怀疑、抵制和不合作的态度,以桀骜不驯的声音主宰叙述。这种叙述从一开始就是自我分裂的,奇怪地睿智,奇怪地清醒,奇怪地天真,同时也导向某种综合。换言之,它总是呈现一定比例的奇幻和一定比例的写实主义,总是渗透孩童的梦幻和视觉,以及富于洞察力的艺术家的那一份悲悯和幽默。
这个主人公兼叙事人看到的世界,因而是一个热切的关注和旁观的距离所造成的喜剧性世界。也就是说,即便是严肃的、接近悲剧性的内容,也会以福楼拜的那种细致冷静而不乏轻谑的笔触展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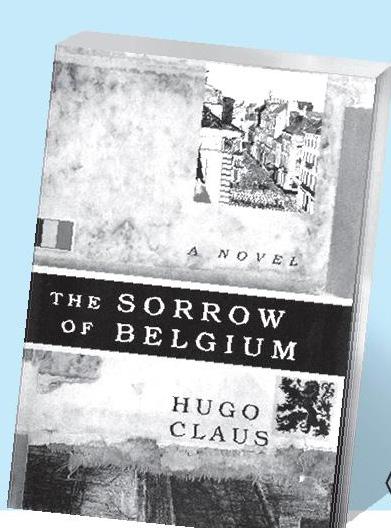 《比利时的哀愁》英文版
《比利时的哀愁》英文版突然,路易斯透過灌木丛看到了他母亲。她穿着一套他从来没有见她穿过的优雅的米色套装。她也和他一样,是在别处换的衣服?在艾尔拉工厂里?她用一把闪闪发光的金属勺子舀了榛果冰激凌放进嘴里,她转着舌头舔掉一半这个绿甜品,同时把这把发光的勺子送到了一个男人的嘴唇边,一个四十多岁,短头发,长鼻子,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的男人。这个男人用牙齿夹住勺子,妈妈大笑,试着拔出这把让男人变成长嘴鹭鸶的金属短棍。
路易斯撞见母亲和她的德国老板有染,这个场景获得细致有序的描绘。书中这样的描写不胜枚举,通过一个孤独的孩童的声音,似在提出这样的问题:
面对生活的真相或耻辱,该用怎样的语调和语言报道见闻?尤其是这种生活的耻辱不可避免地要和历史的耻辱掺杂在一起,即,身为比利时的中产阶级的儿子,不仅要在战争年代,而且要在和平年代或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去面对自身的历史,面对被压抑的弗拉芒语的梦呓,诸如此类,一个自诩为年轻艺术家的孩子该如何去做出反应?
《比利时的哀愁》以其尖刻的质疑提出这样的问题。本来这只是一个有关艺术家成长的故事,而当故事被置于历史语境加以描绘时,有关国族/乡土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思考就成了一个必须正视的课题。
比利时是欧洲的小国。且不说北部弗拉芒语区,即便是整个比利时,夹在强大的德国和法国之间,也不过是一条随时都会被穿透的走廊。正如俄国作家阿·弗·古雷加指出,“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其历史生活的组成部分”,比利时的地缘状况造就了它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和现实的处境。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它一会儿被日耳曼人梳妆打扮,一会儿被法国人调教熏染;处在两大强权的拨弄之下,其脆弱的独立性总是岌岌可危。雨果·克劳斯的小说不仅写出了那种显然薄弱的独立性,并且牢牢把握住“小国寡民”的全景透视画的基调,即投注于那片弱小的故土之上的真实的悲悯和幽默。
小说的标题叫“比利时的哀愁”而不叫“路易斯的哀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了。该篇的语言(视角和基调)促使我们去思考小说的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有赖于复杂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析,它涉及历史意识、精神存在和个体自由等命题。虽然艺术的自由绝非等同于主观性的任意增长,但对主体性的思考无疑有助于视角的确立。
 《午夜之子》[ 英 ] 萨曼·鲁西迪著刘凯芳译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5 年版
《午夜之子》[ 英 ] 萨曼·鲁西迪著刘凯芳译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5 年版通常说来,小国家的历史总是会让它的子民伤透脑筋,因为无足轻重,因为战绩不佳,因为那种连自己都看不起的无所作为,真不知该如何来叙述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然而,意义的问题却是不会因为这种弱小而被取消了追问的。至少在雨果·克劳斯笔下,个体独立性的意识被赋予极大的权重,仿佛通过艺术想象的努力,在诗性真实的意义上,这种个体的独立性就会给国族的独立性以有力的支持和承诺似的。
三
与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相似,这种将主人公变成“早熟”的思想代言人的处理难免导致叙述的此消彼长:小说在展示线性的“成长”主题时会弱化,在表现空间化的历史主题时则像多棱镜那样闪烁辉映。这是该篇的视角设置所决定的。路易斯作为人物是不够动人的,作为叙述视角则富于表现力。主人公已被同化为叙事人,被作者最大程度地利用。主人公被转化为深刻的叙述者,集经验、观察、反思和评判于一身。在雨果·克劳斯的小说中,这个视角既允许分裂也包含了综合,甚至让小说完成一种越界的交流或交互,也就是说,将作者清醒的历史意识与主人公朦胧的现实感交织,其结果是展开叙述的那个视角一半嵌入历史,一半超然于其上,从而编织出一幅虚实相间的“忧乐园”的图景。
与视角有关的这种空间化的叙述,决定了该小说的结构模态。我们第一印象认为缺少腾挪变化的结构,正是它营造的一种特质。这部小说细品之下是有点怪的,篇幅这么长,其叙述却不是被情节推进的。译者李双志在《那一场青春,有别样的烟火》一文中指出,小说“并没有向上的进步或向下的幻灭的线性叙事,而是如小说后半部的行文格式,沿时间轴线串联起的零散碎片拼合成斑驳迷离的个人兼家国往事”。这个说法颇有见地。所谓“向上的进步或向下的幻灭”的情节进程,无疑是成长小说或家族编年体小说的主导性叙述动机,而在雨果·克劳斯的小说中这个动机却被削弱了。其实,“向上的进步”的轨迹还是有的,小说结尾便可证明,但该篇的情节线从不提振,而是发酵出一个个五彩气泡似的东西。换言之,在摒弃常规动机的同时实现一种叙述的膨化结构。
上文提到的君特·格拉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萨曼·鲁西迪、阿摩司·奥兹等,他们的那些作品都没有这么做过;虽然就历史意识而言,他们和雨果·克劳斯是颇为接近的。这种空间化叙述或叙述的膨化结构,似乎最能代表雨果·克劳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构想。实际上,它并不是当代艺术家从事的新实验,而是欧洲小说在过去三个世纪里刻意经营的一种属性,即小说如何艺术化地处理“社会新闻”的属性。小说不是传奇。小说更接近于流言和琐事的报道。雨果·克劳斯试图把这种特性加以发挥,将其特有的塑化能力再作抟揉拉伸。
按照梅洛-庞蒂在《论社会新闻》(姜志辉译)一文中的观点,“社会新闻”都有其公开和隐秘的两个方面。小说依靠公开的社会新闻构筑情节和背景,但小说更喜欢揭示事物背后隐秘的细节;两者互为依存,而后者无疑是更加牵动社会敏感的神经。正如梅洛-庞蒂在文中指出,“需要掩盖的东西是血、身体、内衣、屋内的隐私、呈鳞片状剥落的绘画后面的画布、有形物体后面的内容、偶然性和死亡……”总之,这些有待于从隐私状态披露的事物,这份构建关联的隐喻式的清单,正是《比利时的哀愁》的空间化叙述的组织原则。它不是以长远、持续、起伏的情节线,而是以断断续续、像是掉了一地的零散动机组织叙述的。
 《铁皮鼓》[德] 君特·格拉斯著胡其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年版
《铁皮鼓》[德] 君特·格拉斯著胡其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年版我们讲过雨果·克劳斯对细节的沉溺。或许,把“细节”一词换成“小事情”会更恰当些。我觉得梅洛-庞蒂如下的论断适用于雨果·克劳斯的这部小说:“真实的小事情不必是传奇的和优美的”;“它可能是淹没和消失在社会过程中的一种生活”;“小说只能依据真实的小事情”;“小说利用它们,像它们那样进行表达,即使小说离不开编造,它所编造的东西仍然是虚构的‘小事情”。可以说,《比利时的哀愁》诠释了小说的一种定义,在梅洛-庞蒂阐释的意义上。它是一部由“小事情”敷衍而成的“史诗”。
从这些虚构的“小事情”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对生存的肯定。雨果·克劳斯喜欢被他描述的一切事物,尤其喜欢描述食物和衣料,气味和质地,喜欢视觉中构成形象和色彩的东西。这个膨化状的被描述的生活空间,散发出温暖、乐生的能量,具有心理的治愈力,证明历史虽不堪回首却总包含生存的努力和欲望,而这正是小说能够提供的一种超历史的价值。
《比利时的哀愁》名为“哀愁”,实质是一部喜剧。喜剧并不意味着严肃事物的对立面。一个喜剧性的逐渐解体的世界,也会成为生死转换中一切可悲可怜可叹可敬的人和事的纪念。文学是一种纪念小事情和小人物的仪式。我想,读过这部小说,我们不会忘记路易斯的父亲斯塔夫,那个嘴里含着糖果的印刷厂老板,不会忘记阿尔曼德舅舅、维奥蕾特姨妈和残疾的婆妈妈,更不会忘记路易斯的母亲,那个风月俏佳人,她的名字叫康斯坦泽(意为忠贞不渝),但我不认为这个命名是讽刺……
四
雨果·克劳斯是诗人、导演、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和评论家,是才华横溢的跨界多面手。在《内心活动》(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一书中,库切评论他的创作,将《比利时的哀愁》誉为“二战”后最伟大的歐洲小说之一,但库切的文章关注的主要是雨果·克劳斯数量庞大的诗作。
《比利时的哀愁》的出版,填补了弗拉芒语文学译介方面的不足。随着雨果·克劳斯的小说译为汉语,弗拉芒语区的文学景观便将和他一起进入我们视野,诗人圭多·赫泽拉、小说家赫尔曼·特尔林克等,这些我们感到陌生的名字在小说中频频出现。谈起“二战”后的欧洲文学,现在就不只是有君特·格拉斯、伊塔洛·卡尔维诺、费尔南多·阿拉巴尔等,还有雨果·克劳斯,足可与他们比肩的一个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