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宝光打电话给我说,他有一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旧书。我急切地说,送给我?第二天他送来了。居然就是这本《湘行散记》,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的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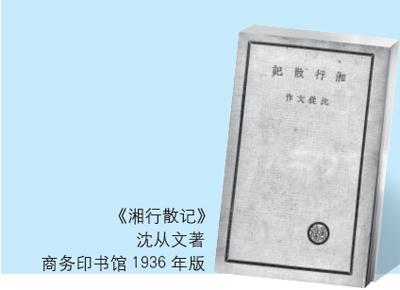
| 2 | 许多的小照片堆放在一起。挑选出来,给父亲母亲整理照片,制作了一本影集。此时,重返去真正阅读照片。有一张战时朝鲜的照片,四个人的合影,很有叙事感。个子最高的是父亲,也就二十多岁,着一身军装。对于这个画面我完全没有概念,有关朝鲜,父亲很少说起。他们四个人在合影,旁边的军人则很匆忙紧张地走动着。
突然觉得照片的魅力,仅在方寸之间,图像将这真实返回过去,暗示这真实已经逝去。照片只是一次“此曾在”。这张照片告诉我,父亲曾经在朝鲜。普鲁斯特说:“看着某人的照片,唤不起什么回忆,反不如凭空想念。”
一次在美国,巫鸿带着我去林肯大学的美术馆,看到几张尺寸都在4英寸×5英寸和8英寸×10英寸的早期照片,巫鸿说,照片其实就应该这么大小。几年后去英国,也有一个叫林肯的城市,有一个很小的美术馆。这个美术馆有个小厅,也挂着些小照片。影调非常迷人,俯看时候,洞开的风景里有人在躲闪,叙述什么?
小照片,可能是照片最好的方式。所有的大照片、超大照片也只有商业用途。
| 3 | 他被他自己发明的“此曾在”一词而羁绊。“此曾在”,对于一张照片的认识,实在伟大,没有任何一个词句,可以极其精确地道出照片之灵魂。罗兰·巴特不喜欢电影。他说,电影故事是虚构的,因此混合了两种定义,演员的“此曾在”和角色的“此曾在”。也因此他忍受不了,他用瞬间画面语言去定义电影,埋怨电影不能出现语言片段,并且被限制着照单全收。他说:“这是摄影的幽郁,当我听到死去歌者的嗓音时,也有同样的心情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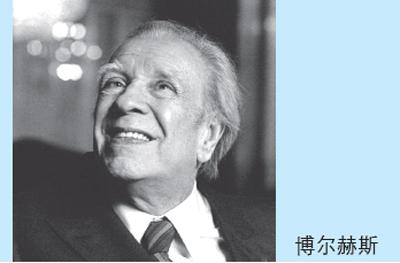
然后,他又觉得自己一厢情愿了,却又要做出一种反抗的姿态。我认同这样的姿态。面对互联网,也要做出反抗的姿态。但是,缺乏一种文法的模式,去叙说一套理论的价值,不带有一丝知识怀疑论的腔调。不过,我一点儿勇气也没有。
| 4 | 在张竹坡刻本《金瓶梅》里,也必须是要“苦孝说”,以掩饰这“秽书”之不名誉,也至今无从知晓其确切的作者是谁。“一切的阅读都暗示着一项合作,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一次同谋。”(博尔赫斯语)有几次,鼓足勇气,希望与曹霑同谋,均在贾政训斥宝玉时刻停止了。倘若,这是一次合作,却是合作不下去的。受不了贾宝玉的作死样儿。虽然同意,于“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一人而已”。同样的家族兴衰史,同样的肮脏生活里,同样的丑陋社会中,《金瓶梅》却尔虞我诈,敢爱敢恨,剑拔弩张,充满血腥气味,这是我理解的生存之生活。
| 5 | 我说:“我不喜欢他的画。”(编者按:这里“他”指英国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他是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恩利说:“我喜欢培根和蒙克。”恩利接着说:“可能他受困于表演之中了。”我倒是觉得他早期画得好,后来仅停留在写生的快乐里。恩利又说:“有必要一张油画画一年吗?画女王那张,要三个月?才巴掌那么大。”不知道这些数据是否有依据。恩利平时很沉默,喝了酒之后话才多起来,“他还总穿一件沾满了颜料的衣服。八十年代中国画家都这样,披着长发,身上沾满了颜料。”恩利抖了抖前胸的衣衫,“看,这是我的工作服。”恩利一身黑色一尘不染。
馮骥才《俗世奇人》里,一则故事有这样的细节:“刷子李专干粉刷一行,别的不干。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他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艺术家时髦留长发的年代里,每人都声称读过他爷爷的书《梦的解析》,一部冗长又晦涩的书。我承认我并没有读完。
罗兰·巴特有一段话:“只要剧中一个次要人物表现出某种欲望的动机(可能是反常的,与美无关,但与身体细节息息相关,声音的质地,呼吸方式,甚至某个笨拙的动作),那么,整出剧可能就会很生动。”
| 6 | 又一夜的梦。有时真不愿意从梦中醒来,耽于晦暗的梦境里,努力去梳理出一个结果,结果却醒来了。梦都是在自说自话,常常设想将幻想并入梦里,但却是平行的两个世界。然而,不愿意在噩梦里多待一会儿,努力挣扎着要醒来,快醒来,却怎么也醒不来,便放弃了,恐惧中继续着噩梦。
| 7 | 开始读博尔赫斯小说,为他的绮丽意象着迷,倒不如说是为他的语言着迷。那个时候,学着他的语式写了五篇小说,沾沾自喜了一阵子。这样的语言方式,出自王央乐的译笔,是阿城不喜欢的翻译腔;而在吴亮看来,则是矫揉造作。前年,听说博尔赫斯全集出版,买来重读,觉得全不是那回子事儿了,才知道是王永年翻译的,译者换了。王央乐已于一九九八年故去。

“我把我曲径分叉的花园留给多种(而不是全部)未来”。在博尔赫斯的著名小说《曲径分叉的花园》里,中国园林被作为他思索时间的线索,园林的真正魅力被曲解为“迷宫”的陷阱,迷宫般展开讲述“时间分叉而不是空间分叉的意象”,走向“我们是不存在的;有些时间,您存在而我不存在的迷蒙境地”。“这段时间里,给我提供了一个偶然的良机,您来到我的家;在另一段时间里,您穿过花园以后发现我已经死了;在另一段时间里,我说着同样的这些话……”这种思考时间的呓语,絮叨,难以名状的错乱时间;这是“西方人使一切事物无不沉浸在意义里”的意义?
以上这段是我十多年前的一则笔记,引用了四段博尔赫斯的小说,王央乐译为《交叉小径的花园》,王永年译为《小径分岔的花园》。第一句,王央乐版:“我将我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遗给各种不同的(并非全部的)未来。”王永年版:“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第二句,王央乐版:“这是时间上,而不是空间上的交叉的形象。”王永年版:“形象是时间而非空间的分岔。”第三句,王央乐版:“我们并不存在于这种时间的大多数里;在某一些里,您存在,而我不存在。”王永年版:“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我。”第四句,王央乐版:“在这一个时间里,我得到了一个好机缘,所以您来到了我的这所房子;在另一个时间里,您走过花园,会发现我死了;在再一个时间里,我说了同样这些话。”王永年版:“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

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却是错乱了的。虽然,我曾狂热地爱着博尔赫斯,可是我根本不懂西班牙文,在这里却出现了三个译本,小说名就有三种,王央乐版《交叉小径的花园》,王永年版《小径分岔的花园》,洪磊版《曲径分叉的花园》。窃以为,王央乐译本最好。不过,倒是最欢喜我自己的版本,但这些句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 8 | 网络上有消息,门德斯将有一部战争片问世,据说是一百一十分钟一镜到底。为什么要一镜到底?一直不明白。有许多人却要去极力地赞美长镜头,难道真的“能保持剧情空间的完整性和真正的时间流程”吗?这样讲故事,把维度框在一幅画框里,就像冗长的句子不带有标点符号。倘若伦勃朗的《夜巡》,那张巨幅的油画,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具有客观性,倒是震撼。《撒旦的探戈》开场八分钟的推轨长镜头,色调晦暗沉闷,牛群从牛棚涌出,一路盲目冲撞,一路还试图交配,镜头窒息般地缓慢移动,并且观众被强迫慢慢地看每一个细节,甚至看清每一根牛毛。如史诗一般的寓言方式,这样地强迫我接受。看冈萨雷斯的《通天塔》,他的跳跃镜头,摩洛哥东京墨西哥美国西部不停地跳跃,不停地转换场景,人物还有叙事。俳句的,线条的,片段的,语义学家的区分,类似恋物癖的材料。
| 9 | 并不同意苏珊·桑塔格所说的“作为生殖器的照相机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隐喻,而这种隐喻却又是人人都在无意识地使用着的”。就像看一张报刊新闻上的照片,街头巷尾,那是别人的事体,不会感同身受,也不能读出隐喻而产生联想。反不如看自己家人的照片,那些曾经的过往,每一张都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譬如杉本博司的照片,我更愿意去阐释,也许可以写出一万字;而观看,却是和看一件北欧家具一样,明快淋漓地爽。荒木经惟的照片,仅在力刻露,过多地矫揉造作,也引不起联想,因为隐喻过分直白。现在,我更欢喜看筱山纪信的一些照片,尤其那张拍摄井可南子坐在花园里,如沐春光,实在美好。毫无主题,毫无隐喻,毫无刺点,既不是假面,也没有割裂现实,更不是偶遇,是一次略有表演的此曾在,布满了可叙述的细节。
看这样与我无关的照片,纯粹影调的言说,简单平凡毫无深度,却无比美好。也因此,我欢喜看年轻时候的陆小曼,还有阮玲玉,这些美女们的照片。
| 10 | 一九九三年在深圳,那时候深圳还有一条老街,有家新华书店,好像在博雅文具店旁边。在那个书店,因为书名好听,设计简单,我买了一本《说吧,记忆》,白封面没有图案,简陋铅字印刷的书。却一直没看。一九九五年在北京,白石桥附近的一个书摊上,买了一本《一个鳏夫的烦恼》,讲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的感情故事,许多情节设计得难以预料。大概一个月才看完,可能语言的连珠炮方式,其中夹杂着许多錯别字,我不习惯。冬天回到江南,去南京拜访大学时的辅导员童忠贵老师。与他聊起最近读的这本书,他说,你看的是《洛丽塔》吧?纳博科夫牛啊,他说,这小说开头就无人能比:“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一九九八年,我的颈椎病特别严重,有一个星期我甚至半瘫了。于病中找来一直没看的《说吧,记忆》,作者居然是纳博科夫,打开第一页,“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尽管这两者是同卵双生”,头开始眩晕了,以为颈椎病又犯了。我的颈椎病情,往往是从微微眩晕开始,然后一阵无以言表的愉悦感出现(可能是某根骨刺阻碍了血管,使脑部缺氧),接着眼前一片黑暗,感觉到死亡临近了。“但是人在看他出生前的深渊时总是比看他要去的前方的那个(以每小时大约四千五百次心跳的速度)深渊要平静得多。然而……”然而却不是,我没有犯病。是他的语言的节奏,以及他的思绪潮水般地涌来,使我眩晕,我很愉悦。“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时间恐惧者,当他第一次看着他出生前几个星期家里拍摄的电影时,体验到一种类似惊恐的感情。他看见了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然后意识到在那里面他根本就不存在……”
后来还是无意间,买了一本《固执己见》。最欢喜纳博科夫的这本访谈录了,发现他比我更加尖酸刻薄,甚至恶毒。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廉价的感官刺激小说家,又笨拙又丑陋”,海明威和康拉德“在精神和情感上不可救药地幼稚”,等等。他这种没有战略的战术,蝴蝶双翅“震颤”般的双唇的战斗姿态,在于他不断地攻击,用于阻拦。后来,这本《固执己见》被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借走了,再也没回还。今天,网上再买一本,估计后天能寄来。
| 11 | 我对父亲概念的认识,乃是政治的父亲。政治即伦理,政治是父权秩序,社会真实的纯粹学科,其基础便是我没有价值。我与父亲基本没有感情,在我十五岁之前,他以至高无上的姿态,随时俯看着我。那夜的梦里,梦境阴森地让我从窒息中挣扎醒来,也就在那一刻,住在我家大门旁的人家,都听见有个女人嚎啕地哭喊着飘进后院我家。那一刻,父亲则在医院里。一口不能呕出的血块,黏稠地将他的鼻腔和气管阻塞。梦里,我被塞进了一个山洞里,洞越来越窄,一个鬼魂死命推我,洞最后变成了缝隙,在我的头瞬息炸裂开来的那一刻,父亲死在了医院。那年我二十四岁,还在南京上学。丧事之后,每次外出回家,临近家门的时候,觉得父亲仍在堂屋里坐着,自小惧怕父亲的心情依旧忐忑着。推门时刻,一个念头闪过,这个人终于走了。
| 12 | 一九九三年的时候,十分迷恋表现主义油画。一种淡淡地接受了周围谈论艺术标准的程序,逐步地同意所发现的世界,或者说,那个时间段里,我只接受了表现主义艺术。不过当时的笔记却是这样写的:“人是可怜的,人的心灵是孱弱的。所以,我对梦的理解是由两种梦境组成:A.夜半的噩梦,是恐惧和荒谬,是泪水伴着绝望。在旷野奋力地奔跑,身体负着行囊,艰难举步,胸膛已被子弹射穿。但我似乎没死,忍受着无尽茫茫黑夜的煎熬,不能醒来。我很累。B.我清醒的理智的梦光辉金色灿烂,有着恢弘的画面飘浮,爱情的甜蜜幻觉不断。”显然的神秘主义倾向,难以自拔的自我爱恋。
当时,我只是同意,没有选择。因此,那个时候迷恋的,不是感性使然,也可能是对技术或者不可企及的作画手感的向往。倘若将所画的人倒置悬挂,或者干脆画倒置的人,是语义学的。但他的笔触,却是表现主义的表象。如同那个颇有争议的画大场景的,回顾“二战”焦土的画面的;他,却是个古典主义情怀的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