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用典的美学争议
诗跟词的关系,一开始我们从“诗词分家”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举一些例子来说。这里牵涉到一个理论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如何来理解宋词。比方说用典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一般用典的话,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出典,那就妨碍了你对这首词的欣赏;当然现在有很多选本也会解释这是出自哪个典故。对于读者来说,首先要知道才能够去欣赏,那问题就来了,这样知识性的东西介入词的欣赏,是不是会妨碍感情的直接沟通交流?而在词学里边,用典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张炎的《词源》是南宋时代词学的代表作之一。他在书中认为周邦彦也是一位大家,他用典只用以前的文学里的典故,而不是用经史或者儒家经典,这就加强了其作品的文学性。张炎的这个意见实际上代表了一些有名的词家在美学上的努力。
那么为什么要用典?用典是作者对文学传统的理解。词家如果用了某一个典,比如杜甫、李白,或者更古的屈原、宋玉,那说明他读过这些作品。而且他既然用到自己的词里边,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话、一种感情的沟通。这就使得作品的文学质地、文学质量,有一种厚重的感觉。因为他表达的并不是单个人的感受,而是经过跟文学传统的沟通,用一个时髦的理论术语来说,就是“互文”。“互文”在现在的文学理论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张炎在《词源》中高度推崇姜夔,认为他的词风格“清空”,具有一种超然的、高级的审美境界。而王国维则非常不满,他说:“《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著。”这里就涉及姜夔的两首词《暗香》和《疏影》。王国维为什么反对?说来话长,我在《书城》上已经登过一篇关于王国维跟他的《人间词话》的文章(《〈人间词话〉的现代转向》,见《书城》杂志2019年5月号)。因为王国维作为近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学问家,也受到了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对于词,他最推崇北宋,甚至于像古代那种直抒胸臆、情景交融的描写。而对于南宋以后所发展的,比如说用典,他坚决反对,他认为读姜夔的词就像是“雾里看花”—看不清。他也认为因为用了典故,这一类词不能直接打动人心,就给感情的表达带来了隔膜。实际上,王国维已经考虑到中国古典在现代的功能,他希望中国的古典传统能够直接地为现代人所理解,不要搞得太复杂,就是要把某些传统的东西简化。王国维的这个看法跟胡适契合。我们知道胡适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九一七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要打倒中国的文言,他说新的文学、现代的文学就要做到八条,这个八条他认为都跟中国古典文学的弊病有关。其中一条就是新的文学应该为大众所能够理解,因而坚决反对用典。而在宋代的词人看来,比方说李清照,她在《词论》里边提出了一些独特看法。她认为“词别是一家”,就是不能跟诗混为一谈。她还对当时的各个名家进行了批评,“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秦观的词特点在于他非常细微、缠绵地表现了感情,的确很少用典故。李清照觉得秦观的词“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这个评语蛮刻薄的,说秦观虽然擅长写情,但是缺少一点文人的涵养,就像一个贫家女,虽然长得好,但总是缺乏一些贵妇的仪态。另外,“黄即尚故实”,就是说黄庭坚。黄庭坚有一个理论叫“点铁成金”,提倡在诗里要用典故。他用的典故出自经史子集,甚至小说笔记。他的词跟他的诗差不多,也用典故,但是用得太杂太乱。李清照觉得反而不好,“良玉有瑕”,一块好好的玉反而有了瑕疵。对于用典,李清照认为要用得恰到好处。这是关于用典的一个美学争论。

我们来看一下姜夔的《暗香》《疏影》到底写了什么,大致概括一下它的写法跟一般的抒情有什么不同。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暗香》)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疏影》)
情景交融是最常见的写法,但姜夔并不是写他眼中所见到的自然景色,而是用了很多的典故,基本上都是文学典故。历来对这两首词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说他这两首词是为范成大写的,范成大当时在官场上有点不得志,所以词里边的内容是暗示范成大以后一定会官场顺通。他又写到王昭君,我们都知道王昭君的故事,被远嫁到匈奴,她骑着马抱着琵琶,是我们熟悉的形象,让人觉得很悲惨。所以又有人根據这样的描写推测姜夔是在表达南宋两个君主包括后宫都被匈奴俘虏,一直被囚禁在北方,是宋代的耻辱。也有人根据这里昭君的典故,认为姜夔有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又是跟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又有人根据“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就认为这是在怀念他自己的情人。关于这首词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莫衷一是,批评家拿不定主意。姜夔这两首词《暗香》《疏影》虽然都是讲梅花,是咏物的,但全是虚写,并不写眼前看到一朵梅花,它开得怎么样,而是通过记忆,重现众多文学作品中的梅花,以及诗人们怎么描写梅花,他们跟人物、梅花之间有怎样的一种命运关联。每一个典故都牵涉一个关于梅花的故事,不同的典故都展现了梅花在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影像。姜夔的词就是在这些文学作品当中与梅花的形象、梅花的记忆、梅花跟诗人之间的关系,重叠、交错,影影绰绰,一片朦胧,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朦胧诗;但是词人的记忆、感情在里边流动,也就是说这种写法已经跟当时或者是抒情传统里边的一些主要手法不同。因为情景交融是一种写实的手法,就是把自己眼前看见的描述下来,渗入主观抒情。但姜夔这种写法完全是虚写,某种程度上,这也像一幅印象派的画。当时很多人不能接受这种写法,因为跟他们平时所遵循的逻辑相违背。如果我们改变自己对于文学基本写实的观念,那就会接受一种新的模式—感情的欣赏模式。

今天来看姜夔的这两首词,我们强调文学性,那是完全纯文学的,是一种纯诗的表现,也反映了词人在创造新的美学模式,在探索描写感情的新的可能性。
这里还牵涉到另一个更加有争议性的南宋词人吴文英,他写的词当时人觉得难懂、晦涩。张炎《词源》说吴文英的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读他的作品一头雾水,不知道它在讲什么。围绕吴文英的批评争议非常尖锐,比姜夔有过之而无不及。张炎跟沈义父都是南宋的词学专家,他们的词论很有影响。沈义父也说,“梦窗深得清真之妙”,清真就是指周邦彦,“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乐府指迷》)。但到了清代的周济,对吴文英大加称赞:“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宋四家词论》)周济是常州词派的理论家代表。到了王国维,他对姜夔基本上完全否定,对吴文英更加不谈,他说:“梦窗之词,余得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凌碧乱。”(《人间词话》)他用吴文英自己写的一句来概括,“映梦窗,凌碧乱”,这的确代表了吴文英创作的一个特点,从修辞手法来说,往往违背通常的逻辑。一般来说,句子应该主谓分明,但是他往往把宾语弄到前面,这样的话,就会让人觉得它的秩序是混乱的,一般人就没法看懂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胡云翼选注了《宋词选》,认为:“南宋到了吴梦窗,则已经是词的劫运到了。”也就是说,到了吴文英南宋词就结束了。他认为南宋的词不好的倾向是讲究形式主义,姜夔、周邦彦、吴文英都是这一路的,对于创作来说是不好的倾向,应当反对,吴文英是这里边的极端。但是到了现代,像唐圭璋,对吴文英崇拜得不得了。他说吴文英有五种抒情的主题,有抒羁旅之情者,有抒怀旧之情者,有抒怀古之情者,有抒惜别之情者,有抒伤逝之情者。如果我们从抒情美学看,吴文英对于感情的表现范围非常丰富、多元、有层次,虽然怀古、怀旧、伤逝,都是属于比较低落的感情,但是不得不说,低落也属于抒情传统,人间有很多不理想不愉快的事,为什么不可表达呢?而且唐圭璋说,吴文英的词有五个艺术特点,凝练、细微、曲折、深刻、灵动。灵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他的词的整个结构里边,可以看到情绪的流动,跟一般写词的章法不同。我们说写词,在上下两阕之间换一个场景是最基本的手法,已经是很有变化的了。但是在吴文英的词里,单上阕或单下阕里边就有曲折,就有感情的转换,非常复杂,由此可以看到他的感情的灵动。叶嘉莹先生很早就写过一篇关于吴文英的文章,说他的词是一种极高远的穷幽艳之美的新境界。实际上从晚清以来,对吴文英的词评价越来越高,有人说几乎晚清的一半詞家,都是受吴文英的影响。

稍微举吴文英的一首词《惜黄花慢·送客吴皋》为例:
次吴江,小泊,夜饮僧窗惜别。邦人赵簿携小妓侑尊,连歌数阕,皆清真词。酒尽已四鼓,赋此词饯尹梅津。
送客吴皋,正试霜夜冷,枫落长桥。望天不尽,背城渐杳,离亭黯黯,恨水迢迢。翠香零落红衣老,暮愁锁、残柳眉梢。念瘦腰、沈郎旧日,曾系兰桡。
仙人凤咽琼箫。怅断魂送远,《九辩》难招。醉鬟留盼,小窗剪烛,歌云载恨,飞上银霄。素秋不解随船去,败红趁、一叶寒涛。梦翠翘,怨红料过南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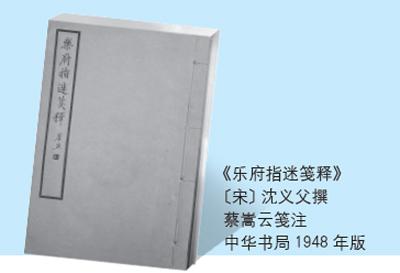
这首词写送客,我们看到,“送客吴皋,正试霜夜冷,枫落长桥”,实写眼前的景色。“望天不尽,背城渐杳,离亭黯黯,恨水迢迢。”要跟朋友离别,而有离情别绪。但是,“翠香零落红衣老,莫愁锁、残柳眉梢”,这是在写谁?这显然涉及男女之情,根据他的序言,那一天有歌女在船里演唱,然而“念瘦腰。沈郎旧日,曾系兰桡”,他想起自己过去曾经也在这船里面。“仙人凤咽琼箫”,则是下半段,仙人是指她的意中人,他想起自己当初跟情人相似的离别情景。“怅断魂送远,《九辩》难招。”《九辩》是宋玉《楚辞》里的名篇,而那一天歌女一直唱着周邦彦的词,可能他有点失落。但有的批评家就说“《九辩》难招”是他心里想着宋玉的经典,周邦彦他不看在眼里,这是一种说法。《九辩》本身是一个很悲凉的作品,“《九辩》难招”写他跟意中人的分离,意中人一去不复返,这种悲情就通过用《九辩》这样一个典故,来显得他感情的深刻性。“醉鬟留盼,小窗剪烛,歌云载恨”,这又是当前的实际,写这个歌女在歌唱,但是歌唱内容跟别离有关。所以他说:“歌云载恨,飞上银霄。”最后说,“素秋不解随船去”,这个句式是吴文英典型的倒装。素秋也就是当时的秋天,船离开了带不走这个素秋。“败红趁、一叶寒涛。”这种句式也有悖通常逻辑,但是也代表了吴文英词作的修辞特点,语不惊人死不休。每每在遣词用句之际,他就要陌生化,这对吴文英来说是一个创新的基本要求。这条原则贯穿在吴文英的词作中,特别是在四字句里边,从来没有重复。他最后说:“梦翠翘,怨红料过南谯。”又回到他思念他的“仙人”。送别友人,但离别是双重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真的为跟他的朋友离别而悲,还是他在为跟爱人分手而感到凉。显然他的重点是在讲自己,但是这种虚实描写,并不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而是在跳动。他的感情一会儿在眼前,一会儿又飞到了前面段落,所以看他的词真的是费尽心机,非常讲究。还有这首词每个句子的第一个字,都是用去声,从音律上来说是有讲究的。这些字对于感情来说—因为去声—就有一种沉重感。按照一般的修辞惯例,是在第三个字或者第五个字用动词,但是他用在每一句第一个字,还都是去声,这是他的独创形式。可以这么说,他越来越得到批评家的关注和称赞,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更为深刻,而且更有耐心去读这样一些表面上晦涩的作品时,说明我们的美学趣味在提高;也正因为我们美学趣味的提高,才能理解其中的奥秘。
七、美学观念的变迁
稍微要谈下诗学与词学的关系。词学是一个独立的批评传统,像张炎的《词源》、沈义父的《乐府指迷》,是南宋时期词学的两部代表著作。他们往往通过树立榜样来定出一些标准,这对词本身的发展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同时也牵涉词的发展和诗之间的复杂关系。诗,是一个大传统,从孔子的时代开始,儒家对于诗就有一系列的论述,比如说“诗言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但词是抒情的,而且一开始就跟当时的流行歌曲连在一起。按孔子的说法,那是郑卫之声,是淫声,是有悖道德,要谴责、要防止的。但是对于词的传统来说,一方面要坚持词的特性,就是音乐性;另一方面要在抒情的同时也提倡“雅正”。此外,词也部分地从中国的古代诗里吸取了一些理论资源。比如柳永,因为他多是跟歌女、乐官打成一片,许多词甚至运用一些俗语俚语,在张炎和沈义父看来这是不入大雅之堂的,所以要反对。到了清代,又出现前后两个写词的热潮,分别是朱彝尊的《词综》和张惠言的《词选》两部词学作品。《词综》推崇姜夔,但到了清代中期常州词派的张惠言之后,主张就比较不同了,反而要回到古典“诗教”,包括描写手法、比兴手法,或者是要讲究词的微言大义,就是要跟香草美人的传统接轨。这种理论上的表现跟各个时代整个风气的转移,以及词学传统本身的发展轨迹有关。

到了清代之后,豪放派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先像张炎、沈义父他们不仅反对柳永,也反对豪放派,认为豪放派不能代表词的正宗,因为词要强调柔软,要强调音乐性。所以在词学传统里边,他们坚持词的特性有一个正确的发展轨道,因而要防止一些倾向,使得词沿着它自身的方向。无论是张炎也好,沈义父也好,或者是清代朱彝尊、张惠言也好,某种程度上都是坚持形式主义,讲究内在的细腻以及感情的表现。
今天怎么来更好地欣赏宋词,怎么更有利于我们理解宋词的传统、词的美学发展,就牵涉到一些理论的问题了。比如刚才说的胡云翼,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研究宋词的大家,他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的立场;现在宋词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吴文英、姜夔都非常重视,而且有一些人认为对他们的研究还不够。这个问题是我在《书城》上写的关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文章中提出过一些看法(《〈人间词话〉的现代转向》,见《书城》杂志2019年5月号)。我觉得词学本身的传统是讲究形式主义的,从总体上来说,词的形式主义没有什么不好。当然每一种主义发展到后来会有它的利弊,但我们今天更要在全球范围里去理解。比方说我们现在一谈到西方的诗歌,就说里尔克、艾略特代表了文学的一种典范云云,实际上之所以里尔克或艾略特受到诗人们的一致推崇,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艺术的某一种高峰,创造了许多美学上的形式。比如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里边充满典故,而且他怕读者不理解,自己做了许多注释。谈起里尔克,我们觉得他的诗是纯诗,他是纯粹的诗的代表。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来看宋词的传统?抒情传统从本质上来说是非常个人的,而且追求形式,其本身就代表了美学的发展,代表了文学的本性。文学的发展一定是受到创造力的推动的。
八、“正宗”与“本色”
二十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在国际学界,美国的新批评发展出了一套批评的系统。欧洲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人的诗作被他们诠释之后,使读者看到了诗作中诸多的门道,也使读者更理解诗。西方学界流行的俄国形式主义,也发展出了一套批评的术语理论,并对俄国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还办了专门的杂志向国际推广,大家才知道俄国文学是那么的经典。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更为深刻地把握宋词的传统,提高我们对于宋词的认识,就要一方面注意刚才我所说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文学从来不能脱离生活实际,词本身的音律、音乐性也是它的法宝。在词学批评里有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反而是来自写诗的一些大师。比如明代的王世贞、清初的王士祯,都是诗坛大家,他们谈词跟那些专门的词学传统有所不同,他们看得比较广一些。王世贞举了“李氏”(李后主)、晏氏父子、“耆卿”(柳永)等一系列的人,认为他们代表宋词的“正宗”,这是一种批评。甚至有人说词学最值得表彰的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后主,一个是李白,再一个是李清照,这也是一种说法。
在我们所举的词的发展当中,它本身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跟生活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跟音乐的关系。柳永是宋词比较早期的开创者,他留下了大量作品,有一点无论谁都不能否认,就是他在音乐性上代表了词的正宗。反对柳永的,认为他格调不高,词作里边有些俚俗之语。他跟歌女之间开玩笑写的词,很有民歌的色彩,但實际上也有巧妙的地方。后来因为他的词受到欢迎,他就变成了一个专业的写词人,为歌女提供词,由歌女去唱,但这种词也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也要“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奸字中心著我”(柳永《西江月》)。这也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但像这种东西在雅正的词学传统里是不被接受的。如果大家都这么写的话,词好像就会失去它尊严的地位。
实际上每一位词人要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都需要对传统有各自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学书法,是先从柳公权入手,后来又学了谁谁,然后就融汇众家而自成一体。文学作品也是一样,它总有学习的,又有独创的,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些特殊的配方,而在天才作家那里,又往往是超越配方或套路的。李清照实际上受了柳永很大的影响。柳永词的音乐性跟歌唱实践是打成一片的,所以作品当中甚至留下了跟歌女打趣的作品。李清照一个大家闺秀,不可能到歌场里去,但是对于李清照来说,写词第一最要紧的就是音律,所以她就把音乐跟诗里边的平仄四声结合起来。她的结合要更加细致复杂。我们看《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开头十四个字,用了叠韵,还有双声,这打破了常规,跨度太大、太前卫,以致当时许多名家不接受也得接受,因为她用作开头的十四个字,跟她整首词的表达是一个严密的整体。所以词家对李清照这首词大加赞叹,甚至有人统计了整首词里边齿音跟舌音有多少字。也就是说这首词里边是暗藏机关的,为的是表达那种凄切的感情。而且她整首词的韵脚用的是去声,这个词牌是她独创的,因为词牌一般是用平声韵,但李清照为了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用了去声韵,被认为是树立了一个典范。
“独自怎生得黑”这个“黑”字要入声韵,绝大多数的批评家觉得这是绝妙,一般人没胆子把“黑”字来作为韵脚,但是她“独自怎生得黑”,又是感叹又是问句,把整首词压住了。而且最后“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表现了什么样的正宗或者本色呢?就是她完全不像姜夔、吴文英、周邦彦,不走他们的路,表面上她不讲究形式,她所取的意象来自她个人的生活,看上去都很平常。而且她巧妙地运用了这些比较口语化的语句,“独自怎生得黑”或者是“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或者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看上去挺家常,但这个的确表现了她的独创性。这一首词代表了李清照词作的艺术造诣,是词的一个绝唱、经典之作。生活现实,锻字炼句,音乐性,这三点对于词学发展来说是最为关键的抒情特质。音韵是表达感情的,要恰到好处体现感情的深刻流动,还要来自生活现实,不脱离生活,因为一旦形式主义走到极端,就会脱离生活的源头活水,也会给创作带来枯竭的影响。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词学本身有各种不同的取向,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反映在具体的创作方面就非常多元复杂,而对我们读者来说也有各种不同的取向。
本文系作者在新华·知本读书会第七十七期所作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