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英国著名当代女作家,一九五九年生于曼彻斯特,几个月后被兰开夏郡阿克灵顿的约翰·温特森与康斯坦斯·温特森夫妇收养。温特森太太意欲将养女温特森培养为女传教士,但温特森生性中的叛逆以及对阅读的热爱打乱了温特森太太的计划。而温特森少时有悖传统的恋爱行为,更触怒了养母、教会与她所生活的小镇,导致了她十六歲时即离家出走。在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就读期间,温特森曾回家探访养父母,与养母产生冲突,不欢而散,此后再未见面。温特森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她一九八五年的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以下简称《橘子》)。凭借这本小说,温特森获得“惠特布瑞德奖”(Whitebread Award),一举成名。
 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
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十几年来,我早已习惯了温特森在文字中无论如何幽默风趣也无法消弭的沉重,而二○一八年秋,当我读完她出版于二○一一年的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以下简称《快乐》)后,突然对她的文字有了新的感悟。在《快乐》一书英文版的扉页上,印有《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对本书的评价:“勇敢,有趣,让人心碎”(brave, funny, heartbreaking)。这其实是温特森自处女作始一贯的风格。只是,她需要时间来化解生命与文字中的沉重,将其艺术化,在悲剧的书写中升华出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净化”(catharsis)效果。这对没有类似经历的艺术家来说,需要天分或技艺,但对在苦难中出生、成长的温特森来说,便不止这些。她有天分,这毋庸置疑。技艺,她说,她不需要。她的作品中碎片化的叙事,在评论家看来是其创作技巧,在她自己而言,却是她的人生本真的样子。那么,漫漫岁月里,如何化解、升华这些苦痛?又要如何原谅?这本自传给了两个答案:书与爱。
“我们从他人的语言中找回自己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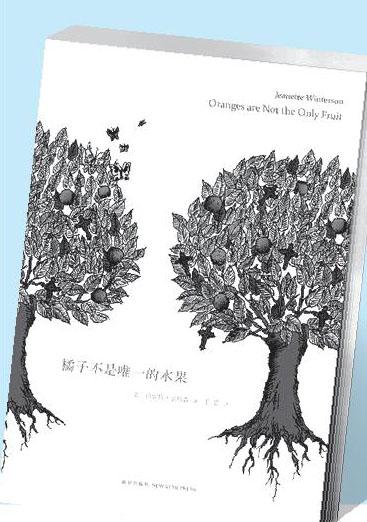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英]珍妮特·温特森著于? 是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英]珍妮特·温特森著于? 是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温特森在《快乐》一书中说,多年以来,很多人就《橘子》中同名女主角的生活经历的真实性向她求证。关于事实与虚构,她解释了很多。但在她解释的众多内容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句话:“有许多事我们无法说出口,因为它们太过痛苦。”(冯倩珠译)与《橘子》相比,《快乐》中的情感表达要强烈、直接得多。
在《橘子》一书中,温特森把成长过程中的痛与快乐通过同名弃儿珍妮特展示给读者。那更像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在换着方式表达背叛者给她的创伤,以及寻找疗愈与释怀却不得的经历。她自始至终并未表达原谅背叛者的意愿。在一个传统、复杂的世界,她努力守护着自己的纯真与纯粹,面对恋人、朋友、教会甚至家人等的背叛,她始终只有一句话:“对于纯净的人来说,一切皆是纯净的。” (To the pure all things are pure.)这句话出自《提多书》(Titus),温特森只引用了前半句。如“背叛就是背叛”一样,这句话在书中反复出现。当时的温特森尚无勇气直面创伤,也缺少力量对抗传统与权威。她只能一遍遍地重复这句话为自己辩护,并隐晦地表达自己对传统与权威的指责与对抗。
小说采用了《旧约》的结构,穿插很多她改写的童话与传奇故事,对应她对自己身份和现存一切的疑惑与反抗。但,她也在这其中时时表达着对抗权威的危险,比如她所改写的公主王子故事。她的故事中,被王子看上的女子拒绝了王子的求婚,并对他的哲学与世界观表示了不认同,因而丢掉了性命。不同于传统的公主王子的幸福故事,女子最终因为挑战王子所代表的权威而被杀。温特森的反抗是隐晦、有意识的,但她也深知这种反抗是危险的。这种认知反映在她改写的关于圆桌骑士帕西瓦尔(Perceval)的故事中。帕西瓦尔千辛万苦寻找圣杯是为了寻找自己迷失的平衡,即,世人眼中的英雄与渴望种花种草和平生活的自我之间的平衡。温特森的研究者瑞娜·范德维尔说,“真实”是温特森在《橘子》中努力逃脱的东西。范德维尔对小说与作者的判断是基于温特森的写作风格,但同时也符合温特森创作时与传统对立的状态。温特森对于“虚构”的探索,实际上也是寻找传统权威力量与个人欲望之间的和解。如苏珊娜·奥涅加所言,温特森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模糊有双重的目的,一是个人的,一是政治性的。我想,也是这一点让温特森逐渐成为不仅仅是沉迷于个人伤痛的作家,而且是借此来思索和反映社会与人类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因此,温特森改写的童话和传奇故事,与她反复强调的那两句话一样,看似果断坚定、毫不妥协,其实更多的是疑惑、怨恨与无奈,是她在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挣扎和游离。
在二十六年后的自传中,温特森依然怨气十足,但她已经可以直接表达。虽然仍会用典故,但她不再隐晦。养母在电话中指责温特森在《橘子》中所写的关于她的那些事情不实时,温森特把养母比作希腊神话中的忒柔斯,把自己比作被忒柔斯强暴并且割掉舌头的菲洛墨拉。在这种受害而又不能言语的困境中,温特森发现:“我们从他人的语言中找回自己的语言。我们可以求助于诗。我们可以翻开书本。有人在那里等我们,深潜于文字中。”如果说《橘子》展示了伤疤的来龙去脉的话,《快乐》则提供了治愈伤口的解药与过程。虽是自传,但其中养母的形象相较小说《橘子》中的更加戏剧化、更富张力。养母的病态与矛盾性是温特森伤痛的源头,也是伤痛最终得以治愈的药引。
温特森对书本的渴望有“找回自己语言”的需要,但在最初,也与温特森太太对书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温特森太太对经书异常痴迷。她每天给丈夫与养女诵读经文,但却禁止养女阅读其他书籍,尤其是虚构类作品。而在她对虚构类作品的禁令中,也有例外。《简·爱》是温特森太太唯一允许养女“知道”的世俗小说,之所以用“知道”而非“阅读”,是因为这本小说是由她来读给小珍妮特的。温特森長大以后才发现,养母在对小说的诵读过程中修改了故事的结局,在她的口中,简没有回到罗切斯特身边,而是选择了与传教士约翰结婚,并开始一起传教。多年以后,重读这本小说的温特森虽然惊奇于养母即兴修改并保持文字风格不变的能力,但再不曾拿起《简·爱》。
温特森回忆,儿时的家中仅有六本书,三本与经书有关,另外三本是历史等非虚构作品,这是温特森太太为了不让养女受世俗文学的影响,为她划定的阅读范围。为了阅读,温特森与养母经常斗智斗勇。
偶然的机会下,温特森在去图书馆帮养母借书时,读到了T. S.艾略特的诗歌,从中感受到了诗歌的震撼与治愈力量。于是开始瞒着养母,用在市场打工赚的钱买书。为避开养母的搜查,温特森把书藏在床垫下。但床的逐渐升高引起了温特森太太的疑心。床垫下露出一角的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使她发现了那些于她如洪水猛兽般的藏书。这些书最终葬身火海。违逆养母禁书令的温特森,眼睁睁地看着她愤怒地将书扔进后院,浇上煤油,付之一炬。面对着被烧得只剩灰烬的书,温特森决定开始背书。因为,“只有内心的东西才是安全的”。温特森太太烧掉了书,但烧不掉已经深藏于温特森内心的那些内容。她决定与它们一起逃离,她不无讽刺地表示,书本燃烧时的火焰给了她暂时的温暖与光明。而毫无任何讽刺意味的是,温暖与光明确实是书一直给予她的。后来,温特森在二○一一年为苏格兰女作家娜恩·谢泼德(Nan Shepherd)的《活山》电子版写的后记中曾直言,书籍在她十六岁离家出走后为她提供了“内在的光源”(管啸尘译)。而正是在养母焚书那一刻,温特森用一句粗话表达了自己写书的决心:“‘去它的,我想,‘我可以自己写书。”
 《活山》[英]娜恩·谢泼德著管啸尘译文汇出版社2018年版
《活山》[英]娜恩·谢泼德著管啸尘译文汇出版社2018年版焚书事件以后,温特森对书籍的迷恋更加痴浓。在家乡阿克灵顿的图书馆里,没有任何阅读经验,未曾受过任何阅读训练的她开始按照字母顺序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艾略特、奥斯丁、勃朗特姐妹、马维尔、纳博科夫、普鲁斯特、斯坦因、伍尔夫等作家就是这样成了进入大学之前的温特森的读物。在图书馆里,她还接触到了弗洛伊德、荣格等心理学家的作品,并惊奇地发现,除了文学书,竟然还有其他类型的作品。她对心理学、哲学的阅读也是从那里开始的。
疯狂的阅读给予她信心,慰藉她无家可归的孤寂与伤痛,最重要的是燃起了她对生活与生命的渴望之火,为她提供了一个认识与寻找自己的途径。被生父母抛弃,又被养父母二次抛弃所带来的伤害,若非书的陪伴,生性的倔强与乖戾或许会使温特森最终走向在英国被大多数人鄙视的“CHAV”(政府救济房[council house], 酒精[alcohol],暴力[violence]的缩写)群体,即没受多少教育、没有工作,须由政府救济并且有不道德行为倾向的年轻人。书籍为温特森带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让她意识到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必要性。初次申请牛津大学失败的她,通过自己的争取与圣凯瑟琳学院的导师约好了第二次面试。她以自己的生平、阅读经历以及要写更好作品的愿望为自己争得了入学的机会,却在课堂上被导师戏称为 “工人阶级试验”。同被导师讽刺为“黑人试验”的薇姬成了温特森一生的挚友。
虽然作为工人阶级的女性,温特森在校时受到了不少打压与贬抑,但她仍然感激牛津大学在阅读、思考与讨论等方面的培养与鼓励。牛津大学的教育,兼之早年的经历与所睹所闻,让她成为一个在写作中不耽溺于自己苦痛的作家。她写出生城市曼彻斯特的历史,在恩格斯的文字中思考这座城市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她在撒切尔夫人的执政中反思私有与国有的区别,担忧以金钱为中心的教育所可能带来的功利与量化。因书而对自我、家乡、社会、国家、人类的思索,让温特森成为英媒笔下自伍尔夫以来最具贵族气质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与之相关的学术论文、专著层出不穷。英国大学的英国文学课程大纲上有她的作品。温特森的弃儿身份是她的创伤,创伤成为她的标签,而这种标签本身就提供了一种“崇高性”的可能,而阅读则是引导温特森找到表达这种崇高性的最合适的方式。
在《活山》后记那篇文章中,温特森坦言在书籍中寻得舒适自在的空间,寻得家与光源的说法在别人听来可能有些神秘。但她又接着说,每个人确实都需要寻得一种存在与生活方式。毫无疑问,书籍帮助了温特森,让她在无助、绝望、苦痛与无家可归的迷茫中,寻得属于她自己的存在与生活方式。温特森太太或许最终也无法明白,自己对养女的禁书令怎么会生出如此戏剧化的效果。
“温太太是个怪物,但她是我的怪物”
自传的前十一章比《橘子》更加全面地展现了温特森在阿克灵顿的生活,与养母的冲突。她在其中写了很多自己在写作《橘子》时,尚无法承受的经历。自传涉及的时间段主要包括两个:一是从她一九五九年被收养到一九八二年最后一次与养母见面,一是从二○○七年直到写作的当下。其中夹杂着个人与历史的叙事,补充了小说中未曾言说的内容。温特森不相信线性叙事,认为艺术时间可以超越物理时间。因此,她省略了一九八二年至二○○七年之间的二十五年未表。就如莎士比亚在《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第四幕的第一场中所言:“我匆匆跨过十六年略去中间/经过不详谈。”(李华英译)那般推翻了“规律法则”。在第十二章直接进入了二○○七年,温特森在养父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后发现了自己真正的收养文件,认识到四十多年前她在家里发现的那个收养文件并非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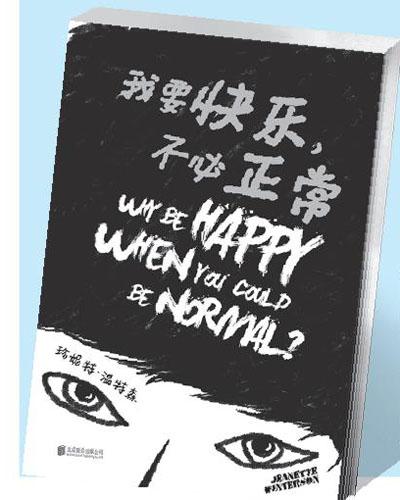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英]珍妮特·温特森著冯倩珠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英]珍妮特·温特森著冯倩珠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心理学家一般认为,养父母的爱能在某種程度上缓解并且治愈生父母弃养给孩子内心所带来的创伤。温特森的不幸在于失去了生父母的爱,也没有得到养父母的爱。温特森太太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教化这个她认为是魔鬼带给他们的养女—在家里任何一个养女可能走到或经过的地方贴上经文;在养女的运动袋上绣上“夏季已尽,我们还未得救”。多年以后,当养父的第二任妻子告诉温特森其实养父很爱她,并且很同情她当年的遭遇时,虽然一直感念沉默的养父对她无言的感情,温特森依然反驳说他当时并未为她做什么,也未说什么。小说与自传中的温特森虽然遭遇有所不同,但她们经历的孤独是相似的,事实是,自传中的温特森比小说中的还要孤独。因为真实生活中的她,连一个如《橘子》中埃尔希那样的忘年朋友也没有。
温特森需要爱,但温特森太太从未给予,或者说只给予了她畸形与扭曲的爱。关于夫妻情、亲子情,温特森一无所知。温特森太太给她的是禁止男孩靠近的指令,但温特森有悖传统的恋爱则让她彻底与养母决裂。也是在十六岁离家时,温特森告诉母亲她与恋人在一起非常快乐,母亲甩了一句:“正常就好,何必快乐?”(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有趣的是,中文版自传的译者冯倩珠从温特森的角度与态度去诠释这句话,因此将之译为“我要快乐,不必正常”。看似与字面意思完全相反,实则是换了角度。)与“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语出自小说中的养母之口一样,自传的题目也是养母的语言。温特森在自传中强调自己这些年的书写主题:“是母亲。是母亲。是母亲。”她用了三个英语现在时的句子(“It is my mother”)表示了过去、现在与未来母亲对她的影响。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全是永远存在的现在时。
爱是一种能力,温特森笔下的养母与生母都缺少这种能力。温特森在自传的前半部分追溯了在不幸的原生家庭中从未感受到过爱的养母的经历,这种不幸让她亦不知如何给予爱。自传接近尾声时,温特森告诉读者,生母也是在缺乏爱的环境中成长。温特森不知自己是谁,不知如何去爱。这在很长的时间里影响了她的生活与创作。她不知如何交朋友,与恋人相处时脾气暴躁,没有安全感。她需要爱,却总是在失去。在创作中,她“着了魔似的、巨细靡遗地书写爱”,并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她“都认为它是最高的价值”。苏珊娜·奥涅加认为“温特森的主要角色们一生都在追逐,推动他们这样做的是他们自身的缺失与不完整性,这让他们强烈地渴望另一个人”。很长时间以来,爱的缺失是温特森和她作品中诸多角色的共同创伤。温特森与她的角色们永不厌倦地追逐爱,但不同方式的背叛总是隐现每段关系的尽头。直到温特森遇到同是作家的苏茜·奥巴赫,得到安稳,习得爱,才终于勇敢地去追寻自己的身世,才有勇气约见生母。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自己,文字里寻爱的莽撞、失爱的绝望才渐渐平息。
温特森约见生母后,发现生母性格要比养母温特森太太温和很多,亦能接受她有悖传统的恋爱。这使得温特森一再思索自己成长的另外一种可能,不一样的成长路径是否能避免其中的挣扎与苦痛?与生母几次相对平和的见面给了温特森希望,直到生母在她面前批评温特森太太。温特森未曾料到自己竟然为此大发脾气,驳斥生母说,至少温特森太太是在她身边陪伴的。她也是在那一刻意识到,如果温特森太太是一个怪物,也只能是她自己的怪物。她亦在同一刻意识到,温特森太太所给予她的“黑色礼物”也不全然是坏的。最起码,是那件黑色礼物成就了阅读、写字的她。她不愿将这样的自己与任何可能的自己置换。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温森特与自己的养母以及她所带来的苦痛和解了。
虽然温特森承认养母的黑色礼物不无裨益,但身为弃儿一直是她的创伤。这种创伤驱动着她不停书写,寻找治愈的可能。在自传中,温特森强调,创伤是她的身份,一旦治愈,她将会再一次迷失自己。但她还是给了自己一个解释,即,治愈的创伤不会消失,因为还有疤痕。那么,疤痕,她说,就是她的身份。那么之后的她将如何生活与写作?对此温特森不无疑惑,在自传的最后,她写道:“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二○一六年,莎士比亚去世四百周年,弗吉尼亚·伍尔夫与丈夫创办的霍加斯(Hogarth)出版社为向莎翁致敬,邀请如温特森·温特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改写莎士比亚的八部重要作品。其中《冬天的故事》由温特森改写为小说《时间之间》(The Gap of Time),被视为这一系列改写作品中的最佳之作。温特森的自传解释了为何她的想象力在《时间之间》中空前地飞扬。小说中,温特森借奥托吕科斯(原剧中的流氓无赖,温特森小说中的奥拓车行卖车员)之口将西方文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介绍给科洛(潘狄塔养父谢普之子),在飞扬与任性中尽显实力。奥托吕科斯说如果早就有环岛,俄狄浦斯与生父拉伊俄斯就不会狭路相逢至冲突,俄狄浦斯也不会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杀死拉伊俄斯,那么多年之后,就不会有弗洛伊德弑父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更不会有那么多花样的文学理论,所谓的“影响的焦虑”亦无从说起。温特森从现当代文明回溯古希腊罗马神话,然后又回到现当代的文学、文艺理论思潮,正如她在其他段落里不经意间援引的福克纳、海明威、纳博科夫甚至还有莎士比亚本人的作品。温特森的想象力在她博大的知识框架中游弋。音乐、电影、电子产品、时装、话剧、整容术,在这部被极度现代化的改写版中交融。这是作者的释放、读者的盛宴。《时间之间》出版当年被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评为年度最佳图书。
 《时间之间》[英]珍妮特·温特森著于? 是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时间之间》[英]珍妮特·温特森著于? 是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在《冬天的故事》中,莎士比亚并没有给知道身世后的潘狄塔多少机会来表达内心所思。这是他一贯的做法,把一切留给读者来想象。潘狄塔回到西西里王国后,很自然地与父王、母后相认,牧羊女成为公主。然而,温特森在这一点上没追随莎士比亚。温特森自己曾谈起对《冬天的故事》结尾的修改。在原作中,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曾经因为不相信朋友波力克希尼斯与自己的妻子赫米温妮,抛弃了女儿潘狄塔,致使赫米温妮在女儿失而复得之前的十六年间如雕塑般安眠。戏剧的最后,潘狄塔失而复得,赫米温妮“死”而复生,里昂提斯向妻子与朋友忏悔,提出找个地方聊聊这十六年间彼此错过的事情。在最后一幕的最后一场中,莎士比亚一句话的机会也没留给潘狄塔。但是温特森则在自己的改写中将最后一部分留给了潘狄塔的独白。她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想把最后的发言权留给潘狄塔这个代表未来的角色:“如果未来存在,新一代将必须发现它。未来是不为过去的暴力与破坏所影响的一片土地。”
除了这些乐观的希望,温特森这样修改结局还有自身的原因。这部戏剧是莎士比亚晚年创作中罕见的以“宽恕”为主题的作品。与潘狄塔同为弃儿的温特森,同有那十几、二十几年的时间之间,她们在其中成长、疑惑、寻找与宽恕。温特森几十年如一日对这部作品的喜欢与阅读,兼其与养母及生母的和解,改写作品的契机,这一切似乎为一幕大戏而生。温特森定不想浪费莎士比亚给她提供的这个倾吐心声的良好机会。临近小说结尾,温特森写道:“现在我走出剧院,走进夏夜的街头,雨水顺着我的脸庞滑落。”读了数遍临近结束时的这句话,我才意识到温特森在此处转换了叙述视角。她把作品中终得团圆、宽恕与幸福的人物留在那里,自己流着眼泪离开。“爱”一定是在“和解”之后,很少会在“和解”当下。在《时间之间》中,温特森所讨论的不再是生父母与养父母的问题,而是在寻求与弃儿身份的和解,是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寻得的一直纠结的、书写的、找寻的“自我”。
《时间之间》中想象力的释放是温特森寻得“自我”以后的信心。这种信心或许也在她自己的预料之外。跨学科的视野与想象力再次绽放于她在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新作《弗兰吻斯坦》(Frankissstein)中。她借这部作品对话了十九世纪的天才女作家玛丽·雪莱的经典之作《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在与莎士比亞的对话之后,温特森在现世与经典之间的穿梭更加自如,她的想象之翼更加强劲。在关于这部新作的采访中,温特森轻描淡写撇开束缚,自信地说:“我就是我而已。”
管它什么标签,温特森就是温特森。
参考文献:
1. Literary Aesthetics of Trauma: Virginia Woolf and Jeanette Winterson, by Reina Van Der Wie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2. Jeanette Winterson, by Susana Oneg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活山》,[英]娜恩·谢泼德著,管啸尘译,文汇出版社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