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 泉
人的名字,是一种归属与辨别的标识,土地的名字也是。人的名字在一生里通常不会更改,土地的名字原来也应该如此。
可是,在人类历史上,为什么每次在政权转换了之后,总要先将土地重新命名?
我的家乡在近代就换了许多不同的名字。父亲年轻的时候在籍贯栏上填的是“察哈尔盟镶黄旗”,我的户口簿上写的是“察哈尔盟明安旗”,而如今,在家乡的族人们却又要称这块土地是“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了。
朋友说,我的遭遇还不算太悲惨,总比要被迫把自己美丽的故乡改口叫做“仁爱乡”“忠孝乡”要好一点,起码还有一部分是来自自己文化的根源。
可是,如果要呼唤故乡,如果在生命的路途上要回头呼唤故乡,有谁不渴望能够找到一个古老、朴素,是由自己的祖先所命名,而又到如今还存活着的名字呢?
因为,只有这样的名字,才能更贴近那块土地,也只有这样的名字,才能更贴近我们的心。哪怕只是座荒凉的山,哪怕只是条浅浅的溪流,只要能够逃过了被更改、被涂抹的命运,留下了一条可以与“昔日”相连接的线索,就是给后世的子孙们最好的礼物了。
这份礼物,终于给我找到了。
三年之前,初次见到父亲的那片草原,才知道她保有了一个古老的名字——“宝勒根道海”,用汉文的意思来说,就是“弯泉”。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最早来自哪个年月,也不知道还能保留多久。我只知道,今天,这是父亲与我以及我们的族人之间,唯一可以共享的愉悦和安慰。
弯泉,宝勒根道海。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线索,开始去寻找一个古老而又朴素的文化。每次翻阅那些历经浩劫的断简残篇,仿佛能够隐隐地感觉到民族血脉的跃动,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
正如人类学家利瓦伊史陀所说的一样,每种文化都有着要强烈保持自身本色的愿望,因为,唯有如此,她才不至于消失和灭亡。

林任菁 暖秋
几十年都过去了,一直要到踏上草原之后,要到了今天,我才开始了解:原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那因为蒙古而流下的泪水并不完全是“冲动”,那在心中固执的渴望也并不完全是“狭隘”,所有的现象都牵连于一种内在的需求,是文化与种族加诸每一个团体之上的,不得不如此的需求。
一切都不过只因为我是一个蒙古族人罢了。认识了这样的处境之后,心里反而释然了,重压卸下,那蒙古文化里明朗美丽的特质反而在处处向我显现。在这里试着把这些心情写下来,就用草原的名字作为篇名,献给遥远的故土。
胡马依北风
蒙古人实在是个爱马的民族。从最早的蒙古史诗开始,以及在后来许多的文学作品里,英雄总是与他的骏马同时出现。在辽阔无边的高原上奔驰,两者仿佛合为一体,共同分担一生的忧患与悲喜,成为被后世所颂扬的勇气、热情、智慧与德行的象征。
而在真实的生活里,马也一直是蒙古牧民倚靠与敬重的朋友。
今年五月,在台北举行的蒙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哈勘楚伦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就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马在蒙古文化里的独特地位。
在谈到蒙古马特别强烈的方向感,以及眷恋故土的优异性的时候,他举了个真实的例子——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蒙古政府曾经赠送给越南友邦几匹马作为礼物。可是,在专人随车送到目的地的时候,其中的一匹骟马竟然独自逃脱,走过千山万水,在半年之后回到了蒙古高原上旧主的家中!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
想一想,它要经过多少道关卡?不但要渡过长江、渡过黄河,还有那其他许多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河道支流,还要翻越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峻岭,还要跋涉过荒寒的戈壁;最不可思议的是:它怎么躲得过人类的好奇与贪欲?在这条不知道有几千几万里长的回家的路上,它难道从来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村镇和城市?从来没被人拦阻过和捕捉过吗?
这样的一匹马,它要具备的是怎样的勇气与坚持?怎样的智慧与判断力?
一位年轻的蒙古学者告诉我,十三世纪左右,中亚的旅行者就曾经在游记上记载了他们的观察与推测。他们说:蒙古马在出发之前,总会昂首向天长啸一声,也许在那个时候,它们就记住了天空中星座的方位,好为归来的路途预作准备。
我很愿意相信这样的揣测。不过,如果是在白天出发的话,又该怎么办呢?并且,蒙古政府送出这批礼物的时候是用汽车与火车来载运的,而这匹孤独的马,却只能靠着自己,一步一步慢慢往北方的老家走回来的啊!
回到自家牧场边上的马儿,泪水不停地流了下来,惊诧激动的主人在想明白之后,更是忍不住抱着它放声大哭。据说主人大宴亲友,并且从此宣告,谁也不能再让这匹马离开他的身边,谁也不准再让这匹马受一点儿的委屈。据说,这匹马中的“尤力息斯”在许多年之后才在家乡的草原上老病而逝,想它的灵魂一定能够快乐地安息了吧。
故事到了这里,算是有了个完美的结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会常常想起另外的那几匹留在越南的马儿来。在会议过后,我再去追问了哈勘楚伦教授,到底是什么在引导着蒙古马往家乡的方向走去?他回答我说: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总觉得应该是一种北方的气息,从风里带过来的吧?”也许是这样。
就像古诗里所说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每个生命都有他不同的选择与不同的向往,有他自己都无从解释与抗拒的乡愁。
因此,我就会常常想起那几匹羁留在越南的蒙古马来,当它们年复一年在冬季迎着北风寻索着一种模糊的讯息的时候,心里会有怎样的惆怅和悲伤呢?
故 居
七月的正午,在新疆的戈壁滩上只剩下酷热君临一切。我们的越野车就像是一只干渴的小甲虫,正脚步蹒跚地沿着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往前缓缓爬行。车窗外是我从来也没见过的奇异风景!一片荒寂大地无边无际,寸草不生的岩砾间满是些黑色的巨大石块,虽然已经被风沙侵蚀得千疮百孔,却依旧矗立,并且像漩涡一般的往四周延伸分散,远远望去仿佛是置身于干涸的海底,又像是超现实画家笔下所描绘的世界的尽头。
而酷热实在逼人,不仅从外面煎烤,就连身体最里面的血管都开始燃烧起来,让我坐立不安。巴岱先生从前座回过头来向我说:
“热吧?再忍耐一下就好了,到前面的绿洲就会好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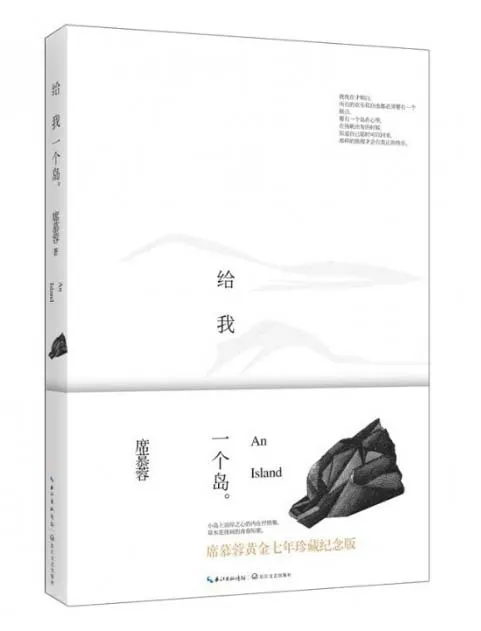
巴岱先生是世居新疆的土尔扈特蒙古人中的长者。他精通蒙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汉文,不但同时用这四种文字来写作,并且更用尽心力来维护这一块土地上的珍贵文化。我对这位长者仰慕已久,这次能够和海北一起来新疆拜看他,并且在此刻能够与他同行,实在是我求之不得的机缘,总该表现得好一点才对。所以,我赶快坐正了回答:
“还好!还不算太热。”
海北却在旁边取笑我了:
“你当然不能叫热!不是还立志要去横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吗?”
是啊!我的丈夫是知道我的。塔克拉玛干、楼兰、罗布泊都是我的梦!是从小就刻在心上的名字!是只要稍微碰触就会隐隐作痛的渴望!要怎么样才能让别人和自己都可以明白?那是一种悲喜交缠却又无从解释的诱惑和牵绊啊!
巴岱先生忽然问我:
“你知道塔克拉玛干这个名字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但是海北说他知道,去年,他曾经从甘肃进去过,向导说这个名字是“死亡之海”,也有人说直译应该就是“无法生还之地”的意思。
巴岱先生却说:
“解释有很多种,每个民族都说这是用他们自己的文字起的名字。我倒是比较喜欢维吾尔文里的一种翻译,说‘塔克拉玛干’的意思就是‘故居’。”
我的心在猛然间翻腾惊动了起来,原来谜底就藏在这里,这是多么贴切的名字!
今日荒寂绝灭的死亡沙漠原是先民的故居,是几千年前水草丰美的快乐家园,是每个人心中难以舍弃的繁华旧梦,是当一代又一代、一步又一步地终于陷入了绝境之时依然坚持着的记忆;因此,才会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这一种在心里和梦里都反复出现的乡愁了吧。
故居,塔克拉玛干,在回首之时呼唤着的名字。此刻的我在发声的同时才恍然了悟,我与千年之前的女子一样,正走在同样的一条长路上。
有个念头忽然从心中一闪而过,那么,会不会也终于有那样的一天?
几百几千或者几万年之后,会不会终于有那样的一天?仅存的人类终于只好移居到另外的星球上去,在回首之时,他们含泪轻轻呼唤着那荒凉而又寂静的地球——别了,塔克拉玛干,我们的故居。
经 卷
1
一九八九年的秋天,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博物馆里,我能够体会那位年轻的博物馆员心中的焦急。她说:
“怎么办呢?眼看着这些经卷就要全毁在这儿了!”
在那间阴暗而又不通风的房间里,见不到任何防潮或者调温的设备。在我们眼前,如山般堆积着的是每一部都用蓝色丝绢当封皮,仔细地包了起来的长方形经卷。不但塞满了所有的架子,连沿着墙边的地上也堆得都是,感觉上就好像是座窒闷的大山一样。
年轻的博物馆员说:
“都好几年了!就这么堆着。再不想办法的话,很快就会坏了的啊!”
2
陪着远客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得到院方的热忱款待,给我们展示了院藏的蒙古帝后画像。在小小展览室的一角,还放了两部刚从库房里拿出来的经卷。像这样的手抄经卷,通常是用泥金或者珊瑚粉写在黑色或者蓝色的底上,做成连接的册页。最外部是两块夹经板,雕刻师与画工就在这两块板上大显身手。有的更是用丝线一针一针绣出来的,光彩夺目,令人不敢逼视。展览室外站着警卫,展览室内的温度湿度都有各种仪器来监控,每个人在进入的时候,还要戴上一层薄薄的白色纸质口罩,讲话只能轻言细语,心情也诚惶诚恐了起来。
后来和一位在台北故宫工作过的朋友聊天,说起那令我印象深刻的口罩,朋友却说:
“戴口罩除了是要保护文物,避免受到参观者呼吸里的湿气影响之外,也是有保护参观者的作用。因为,就算设备再好,长年放在库房里的文物,还是会藏着一些霉菌的。”
3
一九九〇年的秋天,第一次到乌兰巴托的甘丹寺拜谒,同行的蒙古朋友向喇嘛请求了之后,我们得以参观寺中的藏经室。那天天气虽然寒冷,阳光却很好,透过玻璃窗照进来,满墙的佛幡和满室的经卷都光芒灿烂,仿佛走进了一个千彩万色的世界。
接待我们的喇嘛举止从容,他先为我们大略介绍了一下院藏经卷的内容,然后再从架上拿下一卷,平放在我们眼前的长桌上。
经卷外面包着的是一种金黄色的锦织方巾,要先把这层锦织打开,里面才是经卷,打开经卷的夹经板,那雕工繁复精致华美到无法形容的艺术珍品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我注意到喇嘛在拿取经卷的时候非常慎重,一层一层打开的时候,也非常仔细,可是,他向我们展示的时候却毫无戒心,就像是在向我们展示一件他日日都会用到的对象一样。
在回去旅馆的路上,我把心中的疑问向朋友说了,朋友是这样回答我的:
“本来这就是他们日日都会诵读的经卷,藏经寺就是寺里喇嘛的图书馆。当然,这些经卷都是宝物。可是,你要知道,常常有人诵念的经卷才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宝物,不容易坏的。”
大雁的歌
这是蒙古草原上的一首歌,据说是从十七世纪末就开始流传的民谣。老人在草原上看见飞过的大雁,觉得似曾相识,不禁仰首问:
“大雁啊!大雁!那有着碧蓝海洋围绕的南方,是多么温暖和美丽,你为什么不在那里长久停留?非要千里迢迢地飞回来呢?”
大雁听见了,就低飞下来回答:
“春天花开了,草原就是幸福的天地,有一种呼唤带领我们回到家乡。”
老人俯首行礼,表示欢迎和祝福。大雁正要展翅飞离,忽然又回头轻声询问:
“我记得你原来是个多么年轻的少年啊!怎么变得这么老了呢?”
老人长叹一声说:
“大雁啊!大雁!不是我自己愿意变老的,实在是这时光无止尽的循环,让我不得不老去的啊!”
我是在前年春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在台北中广的录音室里,从蒙古来的巴达拉老先生应邀演唱几首蒙古民谣。每唱一首,他都要先向我解说歌词的大意,好让我能向听众作简短的介绍。帮我们两人翻译的杜布兴巴雅尔,在翻译到这首歌最后一段的时候,忽然停顿了下来,哽咽不语。
这位朋友处事一向沉稳,我很少看到他这样失态过,不禁有点讶异。可是,在几秒钟之后,等到他终于把最后一段歌词翻译出来的时候,我也有了相同的感受。
“大雁啊!大雁!不是我自己愿意变老的,实在是这时光无止尽的循环,让我不得不老去的啊!”
老先生站在录音室中间,穿着蒙古长袍,仰首高歌,好像就是那个站在草原上的老人,仿佛空中真有大雁飞来与他应答,高亢苍凉的歌声,唱出了生命的疼痛与无奈。
每一首会流传下来的歌,应该都是从我们心里最痛的地方唱出来的吧?
巴达拉老先生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在草原上采集与传授蒙古民谣。他说:
“我想,人活着总有些天真的理想。这么美丽的歌谣既然是祖先从心里面唱出来给我们听的,那么,就让我们再把它唱进子孙的心里面去吧。”
去年八月,巴达拉老先生因为急病在乌兰巴托逝世。我一直想向他表达的谢意,以及台北的朋友们想为他录制专集的心愿,如今都再也没有实现的机会了。
当大雁再飞回北方去的时候,草原上有谁能够再回答它呢?
父亲教我的歌
从前,常听外婆说,五岁以前的我,是个标准的蒙古娃娃。虽然生长在中国南方,从来也没见过家乡,却会说很流利的蒙古话,还会唱好几首蒙古歌,只可惜一入小学之后,就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的了。隐约感觉到外婆语气里的惋惜与责备,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对一个太早入学,智力体力都不如人的孩子来说,小学一二年级可真不好念哪!刚进去的那些日子里,真可以说是步步惊魂,几乎是把所有的力气,把整个的童年,都花在追赶别人步伐,博取别人认同的功夫上了。
要班上同学愿意接受你并且和你做朋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偏偏还要跟着父母四处迁徙。那几年间,从南京、上海、广州再辗转到了香港,每次都要重新开始,我一次又一次地更换着语言,等到连那些说广东话的同学也终于接纳了我的时候,已经是小学五六年级了。我普通话标准、广东话标准,甚至连他们开玩笑时抛过来的俏皮话,我也能准确地接招还击。只是,在这样长时间的努力之后,我的蒙古话就只剩下一些问候寒暄的单句,而我的蒙古歌则是早已离我远去,走得连一点影子也找不回来了。
那以后外婆偶尔提起,我虽然也觉得有点可惜和惭愧,但是年轻的我,却不十分在意,也丝毫不觉得疼痛。
那强烈的疼痛来得很晚,很突然。
一九八九年夏末,初次见到了我的蒙古原乡。这之后,一到暑假,我就像候鸟般地往北方飞去。有天晚上,和朋友们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聚会,大家互相敬酒,在敬酒之前都会唱一首歌,每一首都不相同,都很好听。当地的朋友自豪地说:鄂尔多斯是“歌的海洋”,他一个人就可以连唱上七天七夜也不会重复。
那高亢明亮的歌声,和杯中的酒一样醉人,喝了几杯之后,我也活泼了起来,不肯只做个听众,于是举起杯子,向着众人,我也要来学着敬酒了。可是,酒在杯中,而歌呢?歌在哪里?在台湾岛,我当然也有好朋友,我们当然也一起喝过酒,一起尽兴地唱过歌。从儿歌、民谣一直唱到流行的歌曲,可以选择的曲子也真不算少,但是,在这一刻,好像都不能代表我的心,不能代表我心中渴望发出的声音。
此刻的我,站在原乡的土地上,喝着原乡的酒,面对着原乡的人,我忽然非常渴望也能够发出原乡的声音。
不会说蒙古话还可以找朋友翻译,无论如何也能把想表达的意思说出七八分来。但是,歌呢?用原乡的语言和曲调唱出来的声音,是从生命最深处直接迸发出来的婉转呼唤,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也无法转换的啊!
在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疼痛与欠缺,好像在心里最深的地方纠缠着撕扯着的什么忽然都浮现了出来,空虚而又无奈。
因此,从鄂尔多斯回来之后,我就下定决心,非要学会一首蒙古歌不可。真的,即使只能学会一首都好。
但是,事情好像不能尽如人意。我是有几位很会唱歌的朋友,我也有了几首曲谱,有了一些歌词,还有人帮我用英文字母把蒙文的发音逐字逐句地拼了出来。但是,好像都没什么效果。看图识字的当时,也许可以唱上一两段,只要稍微搁置下来,过后就一句也唱不完全了。
一九九三年夏天,和住在德国的父亲一起参加了比利时鲁汶大学举办的蒙古学学术会议。在回程的火车上,父亲为朋友们轻声唱了一首蒙古民谣,那曲调非常亲切。回到波昂,我就央求父亲教我。
父亲先给我解释歌词大意,那是个羞怯的青年对一位美丽女子的爱慕,他只敢远远观望:何等洁白清秀的脸庞!何等精致细嫩的手腕!何等殷红柔润的双唇!何等深沉明理的智慧!这生来就优雅高贵的少女,想必是一般平民的子弟只能在梦里深深爱慕着的人儿吧。
然后父亲开始一句一句地教我唱:
采热奈痕查干那!
查日布奈痕拿日英那!
……
在起初,我虽然有点手忙脚乱,又要记曲调又要记歌词,还不时要用字母或者注音符号来拼音。不过,学习的过程倒是出奇的顺利,在莱茵河畔父亲的公寓里,在那年夏天,我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学会了一首好听的蒙古歌。
回到台湾岛之后,好几次,在宴席上,我举起杯来,向着或是从北方前来做客的蒙古客人,或是在南方和我一起成长的汉人朋友,高高兴兴地唱出这首歌。令我自豪的是,好像从来也没有唱错过一个字,唱走过一个音。
一九九四年春天,和姊妹们约好了在夏威夷共聚一次,有天晚上,我忍不住给她们三个唱了这首歌。
是在妹妹的公寓里,南方春日的夜晚慵懒而又温暖,窗外送来淡淡的花香。她们斜倚在沙发上,微笑注视着我,仿佛有些什么记忆随着这首歌又回到了眼前。
我刚唱完,妹妹就说:这个曲调很熟,好像听谁唱过。
然后,姊姊就说:
“是姥姥!姥姥很爱唱这首歌。我记得那时候她都是在早上,一边梳着头发一边轻轻地唱着这首歌的。”
原来,答案在这里!
姊姊的记忆,填补了我生命初期的那段空白。
我想,在我的幼年,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清晨。当外婆对着镜子梳头的时候,当她轻轻哼唱着的时候,依偎在她身边的我,一定也曾经跟着她一句一句唱过的吧?不然的话,今天的我怎么可能学得这么容易这么快?
我忽然安静了下来,原来,答案藏在这里!转身慢慢走向窗前,窗外花香馥郁,大地无边静寂,我只觉得自己好像刚刚走过一条迢遥的长路,心中不知道是悲是喜。
一切终于都有了解答。原来,此刻在长路的这一端跟着父亲学会的这首歌,我在生命初初启程的时候曾经唱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