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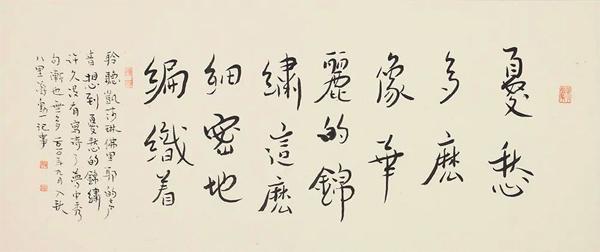

小时候,还没开始认字,就喜欢听母亲说故事。《白蛇传》《西游记》《封神榜》,都是听来的。母亲说故事的能力很好,这些故事大概也是她从小就听来的。家中长辈会有说不完的故事,街头巷尾,也有大家说不完的传说。庙口瞎子,拿一把三弦,叮叮咚咚,唱的、说的,也是“三国”“水浒”“封神”,戏台上反反复复演的,也还是民众早已耳熟能详的这些传说。
“传唱”如果也是“文学”,应该比文字“书写”早得多,“听”也比“阅读”早得多。
一直怀念听来的故事,片段片段的故事,常常不完整,有时岔出主题,又自成一章。语言的活泼自由,语言的多样表情、多样隐喻,常是文字所不及。文字一个萝卜一个坑,语言却天马行空,同一个传说,每次听,都不一样,不同的人说,也不一样。
这是“传说”的魅力。
一九八八年,我写下一些传说,大半是故事原型添油加酱,希望有口传的活泼。
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传说》后来增添几篇,出版了《新传说》,之后,又增添几篇,变成《新编传说》。“新”“新编”大概都是觉得“传说”可以一直演绎下去。“三国”的故事,后来就发展出庞大的“演义”。
联合文学找出这三十年前的旧作,要重新出版。
我重读一次,觉得有趣,文字中的《民生报》早已停刊,高雄《人鱼记事》里也已是三十年前旧事。
“传说”总是要一说再说,白蛇传说了一千年,还觉得是身边街坊邻居的事,白蛇要继续对抗僵化道德的压迫,法海总要把弱势者压到雷峰塔下。
可以“讲古”,也可以“论今”,这是我爱“传说”的原因吧!
重新整理了一次,把旧编辑整理的“导读”放在书末,作为后记,还是读故事原文比較有趣。
“新”和“新编”都拿掉,还原最初的书名,就是“传说”。
“传说”很古老,“传说”也可以很新,即使年轻读者也读得出现代的心事吧。
二○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蒋勋于北美旅邸
庄子与蝴蝶
那个时代,美丽是有罪的。
凡被认为具有“美”的动机或目的的行为,都算触犯了刑法。
法律的条文订得极其细密,刑罚的方式也很多。因此,弄到最后,大部分的民众只能努力记住刑罚的条文,譬如说:“头发故意弯曲造成美感者,受笞刑五十”之类(有关“头发美”而受罚的判例竟多达四千七百一十五种,受罚的方式也都因罪之轻重完全不同)这样细密的条文,自然要耗尽人们的力量,大家在努力记住这繁复到惊人的“美的禁令”之时,早已筋疲力竭,也没有人再有任何余裕去追问“为什么美是有罪的?”这样立法的主要核心问题了。
大约,法律愈繁复,条文愈细密,愈使人只能努力奉行,对于最初订定法律的动机与目的,都无从查证思考了。
庄子走过城门口的时候,正看到一次对蝴蝶的处刑。
蝴蝶的美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那在空中成日招展炫耀的翅翼,色彩缤纷,穿梭飞动于花丛之间,在一个“美丽”有罪的时代,自然难逃刑罚的厄运。
有关蝴蝶的判决是众多判例中较简易的一种,因为蝴蝶的“美”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共识”的基础上,检察官省却了许多寻找犯罪动机与犯罪事实的复杂过程。在判决时,经过民众的叫嚣,“众口铄金”,蝴蝶的罪名也就成立了。但是,大法官为了维持法庭的尊严,还是照例起立,站在高高的台上,三次宣读刑罚的方式,三次接受民众一致的喝彩,使整个判决理性而合法。
蝴蝶的美因为有民众共识的基础,除了作为“美”的惩罚的个例之外,也有杀一儆百的训诫的作用,因此,在处刑上也特别的重。
蝴蝶的美是处以“针刑”的。
有人说,针刑来源于植物学家们的做标本,是一种固定蝴蝶尸体的方法。
但是也有人认为针刑的由来已久,自有人类以来,自人类使用针这种工具以来,便常有蝴蝶被针穿刺钉在墙上。
头脑精明的人甚至发现,最初人类把蝴蝶用针钉在墙上,正来源于对一种“美”的复杂心情,爱之恨之,便形成了一种处刑的方式。但是,这一部分,在思想上已触犯了“美”的禁忌。脑中存在对“美”的幻想,很可能被处以“剜脑”的酷刑。那头脑精明的人便也只敢私下想一想,至于在蝴蝶的审判会上,还是要跟着众人一起吆喝“蝴蝶死!”“蝴蝶死!”的。而且,可能是为了抵抗脑中那存留着的对“美”的恐惧,便要越发叫得比别人声音更大,结果竟被认为是忠贞的“反美丽派”的基本教义信仰者了。
总之,蝴蝶的被处以针刑是确定的了。
用一根细长的银针,准确地穿刺过蝴蝶的心脏,钉死在一张与城墙同高的木制宣示板上。
据说,蝴蝶的心脏极小,因此,这处刑的工作并不容易。首先必须使银针的针尖确实小过蝴蝶的心脏,以免伤害到心脏以外的部分,使执刑的结果违反判决书上注明的细节。在那个一切要求理性的时代,包括犯罪者在内,对执刑的方法是否与判决书中规定的相合,都有认真的要求,执刑的不准确常常引起犯罪者家属缠讼多年的控告,使执法者不得不小心翼翼。
因为对“美”的处刑,连带发展出了精密的法律观念、理性的态度;连带使医学研究有了空前的进步,这些,都算是在“美丽”的惩罚下一种明显的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吧。
至于蝴蝶心脏的学术论述,以前在医学界,是从来没有被提出讨论的;现在却成为热门的话题了。不但在医学界,凡是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公众的场合,也都以讨论蝴蝶的心脏为一种先进的表示。
蝴蝶心脏的准确位置也在医学上做了精密的研究,使银针穿刺时不致偏差,误伤了其他部位。
庄子经过城门口时,看到数以万计的蝴蝶被钉在板上,各种种属不同的大小蝴蝶,各种不同的色彩与斑纹的蝴蝶,有的处刑多日,已成僵硬的尸体,有的刚处刑不久,犹缓慢扇动那美丽的翅翼,仿佛要带着那刺穿心脏的银针,努力飞去不可知的世界。
许多人从河岸上牵着陶罐跑来。许多人搁下了正在缠结的网坠跑来。许多人从江心把船划拢了岸。他们不知道这傻大个老七发生了什么事。
“我看见褒姒了!”
老七气喘吁吁地说。
他静了一下,沉住气,等待大伙的反应。
“哗!”大伙哄笑闹作了一团。
老姜是一个年逾八十的船夫,一手烂泥,正在纤他的船呢,没好气,抹了老七一脸泥。
大家一哄而散,留下老七一个人。
渭水汩汩,夹着上游的雨雪。
渭水流进了镐京,绕着城转了一圈,灌溉了许多梨花、桃花,溶溶汤汤,流进了皇宫。
褒姒坐在花前,春末的花开得缤纷如霞彩。
梨花白里带淡淡的青。薄到有一点透明,细细的雨丝好像花的泪光,给一点点翠绿的花蒂托着。一树一树,一面开一面四面飘散。
桃花热闹极了,像一树深红浅红的血点。
“褒姒!”
幽王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一片桃林、梨树,四散飞扬的花瓣。而褒姒坐着,一动也不动,他怕这美丽的女人又要病了。
“还记得你上次的病吗?”幽王卸了屦,也盘膝坐在一块石上。
褒姒上次的病来得怪极了。她无端端站在水边,看着水,水中的流云,一刹那一刹那移转,她便呆住了,不肯走。
侍仆们急坏了。
幽王急急赶来——
“褒姒,你怎么了?”
这个天下人都宠眷的女子,这美丽到使人心痛的女子,呀,她为何这样忧愁呢?
幽王急忙中,要靠近褒姒,一不小心,袍袖给树枝挂住,“嘶”地一声,袍襟裂开了。
褒姒回过头,细听了一下,水里不断流去的是这锦绣上的流云吗?
她笑了。
河水一阵晃漾,幽王呆住了,他从没有看过这样的笑容。
那是可以使人死亡的笑容啊!
“据说,以后幽王爷就买了成千上万最好的蜀锦,每天让宫人们撕给褒姒听。一匹一匹上好的锦绣呢,像春天的晚霞一样,摊在褒姒面前,摊得一地都是,褒姒就坐在锦绣中间,听人撕锦,她就笑了。宫里都是撕锦缎和褒姒的笑声——”
老七说故事的本领并不好,河滩上的人有点厌恶他把褒姒的病翻来覆去地讲。
“褒姒确实是病了,可是撕锦的事可没听过。”
老姜是实事求是派,不喜欢老七的夸张,便抗议了。
天上有大雁飞过,河滩上的人常常用大雁的往南飞或往北飞来判断春天和秋天的来临。
呀呀叫着的大雁一字排开,往南而去。
一直到雁迹都不见了,褒姒還站在满地落叶的庭院中。
宫里有一点耸动。行人说是幽王怕褒姒受寒,从骊山那边引了温泉来。用粗大的麻竹,外面一层一层裹了稻草,翻山越岭,就在宫殿的北隅,建筑了新的石池。泉水已经引到,冒着腾腾的热气。但是,有几处麻竹管接缝不严,夹进了泥水,水质有点黄浊,幽王为此发怒,正在补救工程。
有人说,这耸动还是因为与犬戎的战争。
空中有一点淡淡飘来的硫磺的气味。
秋后的寒林,露着秃枝,在不知是山岚还是磺气的淡烟里流动。
“听说在新泉宫殿四周种满了香花呢!有栀子、兰、蕙、桂花,有杜衡、茑萝、菟丝,有含笑、芙蓉……”
婢女们纷纷来传报新泉宫殿的铺张华丽。
“可是西边的战事呢?”
褒姒不知为什么想起西边犬戎的战争,听说杀人盈野,遍地都是衔着人头的野狼。
“犬戎的孩子在马上执长戈冲进城来,连孩子们都一翻就上马背,好像是一个人头马身的怪物呢,他们连鞍鞯都不用,也不用笼络,光秃秃一个马背,一翻就上去了——”
老姜磕了一磕他的烟管,谈起他亲身经历的一次犬戎大战,他总是兴味不浅。
“可是褒姒生病了呢——”
老七几次想把话题抢回来,都给老姜偏执的白眼给堵回去了。
老七毕竟只看了褒姒一眼,甚至连一眼都说不上,应当说是“一瞥”。就那么一恍惚,在幽王车辇的旁边,车辇上的帘幙给春天的风吹开了一缝,正巧看到了褒姒,像一尊出巡的神像,端端坐着。
几年来,老七能反复说的也只是那“一瞥”的种种。但是,老姜的犬戎是有情节、有动作的故事。老姜讲着讲着,口沫横飞,半蹲着如骑马,嗒嗒嗒,往前冲去。一个筋斗,翻过来,左臂勒住马鬃,右臂变作一把长刀,往犬戎的头上一劈,“豁”,连头带身,劈成了两半,“一半往前走了几步,一半遗留在原地——”
“哪有这种杀法的!”
老七也找到了破绽,立刻攻击起老姜。
“怎么没有!”老姜红着脸辩驳,“硬是身子给劈成了两半,一半倒下,另一半拿着刀还往前冲。我亲眼看见的,你个傻蛋,你不相信,你试试——”
老七和老姜便在河滩上作势追杀起来。一大群小孩跟着起哄,女人手执窑门的木闩板追打孩子。远看仿佛一队军士,热热闹闹上阵杀敌去了。
但是,褒姒病了。
城里最好的乐师都请遍了。七弦琴,二十五弦的瑟,风动竹篁制成的笛,铜矿回应地震发出巨响的钟,石玉的精魂碾磨成的磬,一一都试了。然而,褒姒一日一日病下去。她看着林木中幽荡的烟云,天上飞去远逝的大雁,那一匹一匹撕碎的锦绣,锦绣上碎裂的云霞,她不进饮食,不睡眠,只是发呆——
“大王,边事紧急啊!”
朝臣们一次一次上奏。
幽王守在褒姒身边,她连新泉宫殿也不愿意去看一看。
“褒姒——”
幽王一次一次呼唤这名字,他想,一遍一遍把她唤回来。辽阔的帝国的疆域,有什么比这美丽女子的心更难唤回的呢。他颓然了。
把帝国舍弃而去
背负起历史昏君的罪名
美丽的毁灭
春夏繁华之后
便是严寒雨雪
那城脚瞎子唱的歌,被诤臣们采录了,在大殿上唱给他听,他怎么会不懂呢!
“历史上可曾也有过一个人,觉得褒姒生病是和犬戎的战事同等重要的?”
幽王胡思乱想了,他有长而入鬓的眉眼,仍然年轻的如漆的黑发。
他的形貌一般被误解了。其实他并不粗暴,也许是所有帝王中最不粗暴的一个吧。
他记得刚认识褒姒的时候,褒姒喜欢听瓷器碎裂的声音。她跟他说,静下来,听,那是土經过火的锻炼以后近于玉石的声音,可是它们碎裂开来了,是那坚如玉石的身体又想回复成为土。
——褒姒拾回了许多为人丢弃的瓷片。把耳朵附在那断裂的土痕上,听着听着。她要幽王一起听。那些土的分子在聚散离合,那些土的分子,被水凝聚,用火的高温固定了,然后,它们又被震摔的巨力断裂开;它们曾经牢牢拥抱紧挤在一起,却还是分离散乱了,它们分离时有叫声……
“褒姒!”
幽王轻轻呼唤着。
“江山与美丽,我都守护不住。”
宫殿里堆满了碎裂的瓷片和撕开的锦缎。
那布帛撕裂的一声,好像天地初始,混沌中有了光。
那土器碎开,原是大地震动啊!
褒姒,我们是历史上最坏的男女
我们听丝绸的哭泣,
我们听瓷片嚎啕;
我们要烽火的光焰,
只为了赞颂女子的美丽;
褒姒,你答应我,
让我燃起烽火,
我要向世人传警布告:
褒姒病了!
那烽火连接着燃起,军士们从四处涌来,戈矛刀戟都十分整齐。周帝国戒备严密,将士们铠甲庄严,镐京城在一夜间聚集了最好的虎贲之军。
告急的烽火,使远在雁门一带的边将都看到了。他们用快马传送玉符。一个驿站接一个驿站,驿使们鞭断了坚韧的皮革,马疲累而死,倒在沟壑中。
老七坐在河边,用锋利的菜刀削刮一支长矛。他不知道为什么,从睡梦中惊醒,看到满天火光,镐京城都在赤焰中。
他抓起一支白杨木,努力削刮着。他心里焦急,甚至满面泪水,一路沿着河滩呼叫:“烽火,烽火,满天都是烽火。”
镐京城照得如同白昼,将士待命。
幽王与褒姒坐在宫阙的高观上,白衣素服。
幽王站在城头,看连绵不断的烽火与还在陆续到达的各地的军士。
他用牛血歃了鼓,然后用力击打。咚咚的鼓声使黑压压一片人众都安静了下去。
而后,他流着泪,大声宣告:
“褒姒病了!”
老七刚刚提着白杨木的长矛赶到。从众人的缝隙中拼命往前挤着,恰巧听到幽王的宣告。
他一吓,愣住了,长矛从手中掉下地。
老七忽然坐地大哭起来。
那哭声与烽火,一夜不停,排列整齐的周帝国全部的军士都肃敬站立。
据说,那一夜,所有镐京城的瓷器都碎裂成片,所有的丝绸锦缎也都无故从头撕成了两半。
这是周帝国灭亡前一个小小的传说故事。
主流的史学研究都把幽王定义为“暴君”,褒姒被定义为“祸水”。
数千年下来,主流的观点从来没有人怀疑。
传说里的老七因此十分重要,因为只有他,真正看到了褒姒。
褒姒坐在车辇中,风微微吹开帘幔,帝国繁华像一个春天的花季。
只有幽王和老七惦记着,除了战争,历史还有大事:褒姒病了……
关于屈原的最后一天
渔父从屋中出来,用手掌做遮檐,挡住了强烈的阳光,四下张望了一遍。
这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酷热的夏天。还只是初夏,太阳整日照着,除了靠近河滩附近还有一点绿,山上的树木丛草全都枯死了。
静静的汨罗江,流着金黄灿亮的日光。
静静的,好像所有的生命都已经死灭了。
渔父侧耳听了一下,混沌中好像有一种持续的高音,但是分辨不出是什么。
他看了一会儿靠在岸边的竹筏,铺晒在河滩石头地上的鱼网,一支竹篙,端端插在浅水处。
他在屋角阴影里坐下,打开了葫芦,喝了一回酒,坐着,便睡着了。
他的年岁不十分看得出来。头发胡须全白了,毛蓬蓬一片,使他的脸看起来特别小,小小的五官,缩皱成一堆。在毛蓬蓬的白色须发中,闪烁着转动的眼睛,嗫嚅的嘴唇,一个似有似无的鼻子,苍黄的脸色,脸色上散布褐黑的拇指般大小的斑点。
他在酣睡中,脸上有一种似笑的表情,间歇的鼾声吹动着细白如云絮的嘴须,嘴须上沾湿着流下的口涎。
他像一个婴孩,在天地合成的母胎里蛹眠着。
“或者说,像一个永远在蛹眠状态,不愿意孵化的婴孩呢!”屈原这样想。
楚顷襄王十五年五月五日。
屈原恰巧走到了湘阴县汨罗江边渔父的住处。
房子是河边的泥土混合了石块搭成的。泥土中掺杂了芦草,用板夹筑成土砖,垒筑成墙。
墙上开了窗,用木板做成窗牖。屋顶只有一根杉木的大梁,横向搭了条木的椽子,上面覆盖禾草。
土砖造的房子和渔父邋遢长相有一点近似,都是土黄灰白混混沌沌一堆,分不清楚头脸。
屈原走来,猛一看,还以为那渔父也是用泥土混合着河边石头堆成的一物。
直到他听到了鼾声——
那鼾声是间歇的,好像来自一个虚空的深谷,悠长的吐气,像宇宙初始的风云,忽忽的,平缓而安静,一点也不着急。
山野林间无所不在的蝉则是高亢而激烈的,持续着不断的高音。
渔父从懵懂中昏昏醒来,他觉得那持续不断的高音吵噪极了,有一点生气,不知道这些虫子为什么要那样一点不肯放弃地叫啊叫的。
睡了一觉,下午的日光还是一样白。
他一身汗,湿津津的,恍惚梦中看到一个人。
一个瘦长的男人吧,奇怪得很,削削瘦瘦像一根枯掉的树,脸上露着石块一样的骨骼。眉毛是往上挑的,像一把剑,鬓角的发直往上梳,高高在脑顶绾了一个髻,最有趣的是他一头插满了各种的野花。
杜若香极了,被夏天的暑热蒸发,四野都是香味。这男子,怎么会在头上簪了一排的杜若呢?
渔父仔細嗅了一下,还不只杜若呢!这瘦削的男子,除了头发上插满了各种香花,连衣襟、衣裾都佩着花,有蘼芜,有芷草,有鲜血一样的杜鹃,有桃花,柳枝。渔父在这汨罗江边长大,各种花的气味都熟,桂花很淡,辛夷花是悠长的一种香气,好像秋天的江水……
“你一身都是花,做什么啊?”
渔父好像问了一句,糊里糊涂又睡着了。
空中还是高亢蝉声混合着模糊鼾声的间歇。
“在天地混沌的母胎中,他好像一个婴孩。”
屈原一早在江边摘了许多花,在水波中看了一会自己的容颜,这样瘦削枯槁,形容憔悴,一张脸被水波荡漾弄得支离破碎,在长河中流逝;一张满插着鲜花的男子的脸。
高余冠之岌岌兮,
长余佩之陆离;
制芰荷以为衣兮,
集芙蓉以为裳。
屈原歌唱了起来,手舞足蹈,许多花朵从发上、身上掉落下来。近江岸边的花被风吹入江中,在水面浮漂,鱼儿以为是饵,便“泼剌”前来捕食,平静的水面荡起一阵波浪。
渔父听过军士们的歌声,是秦将白起进攻楚国京城郢都时的歌,军士们手操刀戟戈矛,一列一列,雄壮威武,张大了口,歌声十分嘹亮。
郢都后来被秦兵破了,老百姓扶老携幼往南逃亡。渔父坐在山头上,看强盗们出没,劫夺老百姓的衣物。老百姓也彼此争吵,男人殴打女人,女人殴打孩子。
渔父打开酒葫芦,呷了一口。
举世皆醉,我独醒;
举世皆浊,我独清。
屈原又唱了一遍。
白花花的阳光,使一切影像看来都有一点浮泛,仿佛是梦中的事物,历历可数,可是伸手去捉,又都捉不住。
他头上身上的花飞在空中,花瓣并不向下坠落,而是四散向天上飞扬而去。
“郢都破了呢!一根骨头接一根骨头,足足排了有好几里长,当兵的都被活活坑杀了,一个坑一个,像萝卜一样,埋到颈部,喏,这里……”这人用手在颈部比画了一下,又说:
“埋到这里,呼吸也不能呼吸,所有的气都憋在头部,下不去。头被气鼓起来,变成一个紫胀的大球。喏,像一个大茄子。还要更紫,紫黑紫黑的。眼睛也凸出来了,然后大概五、六个时辰,眼球就‘啵一声暴了出来。这人就完了。憋着的气,‘咻——长长地从口中吐出。”
渔父笑了一笑,他坐在山坡上,太阳极好,他把火灰踏灭,便又上路逃亡去了。
紧接着几天,是楚国阵亡的兵士们列队从山坡下过。他们还走去江边,在浅滩里洗他们的脖子。因为头已经被砍掉了,那脖子洗着洗着,便流出内脏的血来,流成长长殷红的一条,在江水里像一条美丽的红色的丝绸。
出不入兮,往不返,
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那花在空中散开,像战场上的血点,装饰着华丽的天地。屈原也追上去,跟那没有头的年轻男子说了一会话。他们对答着有关人死亡以后,好像出了家门回不来的感觉。一个没有头颅的年轻男子,便茫然地在平原大地上彷徨徘徊。走来走去,到处都是路,可是怎么走也走不回家啊!
据说,屈原是这一天死的。跳完了舞,唱完了歌,披头散发,一身凋败野花的三闾大夫,爬在江岸上,哭了又哭。哭得汨罗江都涨了潮,水漫向两边,连山坡的坡脚都被淹住了。
渔父一觉醒来,吓了一跳,他的酒葫芦漂在水面上,摇啊摇的,像一只船。
屈原的身体随水波流去,可是水势并没有停止,继续向两岸坡地淹漫。
渔父拾起葫芦,涉水走去竹筏。拔起了竹篙,一篙到底,竹筏便飞一样向江心划去。
屈原的身体,被香花浮载着,像一个很会游泳的人的身体,一直在江浪的顶端浮沉。
屈原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渔父沙哑的声音: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我足。
渔父的歌随着屈原的死亡在民间流传。此后每年五月五日,人们聚在江边野餐,吃包好的粽子,都会谈起传说里那一个爱花的男子的死亡,以及渔父最后唱给他听的歌。
歌词其实很简单,大致是说,“江水清洁,我就来洗头发。江水浊污,我就洗洗脚。”
渔父应该是无意的,不知为什么以后的文人加注了许多牵强附会的隐喻。
(选自《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