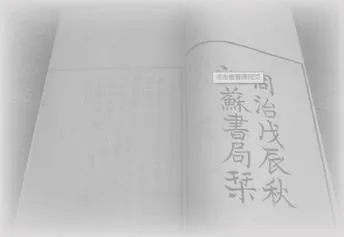
清中叶,地方大员在各省纷纷设立官书局,刊刻传统的经史子集类书,以重建地方文教秩序。对此,方宗诚记载道:“胡文忠在湖北首开书局,刻《读史兵略》《弟子箴言》。曾公在安庆开书局刻《王船山先生遗书》,在金陵刻《四书》《十三经》《史记》《汉书》。吴仲宣漕督在淮上刻《小学》《近思录》诸书;丁雨生中丞在苏州刻《通鉴》《牧令书》诸书;马谷山中丞在浙江刻钦定《七经》等书;左季高宫保在福建刻张仪封所编诸大儒名臣书;何小宋中丞在湖北刻《十三经》经典释文、《胡文忠公遗集》等书;吴竹庄方伯在安庆刻《乾坤正气集》及各忠节书;李少荃节相在金陵刻《名臣言行录》并朱批谕旨等书;丁稚黄中丞在山东亦开局刻《十三经》,皆有益世教也。”可知,官书局在创设之初重点刊刻经史类书。在传统经史子集类书中,官书局为何重点刊刻经史类书?刊刻了哪些经史类书?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晚清官书局的认识。
一、刊刻经史类书之动因
1.无书可读的现实困境太平天国所到之处,大肆焚烧儒家典籍,“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致使各地官方藏书尽数被焚毁,严重地挑战着儒家文化的权威和尊严。莫友芝于同治四年(1865)五月致书曾国藩谈及官方藏书被毁的情况,称:“奉钧委探访镇江、扬州两阁《四库》书,即留两郡间二十许日,悉心咨问。并谓阁书向由两淮盐运使经营,每阁岁派绅士十许人,司其曝检借收。咸丰二三年间,毛贼且至扬州,绅士曾呈请运使刘良驹筹费,移书避深山中,坚不肯应。比贼火及阁,尚扃钥完固,竟不能夺出一册。镇江阁在金山,僧闻贼降至,亟督僧众移运佛藏,避之五峰下院。而典守阁书者,扬州绅士,僧不得预闻,故亦听付贼炬,惟有浩叹。比至泰州,遇金训导长福,则谓扬州库书虽与阁俱焚,而借录未归与拾诸煨烬者,尚不无百一之存。”此外,各府州县学的书籍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出现无书可读的状况。同治六年(1867),江苏学政鲍源深上奏描述了江苏省学府书籍被毁的情况,称:“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乱后虽偶有书肆,所刻经书俱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苏省如此,皖浙江右诸省情形谅亦相同。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同年,浙江巡抚马新贻上奏浙江省书籍的存毁情况,称:“浙省自遭兵燹,从前尊经阁、文澜阁所存书籍均多毁失。士大夫家藏旧本,连年转徙,亦成乌有。”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上奏:“(湖北)三次失陷,造乱最深,士族藏书散亡殆尽,各处书板全毁。”可以说,官方藏书在战乱中被付之一炬,鲜有存者。
私家藏书亦未能幸免,藏书世家数辈子积累的心血付之东流。据《纪闻类编》载:“余生不幸,虽未坑儒,业已焚书。所见者洪逆之流之乱所至之地,倘遇书籍,不投之于溷厕,即置之与水火,遂使东南藏书之家,荡然无存。”又据《苏台麋鹿记》载:“即如书籍贼皆无所用……或抛散一帙,或抽弃一册,甚至顺风扯去,片片飘扬,灰尘珲厕中时有断简残编,见之欲哭。”对此,美国学者艾尔曼写道:“学者们死了,著作佚散了,学校解散了,藏书楼毁掉了,江南学术共同体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消失了。……图书业空前凋敝,一度繁荣兴旺的出版业如今已所剩无几。此时此刻,江南一带学术精英已是烟消云散。”
可以说,太平天国对官私藏书的焚毁,导致战后地方文库空虚,士人无书可读。因而战争结束之后,地方官员欲重建地方文教秩序,解决地方上文库空虚的问题,纷纷设立书局刊刻书籍。这是地方官书局设立的现实原因,亦是经史类书大量刊刻的背景。
2.“窥圣学之原”“达政事之要”
方宗诚称:“粤贼之兴,奏设忠义局,委官绅采访者,亦自胡文忠在湖北始;其后各省援以为例,使忠魂义魄不致泯没,而曾公又扩而大之,藉以延致三江贤士,不但激扬正气,且以培养元气也。”可知,地方大员刊刻书籍旨在“激扬正气”“培养元气”。太平天国焚毁的不仅仅是儒家经典著作,严重挑战着儒家文化权威,更质疑着清廷统治的合法性,搅乱了人心,加剧了士林风气的躁动不安。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汲汲于研磨科举畅销书,“由于科举考试用书市场上的畅销书所收都是程文,故对考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往往使得应考士子并不遵循官方所建议的养成学问的步骤,导致甚至连清代官方设立的科举考试的制度性知识诉求亦大打折扣,许多读书人仅仅是凭借对科举考试用畅销书的揣摩、细读而掌握了撰文的诀窍,并以此在科场上获得成功,甚至连儒家经典的原文都可以不必精研”,而对经史、义理一窍不通,读书功利化的问题日渐凸显。在战后收拾人心之时,官员们试图通过刊刻经史类书籍重振士气,整饬士林每况愈下的风气。
同治六年(1867)四月,江苏学政 鲍源深上奏刊刻经史类书,道:“窃维士子读书,以穷经为本,经义以钦定为宗。臣伏读世祖章皇帝御注《孝经》;圣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诗》《春秋》三经传说汇纂;世宗宪皇帝御纂《孝经集注》;高宗纯皇帝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钦定《三礼义疏》皆阐发精微,权衡至当。足使穷经之士不淆于众说,得所指归。……至穷经之外,读史为先。全史卷帙浩烦,现在经费未充,重刊匪易。恭请饬令先将圣祖仁皇帝御批《通鉴纲目》、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敬谨先刊,分发各学士子读之,已可贯串古今,赅通全史。其余各书再行陆续刊刻。……诚令学校经史重完,士子深于经者,窥圣学之原,深于史者,达政事之要,体用兼赅,益卜人才蔚起,于以光列圣右文之治,广皇上教育之仁,岂非黼黻中兴之盛举哉。”他认为经学“窥圣学之原”,史学“达政事之要”,主张大量刊刻经史类书。该奏折得到同治帝的肯定:“……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从中可知,鲍源深强调经史类著作是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对重建清廷的统治权威,重构清廷统治合法性至关重要。
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御史游百川批评士林风气浮躁,士人不安于学的情况,称:“为学者求名之心太急,往往四书五经未能成诵,而即读肤浅考卷,学为应试之文。既务应试,则束书不观。专取文艺数十篇,揣摩求售。叩以经义,茫然莫辨,且有并句读不知者。师如是,以为教弟子如是以为学。求所谓淹通经史者,盖鲜也。求所谓砥砺行修者,益寡也。岂知学无根柢,安有佳文。”该折得到了同治帝的重视,明发上谕:“原期士子通经致用,若学无根柢,徒恃怀挟倩代,以图侥幸,所谓淹通经史者安在?何以振文风而端士习?学政岁科两试,生童正场之前,例有考古一场。着直省学政于按考各属时,遍谕生童,如有能默诵五经,通晓经义者,准其报名,即于考古场中按名面试,拨之以为研经者劝。”清廷显然试图通过政府的力量解决“寒畯之士不读书而临场蹈怀挟之弊;素封之子不读书,而倩代恃抢冒之为。人心日浮,则风俗愈敝。虽有严刑峻罚,不能禁也”的浮躁、功利的士林风气问题。
同治十年(1871)五月二十八日,四川总督吴棠设局,认为刊刻书籍应以经学为本,史学为先,强调刊刻“钦定”《朱子全书》以培养时人的心性,刊刻史类书籍,以增广时人的见识,写道:“士子读书,必以研求性理为本,以博通经史为先,庶可明体达用。……敬谨重刊钦定《朱子全书》,……颁发通省府、厅、州、县书院,以资讲习,顾既有经学以养其心性,尤须有史学以增其识力。恭查殿本前、后《汉书》考校精详,洵为士林圭臬。……亦次第告竣,……现又筹款接刊《史记》、《三国志》两书,合成《四史》,除分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务期流传日广,俾多士咸敦实学。”
光绪十三年(1887)十月二十五日,张之洞上奏设立广雅书局,主张刊刻经史类著作,写道:“窃维经学昌明,至我朝为极盛。……粤海堂为当日创刊《经解》之所是,粤省尤当力任此举,勉绍前矩。臣等海邦承乏,深惟治源。亟宜殚敬教劝学之方,以收经正民兴之效。此外史部、子部、集部诸书可以考鉴古今,俾益经济,维持人心风俗者,一并搜罗刊布。”又据张之洞幕府人员王秉恩致信缪荃孙称:“春中宏开书局,大抵以经学续学海堂,别开史学,与之并峙。”可知,张之洞强调经学对于清朝建设和维系地方文教的重要性,重视刊刻经史类书。
综上可知,地方官员纷纷强调刊刻经史类著作,认为经史类书是清廷“收拾人心”、改变士林浮躁不安风气的必要文化资源,是清廷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更是维护清廷政治合法性、重建政治权威的根本。因而,在战后收拾人心,重建地方文教秩序之时,经史类著作理所当然地成为官书局刊刻的重点。
二、经史类官刻书
1.经类:蒙童、御纂经类读物各省书局重视刊刻童蒙类经书,如《小学》《四书》《五经》《说文解字》《大学衍义》《近思录》《小学集解》《御纂七经》《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等。光绪五年(1879),山西巡抚曾国荃设立濬文书局,刊刻“《四书》《六经》《小学》《近思录》”。光绪六年(1880),左宗棠署理新疆,建议“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地方官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将此类书籍视为清廷塑造意识形态最基础的读物。丁日昌认为诵读《小学》“最能感悟人心,维持风教。”张之洞言:“朱子《近思录》一书,言约而达,理深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咸宜,所宜人置一编。”因而,童蒙类《小学》《四书》《五经》类经书,成为地方大员主张刊刻的重点,是各地学府采用的重要教材。
为构建清廷统治的合法性,清代皇帝亲自撰写或组织人员编写一系列著作,如《御纂七经》《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周官义疏》《钦定仪礼义疏》《钦定礼记义疏》等。通过编纂书籍,清廷掌握了思想阐释的主动权,并从中汲取巩固政权需要的政治资源;通过推广这些著作,清廷官方力量推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强化清廷统治合法性的基本事实。
2.史类:钦定史类、官箴书
地方书局刊刻了“御纂”史类以及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如《御批通鉴辑览》《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钦定明鉴》《御制人臣敬心录》等。史类著作,尤其是“钦定”“御批”的著作,集中体现了清廷的意识形态。因此,书局在刊刻史类著作时多选用清廷认定的版本。以五局合刊《二十四史》各书局版本选择为例,金陵书局根据“汲古本刻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淮南书局“据汲古本刻隋书”,浙江书局“据江都惧盈斋本刻旧唐书、据汲古本刻新唐书、据殿本刻宋史”,江苏书局“据道光补印殿本刻辽、金、元,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第十六卷、厉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杨循吉拾遗补五卷、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湖北书局“据汲古本刻新五代史,据殿本刻旧五代史、明史,皆可单行”。这些著作的原本大多是汲古阁本,多为乾隆年间所刻。刊刻此类著作,梳理历史脉络,以此论证清廷统治的合理性。
各省书局注重刊刻地方志,如《两淮盐法志》《元和郡县志》《湖南通志》《广东通志》《浙江通志》《湖北通志》《山东通志》等。同治九年(1870)三月二十八日,刘坤一上奏刊修江西省通志,“军务之始于地方志完敝,以及忠义节孝之事迹,均须撰述昭示”,建议撰修江西省通志,要求“参酌各省通志,凡例分门别类,尚属详略得宜,并刊发各府州县,饬令查照章程,延请名宿,各将旧志以后事迹,迅速采访,送省备纂”。地方志的编修,反映了地方社会之变迁,“风俗之良窳,政治之得失,人才之消长,以及实业教育水利防务诸大端”。各省官员通过志书、疆域图的编纂和刊刻,不仅增强士人对地方和中央的归属感、认同感,而且鼓励地方士人积极参与官方知识的再生产,以期将更多的士人吸纳到清廷的统治体系中,无形中强化清廷政治权威和政权合法性的事实。
书局还注重刊刻地方政务类的“官箴书”。编纂“官箴书”的意图在于“丰富和提升帝国官员的行政知识与行政能力,从而弥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僚遗留下来的缺陷”。这既包括提高行政事务处理能力,如《荒政辑要》《筑圩图说》《救荒补遣》《捕蝗要诀》等,以《筑圩图说》为例,丁日昌刊刻此书的目的在于使当地民众明白筑圩的重要性,推进地方上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写道:“现在饬书局刻印筑圩图说,俟书成即当发交该令,晓谕农民,俾知筑圩之益,所禁四条,亦能为民除弊,如农夫去草,芟夷蕴崇,仍望督率劝惩,勤求实事。”这类书籍的刊刻,不仅提高官员处理地方具体事务的能力,而且指导民众开展相关技能训练,提高民众参与地方具体事务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官员地方治理工作;又有官员道德、吏治类,如《牧令书》《庸吏庸言》《牧令辑要》《秋审条款》《实政录》等官箴书。这类书籍试图弥补科举考试选拔的缺陷,提高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帮助官员成长为“技术性官僚”,且极力劝诫和引导官员做“好官”“清官”,保证自身清正廉洁,正大光明,积德行善,奉公守法。
可以说,经史类书,从童蒙经类读物《小学》《四书》《五经》到御纂经类书籍,从钦定史类书籍、地方志到官箴书,无一不是官方介入知识生产,试图掌握知识解释权,塑造统治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产物,是清廷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因而,刊刻经史类书,是重构清廷政治合法性和地方官员恢复文教秩序的共同选择。
三 、结语
晚清时期,清廷面临着严重的内外危机,统治合法性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在战争结束之后,地方督抚率先设立书局刊刻书籍,而这一举动与清廷重建统治权威,重构统治合法性的主张高度契合。于是,在朝廷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晚清官书局刊刻了卷帙浩繁的经史类著作,通过官方介入知识的生产,掌握着知识的阐释权,至少在形式上解决了地方文库空虚的问题,重建地方文教秩序,据称:“寇乱洊经付之一炬,中兴将帅每克复一省一部,汲汲然设书局,复书院,建书楼,官价无多,尽人可购,故海内之士多有枕经葄史,博览迅速,堪为世用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廷政权合法性的焦虑。(王晓霞,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晚清官书局再研究”(项目编号:15YJC770036)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⑩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O].北京:京华印书局本,1926.
② 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330.
③ 徐雁.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20.
④⑤??? 陈韬.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G].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373-376,369,373-376,365-366,365-366.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B],档号:03-5003-021。
⑦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M].上海:上海书店,1983:234.
⑧ (清)潘钟瑞.苏台麋鹿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85.
⑨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文化面面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51.
? 曹南屏.坊肆、名家与士子——晚清出版市场上的科举畅销书[J].史林.2013(5).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7册)[B].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43,393.
? 吴棠.奏为川省刊刻书籍颁发各属以广流传由[B].台湾故宫藏录副奏折,档案号:1083 7 7。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7172-036。
? 顾廷龙校.艺风堂友朋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07.
? 萧荣爵编.曾忠襄公(国荃)奏议(卷十三)[G].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1220.
? 杨书霖.左文襄公全集(卷五十六)[G].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2254.
? 赵春晨编.丁日昌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94.
?? (清)张之洞编纂,范希曾补正.增订书目问答补正[M].北京:中华书局,2011:670,68.
? (清)刘坤一撰,陈代湘等校点.刘坤一奏疏[M].长沙:岳麓书社,2013:236-237.
? 王祖畲等纂.太仓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5:6-7.
? 杜金.清代高层官员推动下的“官箴书”传播—以陈宏谋、丁日昌为例[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6).
? 丁禹生撰.抚吴公牍[O].光绪三年版.
? 夏东元编,郑观应.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