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校猎题材由来已久,《诗经》时代,《豳风·七月》记叙西周早期农人的狩猎活动,《小雅·车攻》记叙周宣王会同诸侯校猎一事,但这些作品并不描写屠杀猎物的情形,因此不带有暴力色彩。汉魏时期,校猎题材为赋家所青睐,此时期赋家不仅在大量的校猎赋中,还在都城赋和七体中描写、渲染狩猎过程中屠杀猎物的暴力血腥场面,从而形成独特的阳刚、雄放、野性的美学风格。金春峰在《汉代思想史》中盛赞汉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将汉代人的气质特征概括为广阔的心胸以及雄浑、粗犷的气势和力量,并将文学艺术中“人兽竞力”的场景归为这种特征的反映。从这个角度上讲,校猎书写确实很好地展现了汉魏的时代特征和精神气质。
一 《七发》对校猎题材赋作的开创意义
赋体文学作品中的校猎题材始于枚乘《七发》,作为汉大赋的奠基之作,《七发》在题材内容上为后世赋提供了思路和灵感,在艺术手法上对后世赋影响深远。《七发》共描写了音乐、美食、车马、游览、校猎、观涛六种题材,枚乘对观涛的描写,可谓文学史上的绝唱,其气势之盛、修辞之妙、遣词之壮美、摹写之形象,后世绝难超越。其他五种题材经后世赋家不断扩展、敷演、创新,佳作迭出。《七发》对校猎场景的描写,即启发后世赋家创作出了专门的校猎赋,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羽猎赋》,张衡《羽猎赋》以及建安诸子的《武猎赋》《西狩赋》《羽猎赋》《大阅赋》等。后世京都赋亦将校猎题材作为铺叙的内容之一,在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中都有对校猎活动的精彩展现。后世七体亦偏好校猎题材,傅毅《七激》、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均继承了这一题材。张衡《七辩》增加了女色、游仙两种题材,舍弃了校猎,但他在《二京赋》中有大篇文字展现校猎场景,还创作了专门的《羽猎赋》,可见校猎题材深受赋家喜爱。观察这一题材的书写方式从西汉初年的枚乘到建安时期的曹植、王粲之间的发展变化,可看出校猎题材美学特征的形成过程以及赋家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不断探索和超越,亦可看出时代背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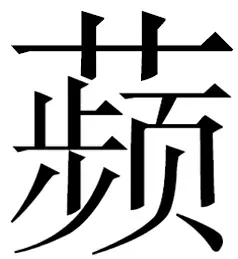
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逐马鸣镳,鱼跨麋角。履游麇兔,蹈践麖鹿,汗流沫坠,冤伏陵窘。无创而死者,固足充后乘矣。此校猎之至壮也……
狩猎场面是校猎题材的主体内容,枚乘首先概括地叙写了猎犬和骏马的精良,向导和车夫的超群,然后简单渲染了车马践踏猎物的情景,并简单铺陈了麇、兔、麖、鹿等猎物的名称,描写了猎物四下逃匿、紧张窘迫的情状以及满载而归的情形。最后,枚乘还描写了勇士近距离捕获野牛和老虎的情景:
于是榛林深泽,烟云暗莫,兕虎并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硙硙,矛戟交错。
枚乘在较短的篇幅内,描写了与校猎相关的非常丰富的内容,但每个层次都只是概括描述,没有多少细节上的渲染与夸张,留给后世赋家极大的发挥空间。
枚乘对校猎活动的描写,主要分为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校猎排场,一般包括对装备、阵容、苑囿的夸张;第二,狩猎的场面,这部分是赋家着力渲染的对象,通常包括对众人围攻猎物、车马践踏猎物、鹰犬追逐猎物以及勇士与猎物搏斗场景的夸张渲染,以及对名物(主要是猎物)的铺排。后世赋家多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继承、扩展和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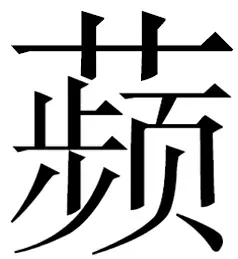
二 司马相如和扬雄对校猎题材的创新发展
司马相如将校猎过程中攻击、屠杀猎物的场景作为重点描写对象,其《子虚赋》描写楚王校猎场景,对枚乘有明显模仿,“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的语句直接从《七发》中套用。但在描写狩猎场面时,《子虚赋》较之《七发》的描写更具张力:“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轊陶马余,乘遗风,射游骐。倏胂倩浰,雷动焱至,星流电击。”车马践踏猎物的力度以及飞驰的速度,带给人心理的冲击。而对于弓箭杀伤猎物的暴力以及猎物中箭后的惨状的描写,则形成视觉的冲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掩草蔽地。”《上林赋》描写天子游猎,在此基础上,追求更为淋漓尽致的表达和浓墨重彩的渲染以及殚精竭虑的铺排。天子校猎的排场,不仅阵容豪奢,而且气势磅礴,惊天动地:
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江河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
天子手下的勇士,与猛兽格斗的场景,分外刺激:

不难看出,司马相如有意在枚乘赋的基础上踵事增华,显露出明显的逞才意图,在描写勇士与野兽的格斗时,运用恣肆的铺排,堆砌奇字难字,铺陈名物,排比动词,用一连串的三字句营造出急促的节奏、紧张的氛围以及充满暴力感的酣畅气势。
司马相如还通过想象天子驾车上天捕获神鸟来凸显天子校猎的不同凡响:
然后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猋,乘虚亡,与神俱。蔺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鵔鸃。拂翳鸟,捎凤凰,捷鹓雏,掩焦明。
这也是对枚乘《七发》的一个创新。
《上林赋》对猎物尸横遍野的惨状进行了渲染:“徒车之所閵轹,步骑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与其穷极倦谷卂,惊惮詟伏,不被创刃而死者,它它藉藉,填坑满谷,掩平弥泽。”各种被车轮践踏而死、被骑兵踩踏而死,以及筋疲力尽、惊恐万状、受惊吓而死的各种猎物,满地堆积,布满山谷、平原与河泽,这种描写对暴力的渲染达到了极致,形成与《七发》的温情柔和截然不同的美学特征,给人极度的紧张感以及酣畅的释放感,唤起人内心的生命冲动,令人血脉偾张。
枚乘《七发》对观涛的描写壮观酣畅,宏阔有力,若与司马相如《上林赋》对狩猎场景的描写相比较,后者营造出的暴力场景对读者有更多的代入感,更加具有张力、感染力和煽动性。
扬雄作赋多模拟司马相如,《汉书》本传记载他“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其《羽猎赋》即模仿《上林赋》之作。
扬雄在模仿的同时,运用丰富的神话想象和极度的夸饰努力实现对司马相如的超越。扬雄《羽猎赋》开篇渲染天子校猎的排场:
撞鸿钟,建九旒,六白虎,载灵舆,蚩尤并毂,蒙公先驱。立历天之旂,曳捎星之旃,辟历列缺,吐火施鞭。萃傱允溶,淋离廓落,戏八镇而开关;飞廉、云师,吸嚊潚率,鳞罗布列,攒以龙翰。秋秋跄跄,入西园,切神光;望平乐,径竹林,蹂蕙圃,践兰唐。举烽烈火,辔者施披,方驰千驷,校骑万师,虓虎之陈,从横胶輵,猋泣雷厉,驞駍駖磕,汹汹旭旭,天动地岋。羡漫半散,萧条数千万里外。
扬雄借助蚩尤、蒙公、飞廉、云师等神话人物,营造比《上林赋》更为奇异的风格,同时运用更多的意象、名物以及夸张手法,营造比《上林赋》更为宏大的气势和更为铺张的场景。扬雄对苑囿的广阔、军队的阵容进行了极度夸张的描述,营造出阔大的空间感以及异常宏大的声响。在描写狩猎场面时,扬雄亦采取一连串的三字句表现勇士与猛兽的搏斗,但是在动词的使用和名物的铺陈上避免与《上林赋》重复:
若夫壮士慷慨,殊乡别趣,东西南北,骋耆奔欲。拕苍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蝯,腾空虚,歫连卷,踔夭蟜,娭涧门,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猋,林丛为之生尘。及至获夷之徒,蹶松柏,掌蒺梨,猎蒙茏,辚轻飞;履般首,带修蛇,钩赤豹,摼象犀;跇峦阬,超唐陂。
扬雄采用比《上林赋》更为生动具体的的细节描写展现猎物的惨状:
观夫票禽之绁隃,犀兕之抵触,熊罴之挐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抢题注,蹙竦詟怖,魂亡魄失,触辐关脰。妄发期中,进退履获。创淫轮夷,丘累陵聚。
扬雄增加捕获水怪的情节来实现创新:
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凌坚冰,犯严渊,探岩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獭,据鼋鼍,抾灵蠵。入洞穴,出苍梧,乘钜鳞,骑京鱼,浮彭蠡,目有虞。
扬雄还植入荒诞的想象来实现创新:
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宓妃,饷屈原与彭胥。
这一想象过于荒诞,曾受到刘勰的批评: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于朔野。娈彼洛神,既非罔两;唯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饰其事,义暌剌也。(《文心雕龙·夸饰》)
刘勰认为扬雄笔下鞭打宓妃以饷屈原的想象是过于夸张的手法,造成表达上的粗疏以及对义理的违背。事实上扬雄写出这样荒诞的文字,只是为了对模仿对象有所超越,其鞭打宓妃的暴力想象,充满视觉和心理的刺激。刘勰亦肯定夸饰手法能达到“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的艺术效果。
司马相如和扬雄对于校猎的描写,可谓挖空心思、殚精竭虑,后人能有所突破的空间并不大。不过,这并不妨碍后世赋家对这一题材的青睐以及创新的努力。
三 东汉赋校猎题材对礼制的引入
东汉最早的校猎题材赋作是傅毅的《七激》。一般来说,七体中的七件事情,在描写的时候用力相对比较均匀,每部分的篇幅长短不会有太大悬殊,所以七体关于校猎的描写,只是文章的一部分,不可能像《上林赋》与《羽猎赋》那样尽情渲染,恣意铺排。《七激》关于校猎的描写,即趋于凝练,其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七激》开始强调校猎的性质和目的:三时既逝,季冬暮岁,玄冥终统,庶卉零悴。王在灵囿,讲戎简旅。
其次,《七激》对狩猎场面的描写细节开始由暴力进而为血腥:
击不待刃,骨解肉离,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
强调“讲戎简旅”,当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礼制逐渐恢复并发挥约束作用的结果。胡大雷《田猎文化与汉代田猎赋主旨的变换》论汉代京都赋,认为“以讲求礼仪肯定田猎”是东汉赋田猎题材的主旨。可以说,礼制和校猎的结合,使校猎题材赋作逐渐形成了典雅这种新的美学特征。这一点在班固、张衡的赋中得到了体现。
班固《两都赋》在校猎题材上又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与班固的政治观点和创作宗旨密切相关。《两都赋》乃班固针对迁都之事而作,他以批评的角度描写西京之奢华,又以赞誉的角度描写东京之合乎法度,以达到为迁都东京而立论辩解的目的。所以,在《西都赋》和《东都赋》中,作者对校猎场景的描写呈现出较大差异。班固的这种写法比较有意思,一方面他在《西都赋》中试图继承前人的精髓,以达到炫耀逞才的目的,同时又试图在《东都赋》中去实现自己维护礼制的革新。
班固《咏史诗》被评为质木无文,事实上他的赋作所展现出来的文采,较之司马相如和扬雄诸人,也是显得比较平实平淡的,《西都赋》所写:
水衡虞人,修其营表。种别群分,部曲有署。罘网连纮,笼山络野。列卒周匝,星罗云布。于是乘銮舆,备法驾,帅群臣,披飞廉,入苑门。遂绕酆鄗,历上兰。
以上是对校猎排场的描写,同样是天子校猎,班固笔下的想象色彩和夸饰色彩减少了,乘銮舆、备法驾、帅群臣这样的排场,多了基于礼制的典雅,而少了司马相如和扬雄笔下的华丽奇幻。
再看班固对狩猎时众人围猎的描写:
六师发逐,百兽骇殚。震震爚爚,雷奔电激。草木涂地,山渊反覆。蹂躏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尔乃期门佽飞,列刃钻钅侯,要趹追踪。鸟惊触丝,兽骇值锋。机不虚掎,弦不再控。矢不单杀,中必叠双。飑飑纷纷,矰缴相缠。风毛雨血,洒野蔽天。
这里班固继承了前代赋家着意表现的力度、速度、气势,以及暴力、血腥的场景描写,但他明显减少了对猎物惨状的细节描写以及对屠杀场面的渲染。在描写勇士与猛兽近身格斗场景时,那种酣畅肆意的铺排成分有所减少,代之以较为规整的形式:
平原赤,勇士厉。猿狖失木,豺狼慑窜。尔乃移师趋险,并蹈潜秽,穷虎奔突,狂兕触蹶。许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脱角挫脰,徒搏独杀。挟师豹,拖熊螭。曳犀犛,顿象罴。超洞壑,越峻崖。蹶崭岩,钜石阝贵。松柏仆,丛林摧。草木无余,禽兽殄夷。
这种较为规整的形式,一方面可能出自班固有意的克制,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受制于自身的想象力和文学表现力。如司马相如与扬雄在描写人兽格斗时采用一连串的三字句,排比名物,排比动词,达到渲染夸张之用,但班固仅写“挟师豹,拖熊螭。顿犀犛,曳豪罴”。诚然,在前人殚精竭虑的写作传统下,已很难在铺排方面有所突破。班固还对校猎时赶尽杀绝的场面做出了总结性描写:“草木无余,禽兽殄夷。”这个描写是基于批判立场的,因为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以极众人之所眩矅,折以今之法度。”其《西都赋》正是着眼于“眩矅”进行描写,《东都赋》则对其“折以今之法度”。司马相如与扬雄作赋,虽有讽谏之用,但真实目的仍在于炫耀逞才,以文求荣,所以实际效用乃不讽反劝。在他们笔下,飞禽走兽被驱赶围猎,尸横遍野,无有遗漏,才能彰显天子的武力和神威。司马相如身处西汉早期,不受儒家礼制约束。扬雄虽然处于儒家思想占据统领地位之时,但他早年作赋应当是秉持着炫耀逞才的初衷以及模拟相如的热情的,所以到晚年悔其少作,乃至于称辞赋为雕虫小技,并且在自叙中给自己早年的大赋一一加上表达讽谏之意的文字。而班固则基于礼制的立场对赶尽杀绝的围猎持否定态度,这在《东都赋》中有直接表现:
若乃顺时节而搜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驺虞》,览《驷驖》,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正仪,乘舆乃出。
以上文字几乎可以视为儒家礼制之下帝王出猎顺时、守礼的典范。
于是发鲸鱼,铿华钟。登玉辂,乘时龙。凤盖棽丽,和銮玲珑。天官景从,祲威盛容。山灵护野,属御方神。雨师泛洒,风伯清尘。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元戎竟野,戈铤彗云。羽旄扫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焰生风,吹野燎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摇震。遂集乎中囿,陈师案屯。骈部曲,列校队,勒三军,誓将帅。然后举烽伐鼓,以命三驱。轻车霆发,骁骑电骛。游基发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辔不诡遇,飞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顾倏忽,获车已实。乐不极般,杀不尽物。马踠余足,士怒未泄。先驱复路,属车案节。
在对狩猎场面的描写中,班固虽然极力营造帝王狩猎的阵仗和气势,渲染狩猎的阵容,但他明显剔除了对猎杀禽兽的细节描写,避免了对血腥场面的再现,并强调狩猎应当遵循“乐不极盘,杀不尽物”的原则,这正是对《西都赋》中“草木无余,禽兽殄夷”的行为的拨乱反正。班固《两都赋》还大大减少了奇字难字的使用,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班固确实在践行以赋“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功能,而不是重点着意于文学的呈现。
张衡《二京赋》在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他以《西京赋》展示铺排和渲染,以《东京赋》表达礼制和约束。其《西京赋》继承扬、马风格,恣意渲染夸张,力求超越前人,比如描写天子出猎的排场:
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駮。戴翠帽,倚金较。璿弁玉缨,遗光倏爚。建玄弋,树招摇。栖鸣鸢,曳云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华盖承辰,天毕前驱。千乘雷动,万骑龙趋。属车之簉,载猃猲獢。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寔俟寔储。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魑魅魍魉,莫能逢旃。陈虎旅于飞廉,正垒壁乎上兰。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张衡铺排的许多名物,诸如“雕轸、骏駮、翠帽、金较、璿弁、玉缨、玄弋、招摇、鸣鸢、云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等,基本是前人未使用过的。且从数量上,也超过了扬、马、班固。张衡不仅效仿扬、马极力渲染狩猎的阵容,刻画猎物被杀死的细节,突出排场、气势和暴力,还特别在名物铺排上,表现出刻意的超越和创新。除了刚才所举之例,再看张衡对勇士近身捕获猛兽场景的描写:

张衡排比了“鼻、圈、揸、扌此、突、赴、探、猎、陵、杪、擭、超、摕”一连串动词,以及“巨狿、赤象、狒猬、窳狻、枳落、棘藩、洞穴、封狐、重山献、昆马余、木末、獑猢、殊榛、飞鼯”等一系列兽类名称和它们藏身之所的名称,这明显是夸耀博学的逞才之笔。
张衡《西京赋》与班固《西都赋》一样,主要是对西京之豪奢进行批评和否定,以此揄扬东京的法度,因此,张衡《东京赋》对狩猎的描写,亦如班固《东都赋》那样,显得雅正克制:
文德既昭,武节是宣。三农之隙,曜威中原。岁惟仲冬,大阅西园。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鸠诸灵囿。兽之所同,是谓告备。乃御小戎,抚轻轩,中畋四牡,既佶且闲。戈矛若林,牙旗缤纷。迄上林,结徒营。次和树表,司铎授钲。坐作进退,节以军声。三令五申,示戮斩牲。陈师鞠旅,教达禁成。火列具举,武士星敷。鹅鹳鱼丽,箕张翼舒。轨尘掩迒,匪疾匪徐。驭不诡遇,射不翦毛。升献六禽,时膳四膏。马足未极,舆徒不劳。成礼三驱,解罘放麟。不穷乐以训俭,不殚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怀民。仪姬伯之渭阳,失熊罴而获人。泽浸昆虫,威振八寓。好乐无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璅璅焉,岐阳之搜,又何足数?
此段描写不用奇字难字,不对暴力进行渲染夸张,不描写屠杀猎物的细节,强调军队狩猎的军容军威,以及对礼制法纪的遵守,强调“驭不诡遇,射不翦毛”,反对虐杀;强调“马足未极,舆徒不劳”,反对过度疲劳;强调“成礼三驱,解罘放麟”,反对大规模屠杀,主张“不穷乐以训俭,不殚物以昭仁”的无逸和仁义思想。
曹胜高在《汉赋与汉代校猎制度》中写道:“如果说西汉校猎代表了武力的张扬和血腥的杀戮,意在显示征服和获得的快感,那么东汉的校猎更多代表着礼乐秩序的恢复和礼仪制度的完善。”
东汉赋家对礼制的引入与宣扬,对暴力书写的节制,为校猎题材增添了典重雅正的审美风格。
四 建安赋家对校猎题材的自由书写与渲染
建安时期,赋家以小赋创作为主,但校猎题材仍保留在七体以及专门的羽猎赋中。现存有关校猎题材书写的建安赋作有应玚《校猎赋》(残缺严重)、《西狩赋》,王粲《羽猎赋》,曹植《射雉赋》(残缺严重),以及王粲《七释》、曹植《七启》中的校猎书写部分。七体中的校猎与专门的羽猎赋不同,七体描写的校猎,只是针对劝说对象,凭借想象写出来的狩猎情景,其狩猎主体并不一定是帝王诸侯,其目的在于启发对方。这样的描写与礼制本身没有多少关联,因此在写作的时候无须强调搜狩礼对人的约束,无须强调对仁义的彰显,无须定义狩猎活动的性质。而专门的羽猎赋以及都城赋中的校猎,狩猎主体都是帝王诸侯,如《子虚赋》写诸侯校猎,《上林赋》写天子校猎,扬雄《羽猎赋》,班固、张衡的都城赋以及张衡《羽猎赋》亦都写天子校猎。扬、马在赋中着重铺陈夸饰,不受礼制约束,班固与张衡则通过不同风格的描写,既实现了逞才夸耀的写作目的,也实现了守礼崇礼的政治意图。
以上特点在建安赋中都得到了继承,并呈现出相对更大的创作自由度。建安赋校猎题材书写主要有两类,七体以及描写曹操校猎之作。建安时期,曹操地位尊贵,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实际政治影响等同于帝王。
王粲《羽猎赋》不仅写曹操校猎合乎礼制的一面,同时又突破礼制的约束,对狩猎场景的血腥暴力进行自由书写和表现。王粲描写曹操校猎合乎礼制,遵从古道:“遵古道以游豫兮,昭劝助乎农圃。用时隙之余日兮,陈苗狩而讲旅。”王粲亦注重渲染其出猎排场:“济漳浦而横阵,倚紫陌而并征。树重围于西址,列骏骑乎东埛。相公乃乘轻轩,驾四辂,驸流星,属繁弱,选徒命士,咸与竭作。旌旗云扰桡,锋刃林错。扬晖吐火,曜野蔽泽。山川于是摇荡,草木为之摧拨。”王粲又极力渲染猎物惨死、血肉模糊、身体破碎、尸横遍野且遭鹰犬咬噬的血腥情状:“禽兽振骇,魂亡气夺,兴头触系,摇足遇橽,陷心裂胃,溃脑破颊。鹰犬竞逐,奕奕霏霏。下鞲穷绁,抟肉噬肌。坠者若雨,僵者若坻。”王粲还描写校猎结束后“清野涤原,莫不歼夷”的情景,将猎物赶尽杀绝,显然不符合礼制要求。
应玚《西狩赋》与王粲《羽猎赋》乃同题共赋之作,赋中首先颂扬曹操的文治武功:“荡无妄之氛秽,扬威灵乎八区。开九土之旧迹,暨声教于海隅。”然后渲染霜寒风劲、草木摇荡、鸷鸟高飞的情景。这些内容的主要作用是铺垫、造势,为曹操的出场营造氛围。赋中没有与礼制相关的内容,作者直接以“拣吉日,练嘉辰。清风矢戒,屏翳收尘”来领起对曹操出场情形的描绘。应玚虽然也极力渲染校猎的气势,但是与王粲相比,其描写不如王粲赋那样惊心动魄、触目惊心,因为应玚赋避免了对暴力、血腥场景的细节展现,仅利用对排场、力量、速度的一般描写来展现狩猎场面:“尔乃徒舆并兴,方轨连质。惊飚四骇,冲禽惊溢。骋兽塞野,飞鸟蔽日。尔乃赴玄谷,陵崇峦,俯掣奔猴,仰捷飞猿。”应玚与王粲同题共赋所表现出的个人选择与创作个性的差异,可见建安士人在创作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多元选择。
建安七体的校猎题材表现出对暴力血腥的进一步张扬,尤为突出的是对杀戮快感的呈现。先看王粲《七释》对“游猎之娱”的铺陈夸饰:
奋干殳而捎击,放鹰犬以搏噬。羽毛群骇,丧魂失势。飞遇矰矢,走逢遮例。中创被痛,金夷木毙。俯仰翕响,所获无艺。于是刚禽狡兽,惊厈跋扈。突围负阻,莫能婴御。乃使晋冯、鲁卞,注其赑怒,徒搏熊豹,袒暴兕武。顿犀掎象,破脰裂股,当足遇手,摧为四五。若夫轻材高足,光飞电去。踵奔逸之散迹,荷良弓而长驱。凌原隰以升降,捷蹊径而邀遇。弦不虚控,矢不徒注。僵禽连积,陨鸟若雨。纷纷藉藉,蔽野被原。含血之虫,莫不毕殚。
赋中写鹰犬逐猎,禽兽四散奔逃,或中箭,或入罗网,负伤的野兽狂性大发,勇士们徒手与之格斗。赋中对近身肉搏场景的细节描写和渲染,尤为暴力血腥:“顿犀掎象,破脰裂股,当足遇手,摧为四五。”这种手撕猎物的场景,呈现出杀戮过程中的利落和暴虐。
曹植《七启》亦有对校猎过程中惨烈血腥场面的极致渲染,进一步突显了校猎题材的阳刚、雄放、野性美学特征。
曹植开篇即言“驰骋足用荡思,游猎可以娱情”,表明此处的游猎,非帝王诸侯基于礼制的狩猎活动,而是纯粹的游乐活动。接下来描写校猎排场:“仆将为吾子驾云龙之飞驷,饰玉路之繁缨。垂宛虹之长緌,抗招摇之华旍。捷忘归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蹑景而轻骛,逸奔骥而超遗风。”脱离了帝王出猎的奢华阵容,此类等同于普通贵族游猎的排场多了几分轻灵,少了一些典重。曹植继承前人对狩猎场面的描写,比如写众人围猎,马踏车践;写士卒追逐猎物搜林索险、腾山赴壑;写困兽犹斗,“哮阚之兽,张牙奋鬣;志在触突,猛气不慑”。然后写勇士与猛兽的近身格斗:
乃使北宫东郭之畴,生抽豹尾,分裂豸区肩,形不抗手,骨不隐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无毛类,林无羽群。积兽如陵,飞翮成云。
这段描写看似不起眼,但在校猎题材中却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曹植描写勇士与猛兽角力,受伤之后仍凶猛无比的豹、貙、熊、虎,被勇士活活抽断尾巴,撕裂肩膀,勇士劈碎熊掌,摧毁虎躯,场面十分暴力血腥。前代赋家亦在校猎题材中展现暴力,展现血腥的一面,但是在描写人与兽近身肉搏之时,却少有曹植这样细致的描写、直接的展现和极致的渲染。这段描写犹如特写镜头,将勇士撕碎猎物的情景推近到读者眼前,人类的双手沾染了猎物的鲜血,这种场景远比飞矢、陷阱、罗网、鹰犬造成的猎杀场景更加暴力和血腥。勇士的锐不可当、奋力呐喊,以及猎物的鲜血四溅、哀号惨叫,令人既有酣畅淋漓之感,又有惊心动魄之叹,不仅呈现出杀戮的无情和熟练,更呈现出一种杀戮的快感和享受。
汉赋中的校猎场景,场面也往往血腥暴力,但曹植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描写了人与兽角斗的场景,重点渲染勇士徒手撕碎猎物的场景。不是每篇包含校猎题材的赋都会写人兽格斗,即使写,也只是轻描淡写,试简单比较如下:
于是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
(司马相如《子虚赋》)
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
(司马相如《上林赋》)
掎僄狡,扼猛噬。脱角挫脰,徒搏独杀。挟师豹,拖熊螭。曳犀犛,顿象罴。
(班固《西都赋》)
乃使晋冯、鲁卞,注其赑怒,徒抟熊豹,袒暴兕武;顿犀掎象,破脰裂股,当足遇手,摧为四五。
(王粲《七释》)
司马相如对人兽格斗的描写十分简单,并无多少渲染,班固的“脱角挫脰”已稍显凶狠,但不如曹植注重细节描写和渲染。王粲与曹植同题共作,在渲染暴力血腥上,所用之力稍逊曹植,但较之前人,已十分突出。建安文人多从军征伐,曹植十四岁就随父征伐袁谭,这种经历,或许让他们亲眼看见杀戮与鲜血,从而赋予他们对暴力的崇尚,并因此在校猎题材中张扬出来。
汉魏赋体文学中的校猎题材,具有鲜明独特的审美风格。赋家对校猎苑囿的空间描绘,呈现出宏伟、阔大的空间感和磅礴的气势。赋家对车马、士卒的力量和速度的描写,呈现出阳刚之美和雄放之风。赋家对狩猎过程中的屠杀、搏斗等血腥场景的描绘,呈现出独有的暴力、野性的美学风格以及尚武精神。赋家基于礼制背景对校猎活动的描写,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典雅风格。为了追求对前人的超越,校猎题材偶尔还呈现出荒诞的想象。且赋家对名物的恣意铺排和对修辞手法的尽情呈现,表现出赋家博学的特点和逞才的写作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建安时期的诗歌虽然亦表现校猎题材,却避免对暴力血腥场景的渲染,如刘桢《射鸢诗》描写曹操射猎的英姿以及精准的箭法:“发机如惊猋,三发两鸢连。流血洒墙屋,飞毛从风旋。”曹植描写京洛少年高超的骑射技巧:“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相比校猎赋,二者在气势和张力方面都显得较为平淡平和,这种创作特点表现出诗赋文体功能的差异,赋体文学具有娱乐功能,可以纵心所欲地表现情欲,也可以自由书写血腥暴力,而诗歌则属于相对严肃的体裁,所以对校猎的表现更符合礼制的要求,相形之下显得比较中庸平和。
综上,汉魏校猎题材的阳刚、雄放、野性的美学特征,是赋家在不断超越前人的过程中形成并达到巅峰的,实际上,其间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汉代政治思想变化在文学领域的作用。汉初以黄老思想治国理政,尽管汉初黄老思想的政治实质是法家思想,但在刑德结合、两手并用的指导思想影响之下,形成相对清静无为、宽容的社会面貌,枚乘《七发》校猎书写略带温情、舒缓色彩的特征,正是这种社会特征的反映。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但是儒家思想尚未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且汉武帝锐意开疆拓土、兴师动众、征伐四方、乐此不疲,必然导向崇尚征服和暴力的时代风气。而且“汉代哲学的主题和基调,同样是人的强大有力和对天(神)的征服。”司马相如校猎书写暴力血腥的特点,正反映出这样的哲学主题和时代精神。此后班固、张衡既承续司马相如校猎书写开创的阳刚、雄放、野性的美学风格,又在儒家文艺观影响之下引入合乎礼制的典雅庄重风格。生活在经学风气瓦解时代的建安赋家则全面继承前代校猎题材的书写模式与审美特征,并借由对暴力的崇尚进一步渲染与呈现杀戮快感,将这一题材的美学特征推向极致。汉魏赋校猎题材的阳刚、雄放、野性的美学风格,对后世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比如盛唐边塞诗较明显继承了这种风格,高适、岑参甚至以诗歌形式表现暴力杀戮,受到学者的批评。
汉魏校猎题材中的暴力书写以极度夸张、渲染为手段,以追求强烈酣畅、惊心动魄的文学感染力为目的,具有恣意宣泄内在生命冲动的表达效果,具有极大的文学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