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大都怕冬天。父親就像是村头的老树,每一个冬天的到来,都要折损其一些精气神。每熬过一个冬,之于父亲,就是过了一劫。
老家村子里,刘姓人家并不太多,铁山、沙海沟、大堰根的刘姓人家,都还属于自己家,红事白事都在一起办。
近日,大堰根狗训家儿子结婚,老父亲想去凑凑热闹,但天气已经冷了,我考虑再三,还是开车送父亲去赴宴。
我所理解的孝顺,就是尽量顺着老人的心愿行事吧。当下物质已足够丰富,老人精神上的满足就显得突出。老年人行动不方便,但与人交流的愿望不减。父亲渴望与亲戚邻里聊聊天,说说家常事,拉扯些闲话。即便天冷了,对老人的身体有诸多担心,但多操点心就是了,这种对老人心愿的满足应该是一种最现实的孝顺吧。
路上,问父亲居室内的温度如何?父亲说还可以。但在冬天,父亲说他的双手总是冰凉冰凉的。他冬天轻易不与人握手,免得冰着别人。父亲说到冬天手凉,就又说叨起小时候他右手腕受伤的事:是1953年,那年父亲15岁。三月初六晚上,晚饭时,月亮初上,他从院里回厨房舀饭,绊住了门槛,打烂了碗,月牙儿般的碎片,正好把他右手腕部的大血管割破了,血流如注。
当时交通条件不好,其实经济条件也不允许,很难送去县城首屈一指的石灰窑医院医治。爷爷当时也不在家,而是在隔邻的邵原镇东阳村药铺坐诊,远水不解近渴。家里人只能用笨方法,把面团拍成饼,贴在手腕上止血。好在,算父亲命大,几经周折,还是止住了血,侥幸活了下来。
但这次大出血,伤了父亲的元气,并就此留下了后遗症,右手无力,抓举能力受限,父亲多次说过,如果不是右手腕受过伤,他的书法可不是目前的层次。另外,就是冬天手凉,越到老年,越是明显。
还有跟随父亲一辈子的气管炎,见冷就咳嗽。
竟然还能活到现在,父亲口中满是庆幸与满足。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
每年的寒冬都是父亲生活的拦路虎。但看父亲当下的心态,我暗暗为父亲即将面临的这个冬天加持、助威。
父亲耳背,不好与人沟通,会因之陷入孤寂之中,形成信息孤岛。也因之吧,父亲似乎就更爱凑热闹,老家邻里族人有办事的,他都想回去见见人,说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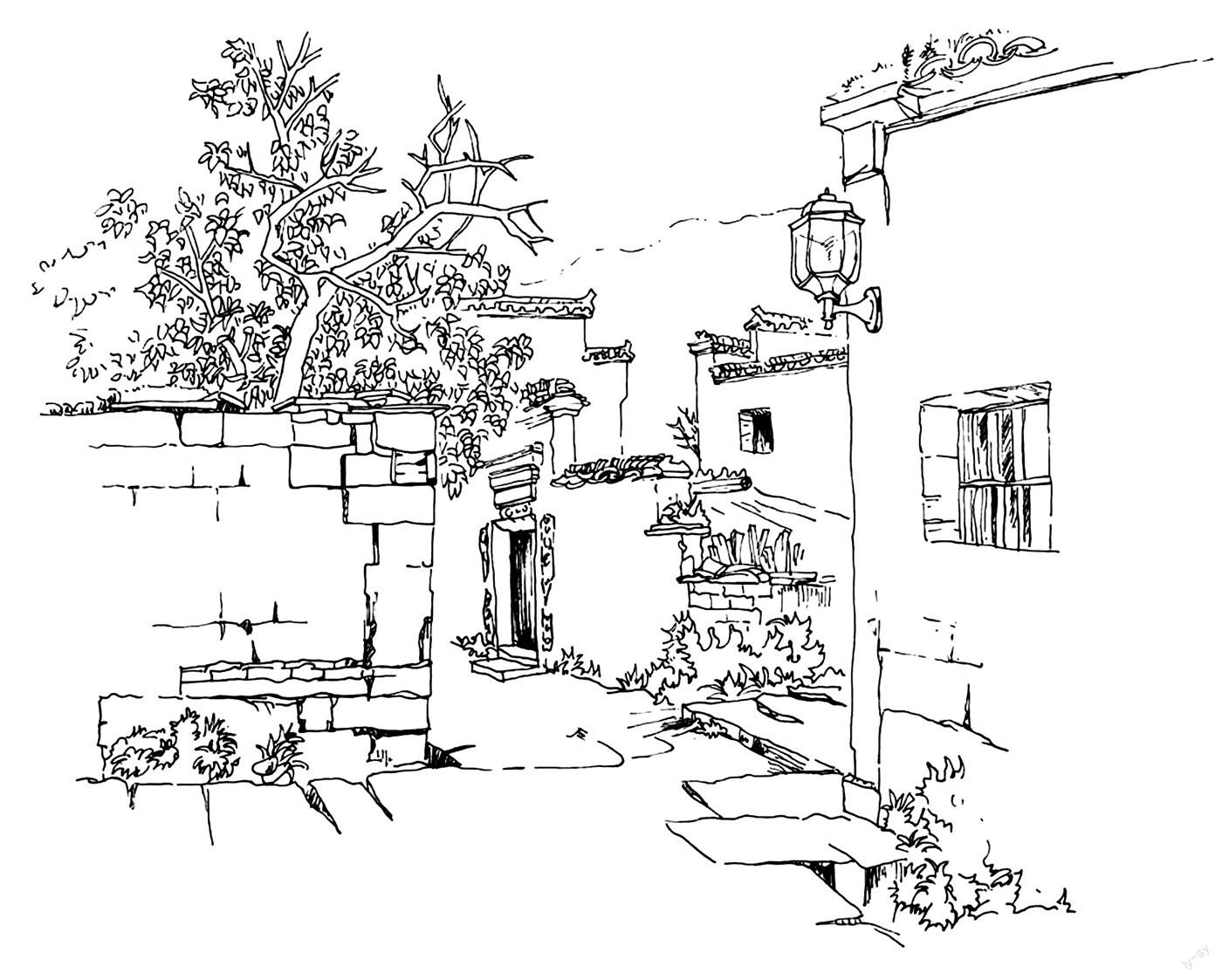
前段时间,我去爬老家后山的五斗峰,说到山脚下的后堂、前堂村,父亲都知道,说他都去过。他还提到家里那个刷床的毛刷,很耐用,就是他与王世龙在后堂买的。
我说到老王——前堂西庄70岁的王银生,父亲仍记得他,并能说清楚一些有关他家孩子的事。显然,在父亲的记忆里,仍能轻松地搜寻到他几十年前烙下的人事印迹。父亲说他的记忆大不如前了,很多刚做的事情转转身就忘了,但多年前的一些旧事,也许他并不刻意记着的,却顽强地固守着大脑内存一域,一旦有人提及,就可以被很快地唤醒。
我并不经常在冬阳下,陪着父亲聊天。
今天交流默契,就利用这个机会,与冬天里萧瑟的父亲多说说话,期望当下的交流能消弱父亲冬天的些许寒凉。父亲又说到他过去教学时的同事李承昇,前几天,他给了父亲一段他亲手挖的老葛根,并说葛根、葛花都是凉血的,可以解酒。又说小单方治大病:前些年吧,李承昇用几棵豌豆苗治好了张树金的一个顽疾,张树金便送李承昇一套《本草纲目》感谢他……就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在父亲口中说出来却很温暖,父亲似乎很喜欢这样唠叨。
冬天,父亲住的房子里,生了一个大煤炉,完全能把整个屋子烘暖。我每次去看父亲,都劝他把炉子烧旺,让室内更暖和一些。但父亲总说太暖和了不舒服。
我的房子里暖气很热,也想让父亲住过来,享受这种暖和。这种室温,父亲的手腕应该会温热很多吧。但父亲总是说住在老宅里自在。
很多年了,父亲的冬天,就在子女的这种焦虑与担心中,结束了这一冬,迎来了下一春。
但日子总会出现波折与变故。
疫情三年,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这个冬天,我们强行让他住到了有暖气的房子里,期望暖气能补充父亲身体阳气的不足,期望父亲能撑到来年的立春节气,身体的小宇宙能对接上大自然的冰消雪融、春暖花开。
也算是撑过了冬,立春节气刚过,父亲还是去了。
父亲实在是给了子女极大的面子,苦苦撑过了又一个冬。父亲属虎,他告别这个世界,在虎年立春之后。
从此,父亲的冬天成为过往。
——选自西部散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