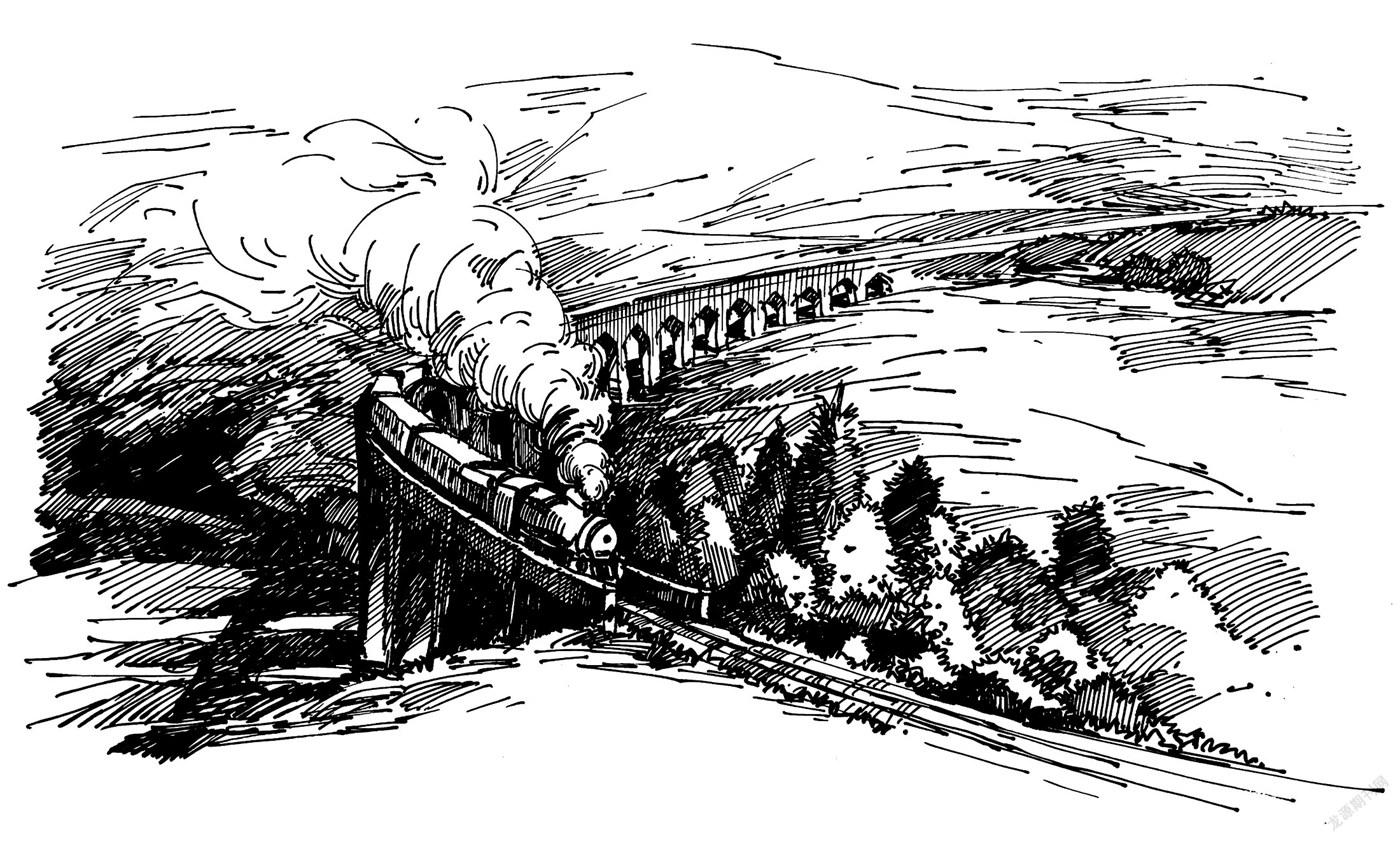
旧厂区征迁,房倒墙毁,一片狼藉。厂里资金匮乏,捉肘见襟,勉力维持,偌大一个单位,住着两三千口人,为安全计,不得不砌围墙。穿衣吃饭量家当,于是便只好废旧利用,将拆下的旧铁栏校正继续安装,行道只补烂处,60年代建厂时的老石墙继續保留,其上砌几层蓝砖,再砌砖垛,形似古城墙,倒还别致。其间有二事,值得一记。
砌了墙,与后山隔离,老职工们颇有微词。缘于山崖有一山泉水,职工们熬粥沏茶已数十载,砌墙后多有不便。物业请相关单位检测,大杆菌超标,我请在食药部门工作多年的友人阅视,言水质颇好,大可放心饮用。为保证水源安全,我们将泉水井淘净,安门上锁,埋设水管下山,砌一石窑供水,在窑洞面前镌刻朱红联: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全靠共产党。鉴于有人担心饮用此水跑肚拉稀,我便拟了几行四言,刻于石碑,镶于石窑右墙,碑名《引泉记》:
厂区倚山,山甚巍峨,树茂草盛,予吾福荫。
山崖有泉,四季不涸,沏茶入味,熬粥爽口。
职工提壶,四邻担桶,排队接水,寒暑不辍。
时在壬寅,小区改建,从众所望,引水进院。
淙淙入耳,涓涓入心,水虽甘冽,不宜生饮。
科学饮用,君当牢记,天地开泰,幸福安康。
以卡取水,唯收水卡工本费,免费用水。由是天明即有人提水,天黑尚有人等候。院内方便,院外住在后沟的几户职工原本取水方便,现在停供,自然不悦,给他们配了钥匙,规定放水时间,方释然。引泉进院深得民心,谈起此事连连称颂。有人一日数次接水,拖地洗衣皆用此水,有时造成水荒。有人不忿,我开导:哪个羊群没两个乏羊?水至清则无鱼,禾与草共生方为大同。
院内山下有一平台,下铺供热管线,拆除倒土颇有周折,便趋利避害,整修平坦,拟建一亭,供人休闲娱乐。亭分数种,雕梁画栋者为上,非我等财力所能建,于是确定朴素大方牢固可用即可,数次考察,建亭材料皆为防腐松木,但报价悬殊,本地老板心重,同样材质、样式、规格,三五万不等,我们选定福建驻延陈氏兄弟建造安装,一万二扫地。此亭因在小区临山处,遂命名:观山亭。有亭必应有联,我拟二联。
首联:山随人心高万丈,
凤鸣长空云自在。
次联:初心不忘满目皆锦绣,
高山仰止气象总万千。
联虽拟好,只可用其一,便利用人脉资源广集众议。领导言:首联意境深远,格局宏大。风俗学家言:次联贴近生活,接地气。剧作家言:首联大气。企业家言:次联简洁。众位都是某一领域翘楚,于是我踌躇数日不能决定。朋友来访,他从厂里调到某事业单位办公室,现在经商,见识不凡。我请教于他。他言:首联旷达高远,超然世外,颇有禅意,适于名山大川;次联合锦绣苑小区之名,山下建亭,亭是寻常亭,山是平凡山,可思厂也曾繁荣,也曾衰落,今又崛起。闻听此言,我便给福建兄弟发信过去,心中再不纠结。
砖墙砌就,恰似排兵布阵,颇有气势,但点亮工程让我作难,继续用老式电灯,不伦不类,颇不谐调。在晚上几次观看城中景观,决定铺设灯带。考虑到天长日久,耗费电能,决定与目今路灯一致定时,天黑即亮,夜半即息,拂晓再开,天亮再息。
做事不易,将好事办好更是不易。众口难调,众口铄金,必须要沉身尽力搞好调查研究,摸清众人口味,一碗水端平,才能将好事办好,皆大欢喜。
种烤烟
我们村是上下川道几个公社最早种烤烟的,这让我们村人自豪了一辈子。
记得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中叶,我十一二岁、在镇上念初中时,村里开始种植烤烟。我想,为什么公社选择在我们村种烤烟,一是我们村平地、梯田、川地多,适宜烤烟生长,且交通运输方便,二是我们村的党支部一班人觉悟高,党性强,党叫干啥就干啥。
毕竟是四五十年前的事,年代已久远,加之那时物资匮乏,只关注衣食,故而对种烤烟的记忆时断时续,甚至有些模糊,动笔时在脑中捋了又捋,总是不太连贯,便就按真实的记忆记录了。
一日,大队砖窑里住进了一个人,听哥说,他是烤烟师傅,大家都叫他贺师(数年后进入社会才悟到他姓贺,贺师是尊称)。贺师发际高,脑门发亮,身材倒是一般,穿一件蓝涤卡中山服,整洁、干净,一看就像个公家人,加之操着一口不同于蟠龙川方言的外地话,与众不同,便产生一种神秘感,让人肃然起敬。村里老幼妇孺大小人等皆对他待若上宾,说敬若神明夸张,但对他不笑不说话,就是平日一脸严肃的村支书也对他和颜悦色,现在想来,敬仰佩服他的本事,技术为主要,次要的是上面派来的,身份不同。村里专门给他办了小灶,配备女炊事员给他一日三餐做饭,当然这做饭的也要长得周正,穿戴齐整,并且锅灶利索。名义上炊事员回家吃饭,但站衙门,哪能不挨两下沾光板子,总沾点腥荤。于是,这炊事员必定是村委会领导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了这个小灶,上面来的干部,村上头头脑脑也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打牙祭了。我哥当时是大队电工,村里磨坊、煤矿、医务室,以及每月来放电影的接电,也算炙手可热,故而我知道的情况多些。
一队的烤烟种在龙王庙坪,二队的种在场坪,三队的种在下坪,四队种在后坪,都是土地肥沃的水浇地。绿油油一片,风摆绿浪,煞是好看。炮楼似的烤窑建在二队的坪里,与公路相邻,与贺师居住的大队部一眼可望,百十米,方便他上下工,且站在院里就可照见烟囱烟雾浓稀,随时掌握烤窑火候动态。
贺师出了一件事,几乎要了命。房中的电灯不亮了,他架上梯子爬上窑面,检查电路,被电触击,仰面八叉甩到地上,幸亏旁边是医务室,惊动村人,卸下门板,放上去,做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好半天,才悠悠醒来。但后脑勺磕烂了,绷了几天绷带,我们感觉极像电影上国民党的伤兵,故记住了这一骇人情景,此事也给我们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使我们知道了可爱的电也很可怕,会要人性命。白天贺师是忙碌的,指导收、贮烤叶,以免损伤叶状,降低品质。晚上,他的房子灯火通明,烟熏火燎,这里成了村里人玩扑克牌百分、升级,或者听“古朝”的场所。那时农村贫穷,村里虽然通上了电,但有的人出不起每度2毛4分钱的电费,还点着煤油灯,有的虽安上了电灯,但舍不得开灯,形同虚设,有的虽然也用,但只是亲戚上门或家中有重要事情才开灯照照。故而,贺师房子的50瓦电灯吸引着他们。农村的精神生活贫乏单调,在这里可以蹭贺师一半支盒装纸烟,更能放心大胆把散烟沫装进旱烟锅,也可卷成喇叭,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贺师有的是烟沫子。女人们也在这里既谝家长里短,又做了针线,纳鞋底,缝补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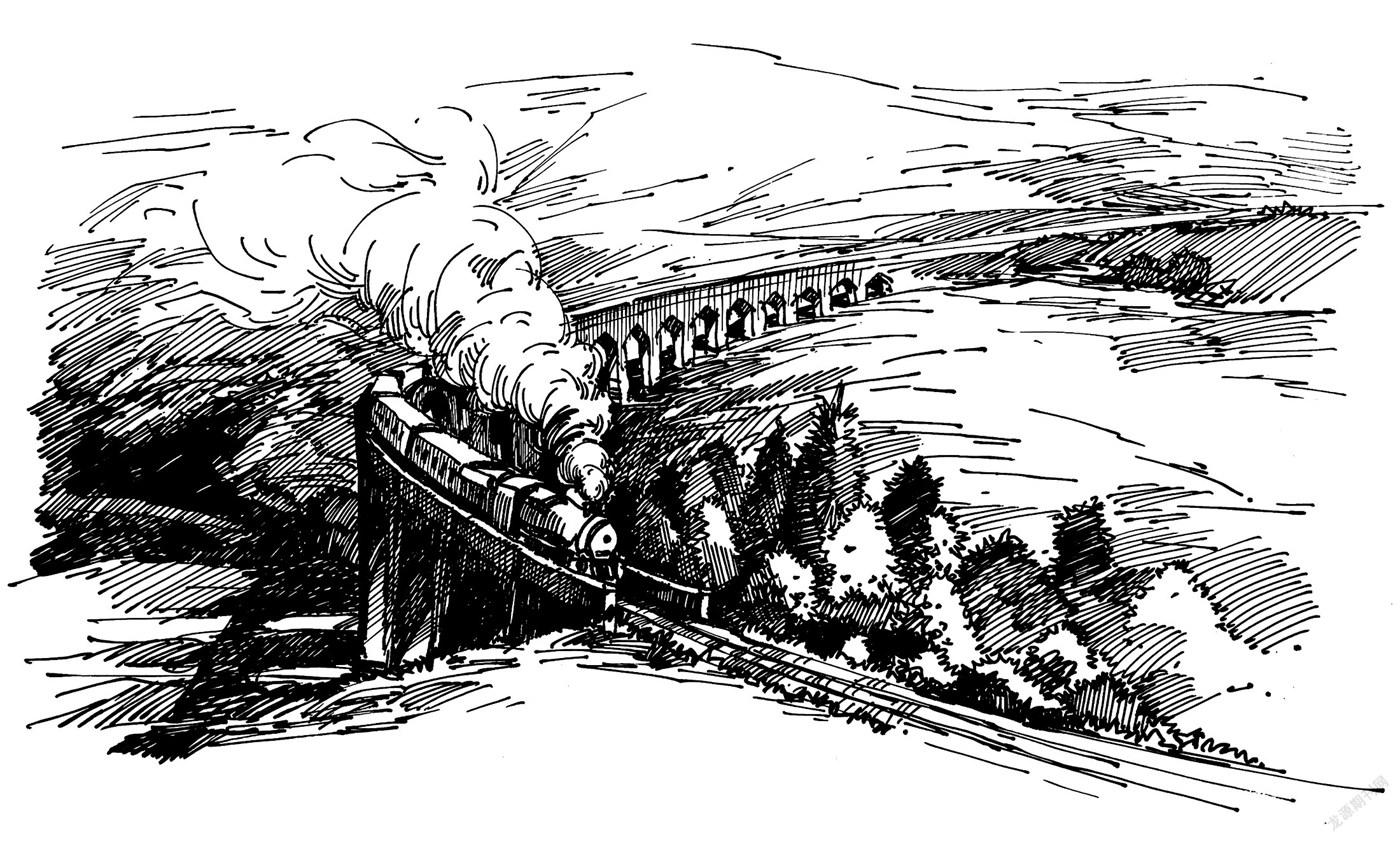
碧绿肥硕的烤烟出炉,便涅槃重生,金黄,苗条,烟香在村子弥漫。队上虽三令五申不准私拿,并派专人值守看管,但家家户户还是或多或少有了这物。老烟民们说不如旱烟过瘾,但不花自己钱的烤烟还是驯服了他们的口感味觉。也是不用花钱,加之好奇,随众心理所致,我们这一茬少年也都耳闻目染,加入了烟民行列。从古至今爱沾光占便宜的陋习无一例外地诠释了人性。我们起先用作业本卷喇叭,后来有人不知是发明还是从别处学到制作卷烟机,用薄木板做一木槽,卡一细棍,将选好的平展烤烟叶放进,推动木棍,我们叫卷烟的雪茄便制成。工艺简单,程序单一,但烟叶不可太干或太湿,太干则脆,卷不齐整,太湿卷下的瓷实,难吸。只有用稍潮的烟叶卷的雪茄既美观,又易吸。我们觉得可与当时供销社卖的唯一的“工字”雪茄媲美,但没有“工字”劲大。年轻人爱慕虚荣,在电影中看到斯大林不离口的烟斗和邱吉尔叼着的雪茄帅气,便竞相模仿。我也偷偷拿出父亲的烟斗,跟伙伴们炫耀,自然遭到父母的严厉训斥。我们上学时书包装着雪茄,与邻村的同学易货,与毛沟村的同学换果梨,与纸坊坪、纸坊沟的同学换麦面馍。这股歪风邪气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从老到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烤烟虽然对我们的身体没有造成明显的伤害,但侵蚀了我们稚嫩的心灵,使我们村这一代男性大多从少年时便沾上了烟瘾。但记得村里女性只有我一个大奶奶抽烟,这是缘于我们土著根深蒂固的传统守旧观念。村人对女人抽烟颇不以为然,我这个大奶奶也总说自己有个肚子疼毛病,“只有吃上一锅烟才能止住”,众人方才不太说三道四,但还是有几分不屑。
贺师什么时候离开我们村,他此后的情况再未可知。前几天,我与大哥谈起村里种烤烟,哥说他叫贺志强,是南川临镇人。我们村什么时候停止种植烤烟,我亦忘记。但隐约记得大约80年代末全市大规模推广种植烤烟时,政府硬性分配任务,村里又大面积种植了几年,但由于烤烟收购站标准高,等级严,获利微薄,烟贱伤农,便消极抵制。到90年代末实行退耕还林,虽然平地尚在耕种,但再不强制种植烤烟,基本还田于粮食作物了。此时的农民,终于摆脱了婆婆,有了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志愿种植。
至此,我們村的种植烤烟史彻底结束了。这段历史的始末,只有60岁以上的人尚知一二,而关心这段历史的人则少之又少。我用文字将它记录,无关乎对错,只是觉得它毕竟存在过,那高耸的烤窑烟囱的烟雾曾经融入过故乡蔚蓝的天空。
——选自西部散文学会微信公众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