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过江浙一带许多古村落,都少不得敞开几座颇有历史根基的大门大户,也免不了摆出几件古董旧物,一沾上名人雅士之气,一贴上某朝某代标签,便似乎得了尚方宝剑,可以轰轰烈烈地以此为凭大搞旅游建设,吸睛无数,村子犹如注射了一剂长生药,好羡慕这样的村落,以此为家乡,人生之根就可以深深地扎下去。
苏州虎丘山北麓平平展展地卧着一个大村落——北庄,原名北庄基,除了两块石碑是清朝的,其它而言:外部平淡无奇,内部局促拥挤,于是在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建设中注定要经历一场变迁。历史是一张网,只张罗大鱼巨蟹;历史也是一只沙漏,无情地筛漏那些细沙碎屑。村落,也像人,如果不足以伟岸、巨大,终将陨灭在历史长河。一个无名之辈面对一个无誉之村的殇情,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码些文字,也注定随风而去,一如烟云。尽管如此,还是忍不住地要在它拆迁之际倾尽歌咏之心,这个村落终究是我们一群渔民后代的家乡啊!
北庄内塘养鱼的历史,从春秋时期开始已有两千多年,《苏州府志》《姑苏志》和《吴县志》中均有记载。
越国大臣范蠡协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为民携美女西施驾着轻舟来到蠡口、黄桥一带隐居渔猎,留下了西施浣纱西堰栅的美丽传说。汉武帝年代,约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间,无锡的葛、金、沈三姓人士驾着三只扁舟为奔波生计寻觅而至,在黄桥北庄地段捕鱼为生,搭建棚户,落户定居,繁衍后代。
一个地方从某一历史时期走出,如若辉煌过,必定会留些遗存。北庄村历经一个又一个时代,却鲜有像样的遗存,世世代代渔民在这片土地上自给自足,随着时节行走,兴而后枯,枯而后兴,一茬又一茬,小草一样生生息息、平平凡凡。即便许多当下老者曾经见证过解放前村内的大户人家,有一座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还做过北校校址,终究也抵挡不住历史潮流,湮灭了。
世世代代的渔村居民,一代又一代在此繁衍生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数十年间,渔村在人口爆炸后,以老庄基为核心,向东南北三个方向辐射发展,一跃变成了一个超级渔村。
浩浩北庄村,709户民宅,基本是兴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式小楼,或两间开,或三间开,粉墙黛瓦,也不乏掺杂一些戴绿色或红色琉璃瓦帽的小洋楼,它们从南木圩、小河南、老庄基、河南巷、湾堂、长村、里浜、摆渡口、短浜上、独水墩、三家村,一路覆盖,绵延整个北庄大村落。东塘河、门前浜、前浜、后浜、苏州河等自然的河流或截、或穿、或围、或隔,错综其间,民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形成了自由贸易的小集市,颇为热闹。俯瞰村落,犹如一只庄鸡正在虎丘山麓的三角咀东边振翮扑食。
时代的洪流流经村落,村落陷入不堪重负的困境,场面高低,村巷窄小,加之地形复杂,汽车难以入内,村落无法适应膨胀的发展之需。姑且在各处开膛挖肚,螺蛳壳里做道场,零星地建立了几个停车坪。然而,仍然逼仄。
当拆迁放上具体的议事日程,村民便掰着手指历数家珍。这个渔村中能当得起家珍的便是两块石碑,它们一如这座渔村被封存的两枚历史印章,又像遗世的老人。一块为《奉旨勒石永禁》碑,行文繁复地详细记述了一件清朝时期的渔事。内容为北庄渔民受生活劳作之逼,联合起来与黄天荡湖霸荡棍开展斗争,获得了官府支持。另一块为《奉旨遵宪蠲免渔课永禁泥草私税》碑,所刻碑文有长洲县渔民陆江、葛华等43人呈告当地豪强地主和渔霸向渔民横征暴敛私税的情况、苏州府海防厅查询的情况、清地方政府对吴中豪强私征渔税的禁令梗概。
石碑为凭,北庄渔民养鱼从此走上了一段太平昌盛之路。
清朝的石碑静静地矗立在21世纪村民的小楼前,当年的“永禁”早已不复再起作用。然而,石碑终究镌刻着这个村落中渔民曾经流淌的血泪,在渔村和石碑决绝断离的拆迁节点,令人感叹的是主人行将离去,但石碑却像一对被卸下的翡翠镯子,执着地留住了主人的血脉,带着这份渔村的气息,石碑何去何从?也许会静立某博物馆的一个角落,没有风餐露宿的困苦,却再无渔民激浪的豪情回响。
关于北庄村养鱼,民国版《吴县志》载曰:“介于阊齐二门之南北庄基,均以畜鱼为业。其畜之,也有池,养之也有道,食之也有时,鱼有巨细,以池之大小位置之,时有寒暖,视水清浊调和之,大要春夏宜清,秋冬不妨浊也。食有精粗,审鱼之种类饲养之,鲭鱼食螺、鲩鱼食草。防其飞去,置神以守之。”寥寥记述,从中隐见养鱼之繁复和渔人之艰辛。
北庄内塘养鱼确非顺风顺水,在历史长河里,渔民靠着一条船风里来雨里走,成就了淡水养殖业,培养出了闻名遐迩的北庄粉青鱼。渔民劳苦功高,渔船功不可没:渔船是渔民的脚,行走四方,奔波劳碌;渔船是渔民的心,颠簸水流,随波忐忑,操劳辛苦。
而一只渔船之于一条鱼儿的意义又何在?
渔船是鱼儿流动的家。一条小青鱼苗,原非土生土长,来自遥远的长江滩涂,一只渔船千里迢迢逆流而上取得鱼苗,小心翼翼,呵护备至,鱼苗方能得以抵达北庄村西三角咀水域大大小小、规格不一的花子潭安家落户。一条渔船犹如一个流动的家,它长途跋涉改变了一条幼小生命在长江水流里野生的命运。到得池内,喂以鸡蛋、辅以豆浆,渔民对于一条鱼苗的呵护也许胜过爱家里的子女。
渔船是鱼儿备食的舱。一条渔船也许曾经奔赴过阳澄湖、金鸡湖、独墅湖、黄天荡,渔民历经一场辛苦的捞草劳作后,渔船驮满沉甸甸的水草,老牛一样,涉水而归,草鱼却有了饱享的福;一条渔船也许还曾奔赴过太湖,渔民借此流动的水上平台吸回满舱的螺蛳,又涉水而回,青鱼却有了饱食的乐;一条渔船还曾奔赴过苏州市河,历经与各种船儿的博弈,终于在激流里不辱使命运回一船舱糖糟,够鱼宝们饱食终日,享乐无穷。
渔船也是鱼儿行走的脚。北庄村的渔民好个勤劳智慧,先前从长江里淘来鱼苗,后来科学养鱼,自己培育金贵的鱼苗,开启了传经送宝之路。春日里,渔船肩负新的使命,承载鱼秧,外出送达四方八邻。冬日里,渔船装满肥硕的粉青鱼,奔赴上海,为上海人岁末年终的团员宴增添美食。船儿奔走四方,风雨飘摇,运载鱼儿,抵达目的,无怨无悔,矢志不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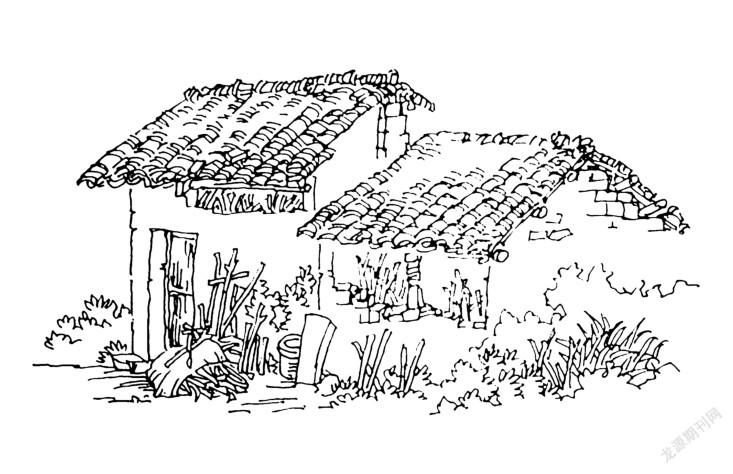
渔船从晨曦里出,从暮霭里归;渔船从静波里去,从风浪里回。一条渔船在历史里行走了两千多个年头,终于苍老了船舷,斑驳了船艄,船橹累了,搁下无力的臂膀,停歇在21世纪的渔村,像一位疲惫沧桑的老人,她睁着浑浊的双眼,看一眼村外马路上汽车的绝尘,静静地睡倒在通关桥边塘河滩头。风雨里落下的尘土淤积在船舱,滋生一丛青草,祭奠曾经劳碌在渔村的生命之船——一个仿若呵护了众多鱼儿的老妈妈。
一条渔船,能奔波,能运输,能储藏,它用两千多年的坚守,让一条北庄的粉青鱼名扬四方,曾经有村民无比自豪地抱着鱼儿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北庄内塘养鱼大村的名声让村民攒足了底气。
然而,一条童话一样崛起的青鱼在历史的舞台上迅速地隐退了,时代的车轮在渔村边轰鸣,渔民上岸奔波新的营生。丰富的物资里,鱼儿找不到自我;曾经污染过的水源里,鱼儿无法宁静。鱼儿呜咽,决绝于21世纪的河流。石碑见证了渔民曾经为一条鱼儿所做的努力,却没有记下一條渔船的功勋。
2018年的春天,北庄渔村拉开了拆迁的大幕。21世纪20年代前后数年之间,渔村断断续续拆迁了,一本书写了两千多年的吴地渔文化,沉重地合上最后一页,留下的既有失落的伤痛,也有重新崛起的欢愉。
拆迁之际,村西口的三角咀湿地涌动着一股股春潮,似乎在说:历史不会忘记。是的,历史不会忘记:
那条船儿虽然没能久留,但也许变作了村头上空的弦月。
那条鱼儿虽然没能久留,但也许化作了渔村居民的血脉。
拆迁后的村子不再,然而,渔村居民的血脉尚存,渔文化的基因密码仍然可以鲜活,鲜活在每一个乡人心中,永远永远!
——选自西部散文学会微信公众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