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是个谜。
四十年前我不这样认为,它就是我隔三差五路过的一个小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睁大双眼,努力在认识它,猜测它,探究它,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谜,一个待解的谜,一个难解的谜,一个不知驴年马月能解开的谜。
我对石峁的认知是模糊的,远没有现在专家学者文人墨客对它的认知与猜想。但我和石峁的渊源颇深。
在我的少年时期,最熟悉的三个地名就是高家堡、石峁、葫芦旦。高家堡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的居住地,一个具有五百多年历史且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古镇。葫芦旦是我母亲的出生地,一个夹在大山里的瘦弱的小山村。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的十八年一直生活在这里。石峁村就在高家堡与葫芦旦之间,一头挑着厚重的高家堡一头挑着瘦小的葫芦旦,现在也挑着,我从没听过它哼唧过一声,不知久远,默默无言。谁知道它竟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的少年时期基本上与半饥饿相随。吃不饱饭是常态。小小的心灵有两大盼望,一是盼高家堡赶集,这样外爷就会来到我家,不是拿二升谷米就是拿一袋山药,用来补贴我们这个恓惶的家。放学后,我看到外爷坐在我家的炕沿上,一边抽旱烟一边和母亲拉话,话题就一个,让母亲再艰难也要供我念书。完了烟锅子在硬硬的老便纳鞋帮上磕几下,收拾起褡裢乘夜幕未落回葫芦旦,临出门,还不忘掏出二毛钱给我。母亲再三挽留她的父亲吃饭,外爷说他要早点回去喂牲口,下次吃吧。外爷知道,我们家没吃头。二昐星期天,我会借口想外爷外婆了,给父母说一声,一个人就去了葫芦旦,为的是吃两顿饱饭。高家堡距葫芦旦十多里,全是山路,唯一穿过的村子就是石峁。孩提时代我对石峁的认知就是这个小山村石墙特别多石堆特别多坟头特别多。偶尔在石堆上能看到些模糊不清的石人人,有鼻有脸有眼睛,形态各异,表情夸张,奇奇怪怪的,比现在的石匠打造的人人马马水平高。
说心里话,石峁是黄土高原上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山村。海拔也不过千二三米,山势颇为平缓。石峁村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人家散落在北面的山坡上,这面山坡比较高比较陡,也就是现的黄城台下。一部分人家居住在南面的缓坡上,窑洞就建在庄稼地畔,也就是现在的外城。南北两山的中间有一条又大又长又深的沟,沟掌的山坡上住着七八户人家,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内城。我五妈的娘家就是石峁村的,就住在这个“内城”里。我五妈的两个兄弟都长的人高马大,眼睛珠子特别明亮,每每遇见我穿村而过时,不无讥嘲地说"街爬子,又饿得不行了,又去葫芦旦寻吃格呀!”我眼泪汪汪,真想拾起脚下的石头圪蛋砸过去。
石峁的这条深沟有一股流水,不大,但能听见响声。因为它在嶙峋的乱石中穿行,那不屈不挠的行走溅起了一路激响。它在二里外的石东门口拐了个弯流入洞川沟,再流入秃尾河,最后注入黄河。前几年我在佳县白云山下的黄河畔溜达,看着奔涌的黄河,踩着大小错杂的河石,常常想,哪一股水是石峁沟里流下来的,它挟带着什么,灵气、仙气、神气?还是一股神秘风。它流入洞川沟后就变得浑浊了,裹着泥沙碎石,磕磕绊绊,不招人喜爱。不过,黄河的水一直没清过,一直是浑的黄的,尤其在晋陕峡谷,就是一条奔腾的黄龙。
石峁是个美丽的小山村。四季分明,景色宜人。春天满山遍野的桃花杏花一嘟噜一嘟噜开着,濡染得严肃深沉的古墙也温和了许多。墙上生出的暗黑色的苔藓仿佛也绿了不少。我最喜欢的还是香喷喷的槐花,捋下就吃。对当时又饥又渴的我来说,无异于一顿美餐。石峁村的人也吃槐花,他们用槐花炒炒面,摊饼子,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夏天葵花遍地,太阳照上去,硕大的葵盘金黄无比。更奇异的是,石墙上生长着一蓬又一蓬的柠条,蓬勃茂盛。柠条花金黄透亮,香气独特,沁人心骨。每到七月,柠条角角成熟了,里面的籽要蹦出来,柠条角角就噼噼啪啪地响,炸裂声,颇震撼!有的柠条角角直接跳到地上,打着滚,翻着筋斗,那分娩的痛苦,不忍睹。柠条冬抗严寒夏抗高温,防风固沙保土老足劲了。柠条根柠条花柠条籽皆可药用,消炎去肿。石峁的石墙千年不倒,我想肯定和石墙上一排排生命力旺盛的柠条有关系。石峁村的香瓜在周围几个村数一数二,又脆又甜,好吃,俗称"老汉绵",适宜上了年纪的老婆老汉们吃。我夏天路过石峁村时,总要偷着吃两颗。一般石峁村的香瓜地都是村集体的,大的四五亩,小的一二亩。一般大的香瓜地村上在瓜地中间搭个二层木架子,一层铺满干草,上面垫个棉花褥子,再上面铺一张黄或黑色的狗皮,旁边放一床黑不溜秋油不拉几的被子。二层是用来嘹望的,防贼偷。村上照瓜地的人不时站上去四下望一下,看有没有偷瓜贼。我一般选择大的香瓜地,在地畔下的土壕里埋伏半天,等到亮红晌午时,主人燥热得呛不住打起了瞌睡,我蹑手蹑脚地爬在瓜地旁,迅速摘下兩个先前瞄好的大香瓜,一骨碌溜入土壕,渐渐远去。以后被石峁村人发现了,他们热情地说,你不是葫芦旦换换(我舅小名)外娚吗?来,进来吃小瓜。母亲以后也知道了这个事,严肃地对我说,想吃,就大大方方地进瓜地向人家要,你就说你外爷的名字,或你舅舅的名字,说我的名字也行,千万不能偷。这是不光彩的事。我鸡啄米似的点头。秋天糜子谷子向日葵都熟了,惹得鸟儿雀儿山鸡雁咕噜们都争着抢着去田地里觅食。尤其灰野鸡,胖乎乎毛格茹茹的,七高八低站在石墙上,风吹得浑身的毛尖尖抖抖索索,它们仍站在石墙上东张西望。有时,我扔一颗土圪垯过去,呱呱叫几声,轰一声就散了。我常常看着它们发呆,石峁山上散落的粮食,足以养活它们。我去葫芦旦外爷家,不也是为了一口吃食嘛!糜谷的杆杆,瘦瘦的杆杆,都顶着沉重的果实。像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勤劳一生,没过几天像样的日子,像土圪垯一样活着,去世后又归于深不见底的黄土里。要说石峁四季最美的,我觉得还是冬天,尤其是雪后。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黄土高原的苍凉与壮美,起伏与宏大,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描述得让人心旌摇荡,永生难忘。雪后初霁,古老的石墙明光究赞,映射着神秘之光,仿佛在召唤远方的人们来探究它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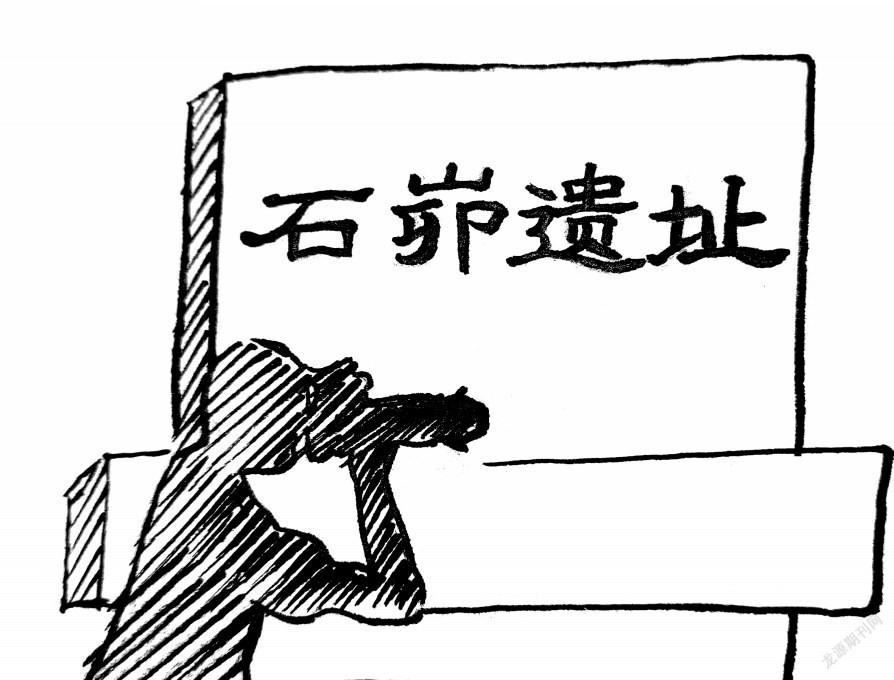
我对石峁的认知荒废了若干年。我真正关注石峁是我上大学后。我从有关资料上得知,1929年冬天,就有4个高家堡商人去北京卖玉,用褡裢装着,卖的是石峁玉。有玉刀、玉铲、玉璧、玉璜、玉琮等。据说最有价值的是一个牙璋,形体硕大,透出威仪。这些玉器被一个外国人廉价买走,至今躺在德国科隆的远东艺术博物馆里。每逢寒暑假回到高家堡,母亲总给我讲,派出所又抓住了多少多少石峁盗墓贼,咱堡子的谁谁也参与着了,被派出所上了铐子,铐在派出所院里的电线杆上,丢人哩。我就问,石峁上究竟有甚了,住过谁,发生过什么?母亲也不甚了了,只说古代石峁上住过两个女王,是亲姊妹,都武艺高强,拥兵过万,后来反目,自相残杀,直至衰落。母亲讲的,我询问了不少高家堡老年人石峁村的老年人葫芦旦村的老年人,他们不置可否。
石峁真正出名,是一个叫戴应新的人来到了石峁山上。他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又是西北大学教授。1975年的冬天,他在高家堡收购了127件石峁玉器,回到西安后,他大声疾呼,石峁是个谜,考古价值巨大,应该迅速展开田野考古,勘察挖掘探寻。然而,一个学者的呼声毕竟微弱。直到2011年,省市县才联合组成了考古工作队进驻了石峁村,神木市也随即成立了石峁管委会。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纷涌而来的实物与信息惊天破石,令人目不暇接又瞠目结舌。一座4300年前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巨大古城横亘在面前,一个具有完整的社会阶级功能的国家形态展现在面前。一个又一个谜面揭摆了出来,一个又一个课题需要探究破解。石峁玉从何而来?为什么要插入墙体?四百多万平方米的巨大石城如何筑就?石料從何而来,庞大的劳力从何而来?是役使还是专业造城队伍?石人人石马马及刻在石头上的符号图案是谁的图腾?部落的还是哪一国的。外城门口发现的两处四十八颗少女头骨,是杀戮还是祭祀?东门瓮城墙上新发现的彩色壁画谁人而为?是展览还是记述?能把中国美术史前推多少年。石头王国是缘何兴起,是不是黄帝的昆仑都城?它和三百年太史公记载的"三皇五帝"中哪一位有瓜葛?黄城台里居住过谁?为何建在一块巨大的整石上?它是如何毁灭的?是毁于战乱还是灾荒?这块苍凉而神秘的土地上,倒究发生过什么?虽然目前所掘物证,已把中华文明向前推了三千年。有的专家甚至把石峁考古标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但一系列的发现还需严谨而科学的论证,绝不仅仅是猜想那么简单。考古就是破案,只争朝夕,一百年也不远。
我家的祖坟就在石峁山上。准确地说,就在石峁的外城里。我不得不佩服先祖当初看坟地时的慧眼,也许是请了一个风水高手吧。他们绝没有想到,他们的长眠之地,竟是中华文明的一块圣地。为此,我万般自豪。
——选自《榆记》微信公众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