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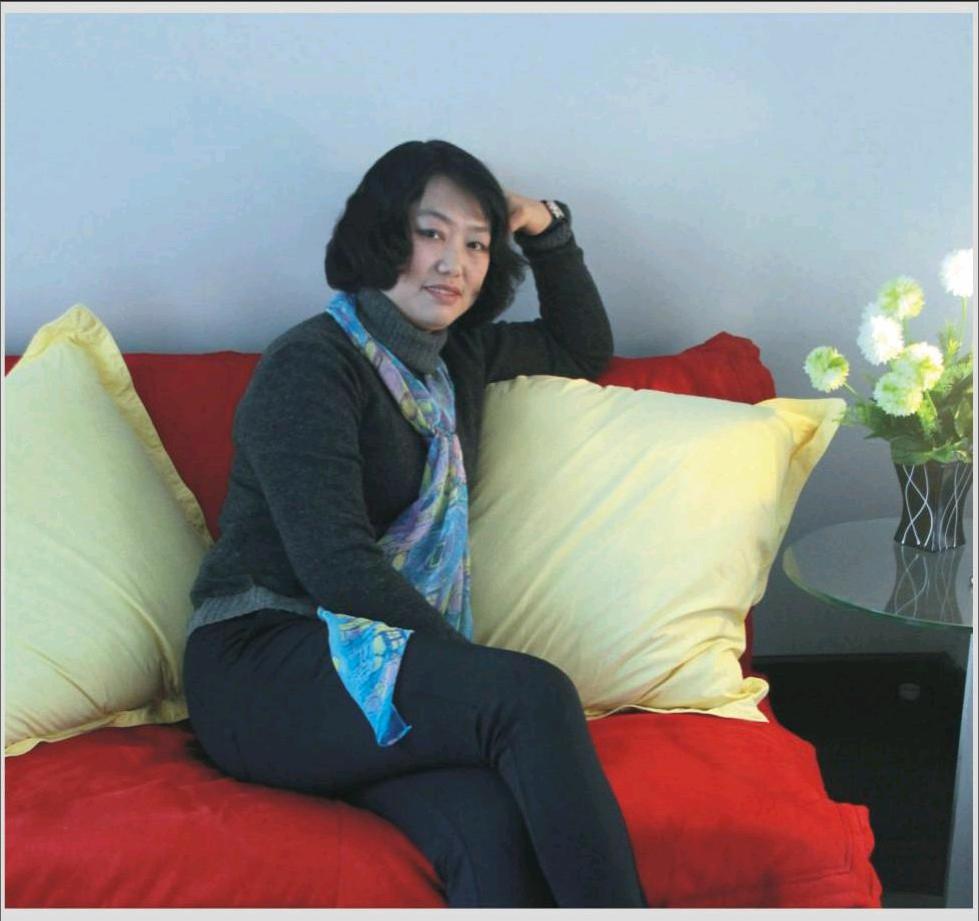

现代蒋经Modern Poetry
陆新民,男,安徽南陵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经济师。服过役,造过桥,现供职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晨之光(组诗)
陆新民
陆大村
他们一个一个走向我
他们叫着我自己都陌生的乳名
他们说,你还认得我吗?!
我现在惟有呲着牙笑
有十年没回祖籍之地了
无法形容的俗务使我
忘却了这片热土
打谷场,水塘,祠堂,祖上的坟冢
整齐的,一层一层过渡的村落
一直在拍手致辞的白杨树
刚才还迷糊的我,一下活泛过来
我知道这些亲切看着我的人
全都是我的亲人
我在他们的身上
依稀,听到父亲的声音
看到父亲的面容
我开心地,又不无歉意地笑着
我握着他们的手
紧紧地,从未那么紧地
和别人这样握手啊
我知道,这是亲人的握法
这一握,血脉贯通
我是代表父亲回故乡的
我感到云天之上父亲的垂询
我所有亲爱的亲人们
他们正欣喜地看着我
这相逢的一刻
让我无比轻松,也分外动容
晨之光
丘陵的国土上,有一片
小平原。当年
我们仨,粮食收购协助员
某天,自南向北,在圩堤上行进
稻浪,迎面扑来又向后涌去
一首不知名的旋律
轻抚七月的晨光
这时奇异的景象发生了
一个伙伴在喊:瞧!
在我头顶上
向左一瞥,我发现
自家头顶上,罩着
一个长长的
光环
另一个伙伴也说:啊
我头顶上,也有一束光呢
我们停下,比量着
震撼,惊骇,转而缄默
(这光,为何在圩堤上
在追着罩着自己,旁人却看不见)
我甚至想到口吐剑光的仙侠
白、青、红、紫
多年后,我寻找这本地下流传的演义
却忘了它的名字
西宝线上
穿越,明亮的阳光
一排排苹果树
——树上间或挂着黄纸
我往宝鸡走
多么适宜人居住的城
多年前,我曾想
是否带着牙具来此旅行……
远远的,石鼓在喊着甲骨文
我无法读懂
“关山草原的蚊子大如蜻蜓
不咬人……
骏马,蓝天,篝火……
去,只消半个时辰”
我甚至想卖掉南京的房子
来炎帝陵脚下
买套三千平米的别墅
来吧,都来我这里小住
诗人
像炎帝尝百草一样生活
一张黄纸,经幡一样
又飘在我眼前
我始终没有问明它的用途
我想肯定与古代和传奇无关
就像我,一名
流连在西宝线上的不速之客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一年之内,两次
来到这里
你的生命比我久长
“看一次就少一次”
每一次,都有独特的发现
那些青铜器,那些
精美的纹饰,那些
我知道用途,却每每读不准的字
隔着厚厚的玻璃
想到我的故乡
青铜的故乡
三千多年前
南陵大工山,铜的冶炼
这里的青铜也来自我的故乡吗
放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诗仙
在烽火岁月,可曾暗渡陈仓?
而今我坦然来去
一个诗人的怀旧,绝非矫情
在青铜打造的历史面前
我久久地站着,我
可是那辆隆隆向前的战车上
一枚小小的铜钉?
隐喻
在某些雷雨交加的夜晚
我会想起你,与你同一脸形的人
你在赶一程路。我们
共同沉浸于往日
焦灼的灵魂不再狂热
我记得那条河,那条小路
你轻轻打开车门
裹挟一片薄云
把雷霆拒在门外
此刻我要说明,我理解你的行事规则
包括天光灿烂时
所有的不能理解
“我在等着你回来”
我已缓缓老矣,如同透支的尘埃
对手
我们和时间,永远的对手
桌子上——
一只铁水壶,内心温暖
外表已悄悄锈蚀
网球大的一对苹果
蹲在一张纸上
李白隔着一层玻璃
嗅到它消退的香息
轻松学开车的系列光盘
古堡形状的储物罐
占据半个桌子的书报杂志
挤在了一起
时间是看不见的
只在这些物件上
加一层隔天的尘埃
仿佛一个无头案,悬而未决
我告诫钟点工:请勿动我的桌子!
我不是时间的对手
仅仅是,在还有气力的时候盯着它
我喜欢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
与时间对峙
章凯,1969年生人。2003年开始诗歌写作。有作品在《诗歌月刊》、《十月》等多个杂志发表。
章凯的诗
沟壑
我立于窗前。看得见风——
吹过窗前的杉树。
却听不见任何声音。
那——
羽毛般的树影,飞舞着,
攀上它自身的树干。虬枝
像其上的鸟儿们一样,不断地向广袤的世界彰显
它们的影踪,存在又丰硕。
它们要以此呈现它的无限魅力,
而我的心那么迅速地占据了这一切。
如同一片落叶飞过深深的沟壑。
如同干旱紧接着降临。
雷鸣
甚至连那雷鸣也会消失。
那么,如果
两只鸟儿一起飞临在天平上,
能有瞬间给出那结果吗——
孰轻孰重?
灾难不足以驱逐妄想。
然而,我们的颤抖足以弥补
雷鸣的消失。
前面
死亡永远在太阳前面。然而,
太阳初升,就将死亡遮蔽。
我们看到情形总如是。其实,
我们已无土地可以栖宿。
而当幸福仅来自于忍耐,
观察他人,使我们的灵魂
只有树枝之高。 当
微风轻拂寒冷入侵,使我们的
白发下沉,如陨石下落无语。
啊!我们太小,而
他人即天堂。
狗
像狗一样理解生活。
仰观天象,俯察大地。
一切只凝于一点。
……一切,都
从那一点唾液中滴落。
那胸膛中吱吱叫唤的,就
是这世界最雄壮的序曲。
……从来不尝停歇。
如果一条狗沉默,
它将听到一切的喧嚣。而
霹雳将是……月上东方!
那霹雳将一切抛弃!那么广阔,那么偏狭,
正如一只狗理解的生活那样。
这由沉默、围攻、胜利而组成的生活,
肉体由蛆虫最后解放,展翅远飞。
当一只蛆虫飞向高空,每一只狗也就是
每一只苍蝇。
一样地组织规模围攻,既不更广阔也不更狭小。
海,暮之海
人世间是一片甜蜜之海。那
穿过甜海的苍蝇,这镀金的花朵之灵,
快乐地叫着,在这真正的闲暇之界,
越过我们的视野。快乐,仿佛云帆
落在床单上。又升起。如同落日
自昨日它升起的那一小块地方。
这每日都将死的火炉,每日都
吐出它曾在人世间得到的一切:
所有的初次,包括死。
——清晨或者傍晚,只有暂离大地的
鸟儿们不断鸣唱。太阳!它们!
高翔万里,一览无余,向着
这美丽的世间、这熙熙攘攘无人之境、
这三千恒沙之外
不断传唱。它们传唱无所不在的虫蛀之洞。
像我们不断地传说寥寥可数的世间之始,
不断地传说,但寥寥可数。
星星索
从一个自我安慰到另一个自我安慰。
但远远不够。在远处,那明亮之光在
闪耀。星!听!它在白色的帷幕
堆积。这延展的二维世界多么广阔!
从炽热,到冷却。
一直在延展。蚁步般缓缓延展。井然有序的空间
次第开放。而那新的星空!
曾是旧的黑洞!它将抵达
它的边陲:一只闹钟在遥远星球的鸣响。
既定的,散漫的鸣响。
存在必致遥远。在这巨大无垠的星空
无可比拟的漩涡中,诞生着怎样的
事物啊。它们正不断地艰难无比地
消失。在逼窄的乡野,星空垂注而下,
瞬间就在村落中丧尽。如果我们有意,
我们将听到一声莫名惊惧的叹息,一声狗吠,
或者看到一只细蛾,在一两株草的枯黄里展露舞蹈:
细蛾:飞蛾、蚕蛾、夜蛾…蝴蝶都再次化成虫蛹。而上面,
超过上帝给予的恐惧
上帝恐惧“真正”的人,因为
“真正”具有神性。即使面对责难,
“真正”仍具有神性,甚至包括
神性的愉悦。
如雷声跟随闪电。
如同雷声仅是雷声,
我们超过一个,但并不总是
到达另一个。即使回到出发地,
一无所知的痛楚又将加深原来的破落。
记忆如是长久。
它以各种形式继传。
有时是流言,
有时是谬误。
我们不过是警觉的动物,
跟随自身的无知的指向,茫然前行。
在冰岛,不易驾驭的驯鹿
被它更加不能驾驭的激动驱策着,
发现一十三年来满地开着的
鲜花不同于往日。
如同我们发现工业革命不同于往日。
生命中的欢娱给我们一切。
但一切生命终要回到原点。
那么迅速,仿佛性能优良的车
开过笔直的大道。
如果我们曾发出呼喊,那呼喊
不过是对自己狂妄无知的回声。
如果我们曾向上帝祈祷,我们祈祷的那个
并不是“真正”的上帝。
“真正”的上帝一直无能为力,
面对人类自相矛盾的诸多祈求,
他面对另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的责难。
对我们的责难不过是两只合拢的手
忽然摊开,要迎接追缴生命的枪弹。
而对上帝的责难,是两只合拢的手,
忽然摊开,要面对撒向世间的谎言。
宛如我们抛撒在自己脸庞上的眼泪。
张巧慧,女,本科。1978年2月出生于浙江慈溪。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十月》、《星星》等十余种文学刊物及年度选本。出版有散文集《画荷的女人》、诗集《朔风无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协会员,慈溪市作协秘书长。
走失的蝉衣(组诗)
张巧慧
每个人都怀揣光源
“黑夜里走进黑屋子,你能否看到
我的眼睛?”父亲忽然这样问我。
他眼中的光一闪而过。屋子里,所有
暗的物体,都亮了一下。
这个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人发出一声响动
黑夜,黑屋子。每个人都怀揣光源。
但有的眼睛,因为不懂得
把自身的光引出来,而长久与黑暗混为一体
蜕
有些空壳,必得放下,
为自身的生长解除束缚
请在羽化之前向低处交还盔甲
体轻,中空,易碎。生命高飞
蝉蜕还保持着爬行的姿态
我曾遭遇一条蛇蜕
圆筒形,似蛇,有光泽;但压扁而皱缩,
它寄居其中的勇猛已经起身离去
(也许天生就携带障碍,我尝到了局限)
要怎样相逼,才能把蜷缩其中的骨骼
撑开来
——我正在酝酿一次蜕变
空,是最大的容器
一张方子,半世疾病。蝉衣。背上的裂缝。
惊心动魄的挣扎。我曾用一个空壳
成全生命对高处的渴望
“治外感所袭之喑哑:净蝉蜕二钱;
滑石一两;麦冬四钱;胖大海五个;桑叶、薄荷叶各二钱。
水壶泡之代茶饮。一日音响二日音清三日全愈。”
蝉蜕两钱。她是空的,空是最大的容器
相对于鸣叫而言,它淡定
有放下的顿悟,甘于永久的不语
安放我死去的无形之物
六月活着,而五月死了。
它还是一味药。试图让某人恢复嗓音。
养蚕者
有人养狮,有人饲虎,有人
一生防着花斑青蛇
与养着的这些猛兽,对峙,僵持
一分为二的人,一半化作虎
一半为虎所啖。大部分人,做了一辈子饲养员
到底只在心中学一两声怒吼
我是个养蚕人,多么
柔软啊。它长一圈儿
我就蜕一层皮。腹中的苦水
千丝万缕。吐丝,做茧
蚕食空了。它不顾一切化成蝶,飞出
自己的坟墓
现在,我像一个孤零零的空囊
飘荡在尘土中
当灵魂遭遇神
像神一样,你
有限的爱,唤醒无限的可能
爱上你的那个女人,不是我
不是那个风沙覆面的女人
因为一次遭遇,那个女人
反复擦拭蒙尘的神灯。——这个只剩下风沙的女人
上半生处于焦渴,下半生惊艳于
陌生之地
内心的荒漠,借助隐秘的力量复活。
手持星光,参与了
另一个世界的建造。因为曾经死过,
她的美,有被毁的痕迹
她观照的两个世界
一个为肉身建造殿堂
另一个,致力于为灵魂立碑
我并不因此而羞耻
是一个池子越积越深,
是池子里的淤泥不再轻易浮出水面
“人到中年,我只想
安安静静,做更好的自己。”
午后孤寂,偶尔我跟自己玩个游戏
将电线拖入水中,慢慢煮着池塘
气泡一个个冒出来,前赴后继,像无数嘴巴
吐气,诉压抑之苦。我捞起一个,空了
又捞起一个,还是空的。美丽的空洞之物
只剩下浮萍
水落石出,你该提着头颅与我相见
与我,隔着沸腾的水。
“曾经我是电,如今
我是绝缘体。”
但跳下去,我还是那么决绝
飞翔
清晨,我偷听了两只鸽子的谈话
“我要飞翔,飞到白云之上——”
“你要先适应这逼仄的屋檐,才会慢慢丰满翅膀。”
它们筑巢在我的窗台,却每天打算着离开
晨光明媚,它们从不曾怀疑飞翔的意义
每一次扑腾,都会加快窗外的风速
让人类的两腋也微微生风
我收集着一只幼鸟的羽毛
这些不属于我的羽毛像柔软的内脏
我的心口发烫
我有翅膀,却早已合上
一条河,流得越来越慢
他们拒绝泥沙俱下。灰霾,沙尘
体内的水位越来越高
魂是轻的,
命是沉的。
他们砌,把自己砌进堤坝
防备着汹涌之物
“江河之大,水不能堵
如果黄河要来,它一定要来
只能人为它让路——”
像等着最后一场潮汛。
一条河,流得越来越慢
每个人心中都在筑一道堤坝
又莫名地
渴望一次冲垮——
尘世之上,山川之下
从山顶俯瞰一个村子,房屋低小
像一堆玩具。找不到下榻的宾馆,那幢
十层高的楼房,是大地上的一株草
越接近,越被放大。尘世的一切
又变得坚硬。刚被我俯视的建筑,此刻被我仰视
山顶的人,看不到我的小。但迟早也要回到地上。
寒寒,本名孙建娣,1973年12月出生于浙江慈溪,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医务工作者,供职于慈溪市妇幼保健院,任副主任护师、高级政工师。2007年末涉足诗歌写作,有若干诗作见诸于报刊,现为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
小乍现(组诗)
寒寒
昨日谷雨
昨日谷雨
消息源于一友人博
他正用一连串美好的修辞点缀
他的生日。主题盛大,场景落寞
想他必定等急了果实和新绿
看看窗外,果然落英缤纷
无限老去的春风啊,你真该做个回应
留他一点时间
在下一个立夏来临之前
在这场生死爱的虚构和现实中
从容交出
妥协和热爱
花事如朝
晓雨初歇,众身不惑
赶赴一场五百公里开外的山野之约
所谓花朝月夕,红尘深深
义无反顾地
只为趋近更强烈的明媚和闪耀
必须在花团锦簇中牵出一匹白马
让一再蛰伏的心
跃出沟壑和黑夜,正好
山脚有渡口,彼岸烟火清明
而尘世如灵犀
说来,就来了
越过他的蓝
越过他的蓝
她瞥见暗礁、歧路和陷阱
乃至险象环生。是谁动了
那条内心的河流
——宁静、舒缓、疏阔、沉邃
从此,一去不返
一去不返
一剂处方还没下来
时序击鼓催花
小满刚过,沉默布满缝隙
静候一场荼靡秀
嗟叹突击而来,兀自演变
喋喋不休。我从一杯凉薄的茶水中找到你
面目无助,暗露不羁
道别。耳畔弦犹微振
是谁又在窃窃私语:
疼痛是一种高贵的克制……
嘘,一剂处方还没下来
让诗经沉睡
让夜风缓缓吹凉夏天
植物小常识:水芹和水蕨
相比楚葵或蜀芹
还是如意莱或长寿菜
这些响当当的别名
我更偏爱龙须菜、龙牙草
甚至牛草、水英……
乡野气赋予它们独特的功效
据说皆可捣汁外敷内服
并入脾、胃、大肠三经
奈何春色无端,即使有心托杜鹃
水灵嫩滑亦终究会被老气横秋取代
独留山野静默,故园零落
而你却说——“常识之外
总有无量的惊喜”
小美食之泡椒凤爪
它们的结合绝对是
一次蓄谋已久的暴动。既然
危险已经降临
就让它转为一种赐福。你瞧
——她红脸、她蹙眉、她眯眼
她的舌,她的牙,短暂的休整之后
继续高持虔敬和友爱
或许是生活太无力
每一个恰如其分的时刻
并没有惊心动魄。所以每年
她总要精心制作一坛泡椒凤爪
仿佛只有这番味蕾跌宕的经历
才能让她获取
清醒自立,以及,如释重负
不如等他骑马归来
一个人的晚餐
有时简朴有时繁复,正如
年岁渐长
孑然独处的时光总是纷至沓来
今晚摒弃传统的清炒
花椰菜成了盘中唯一的主角
免去蒜末姜片的俗套
佐以香辣肉酱,饰加三色甜椒
那盲目、那分明、那风情中的突兀
竟然不可名状
窗外无月,夜色难赋
她开始摸索到自己,愈来愈凉
舌尖颓然之际
忽接故人短信:“不如等他骑马归来”
暴雨突至
一切来得突然,但似乎又是应景的
刚刚还在激烈地讨论,那无处安放的青春
悬,而未决。自责在我
总是困顿于琐事和眼色。跌宕沉溺中
雨水瞬即缘窗而下,过往彼此
了无痕迹
凝重的午后。欲且抛却不解和沉闷
重返轻盈和跳跃
却无从寻觅那条秘径
也罢。从此,没有了安静的倾听
更不会再有喷薄的泄诉,以及
处处沦陷
这些天一直在下雨
严肃的、苦闷的、茫然的、颓废的
一个人独步细雨的街头
再宽阔、再通达的路
也是无穷尽的
如此车马喧嚣,如此市井纷杂
令人幽暗,令人沉重
不能躲避,无法抗拒
一切……缓慢,彷徨,无奈且伤感
无人能解。多年后
被雨水打湿的
将是中年某个午后的决绝和忏悔
汪治华,男,安徽人,现居广州。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诗作300余首,入选多种年度选本,出版诗集两本。
汪治华的诗
杂记
整个世界里,我想最后一个睡
整个世界上,我又想最早一个醒
我睡在路上,时刻准备醒来
那个月我病了,对“意义”这个词
理解得更为清晰。怜惜之心,让我宽广
整条河上,那不断咕嘟咕嘟
流水般的说话声,怎么都不见了
月光照过来,树影起了清风
月光照见河底的卵石,像辨别我的毛细血管
我想找出一块鱼形的石头,没有
而流水形状的石头,却全部都是
我发呆的时候多了,这就是幸福
是我自己的也是他们的
戴上手套,我就不可能
再去击打同样的某个人
把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这就是艺术
把可能的东西变成不可能,就是垄断
思维跟思想是两回事。在正确的方向上是同一回事
谈及方向,它令人不安
所有的方向都是方向,规定其中的一个
而忽略其它,不如把黑夜
直接缩短到一个玻璃瓶里
在故乡的大层面,它是值得热爱的
在细小的层面,它是令人灰心的
一下子出现那么多蓝天,是经济不行了还是很行了
只有天空的蓝,不让人产生错觉
感恩之心占据我的灵魂
让我成为纯粹之人。无所畏惧之人
我注视黑暗的池子已经很久
当我踏入池子的边缘,它突然亮了
2013-8-3
渡
沙子般被生下,石头般成长
黄土般被埋进土
总有一座坟,能登上山顶
还有竿子立在上面,比树高
北风吹来,茫茫一片
北风吹去,一片茫茫
松涛阵阵在前,流水若干在后
一群白马,驮着雪峰在奔跑
马如果停下,山就会停下
时间也会停下,让位于空
2013-7-26
菩提树下
累了才来这里
来到这里已经更累
站着站着就睡着
睡着了梦见自己还站着
菩提树时高时远
清风中还有曲线
看着它,就是一整个夜晚
菩提树的种子
落入我睡眠的心中
到达彼岸
2013-7-6
好时光是用来浪费的
我终其一生的忙碌,不过是
把每分每秒,都塞满垃圾
好天是用来下雨的
好朋友是用来怀念的
做过牛马、骆驼、狗和猪
我一直错以为自己也做过人
连剪指甲都没空的劳碌
是用来后悔的
好山水是给别人看的
好东西是用来想象的
好心情是因为今天大雪
好雪是下下来融化的
2013-6-6
沉默
整整一个星期,没说一句话
鹦鹉开口,我丧失说话的冲动
我忙于穿过风,风忙于穿过挡道的树木
我丧失说话的时间
万物之中,只有人会说鬼话
我丧失说话的理由
整整一个星期,只需要一个字
就能说完:操!
我不开口,不
我在找寻一个累并快乐着的人
找不着,让我更累
我突然唱起歌来
我被自己的声音吓着
而无意识唱出的字,经我细想
我还是给了自己,两个嘴巴
2013-7-27
我坐在这里
这大风大浪的海边
坐久了,就获得安静。安静有着
海底的推力。它低沉地咆哮
数米高的波峰与数米深的波谷
于水,都是一马平川
大地低矮。这些所见过的山头
踩上去,将如水一般回落
如水一般,回到平静的中心
2013-11-9
寂静
从世事归来,藏于一滴雨中
端坐,而后消失
雨,越下越大,越远
直抵大海、沙漠
烛光拉扯夜色,时远时近
轻轻哼首歌吧,让时光喘息
得以延长。静静想点事
让物象幡然复新
一个精神独立的人
一个辽阔的人
他的寂静,将大而一统
他的时光,每分每秒
都细密如林中之叶
2013-6-7
去山上看水
去水中看山
去有人的地方找鸟
有鸟的地方找鸟人
去向婴童学习
向老人致歉
去看一些严肃的面孔
想象它们嬉笑的样子
去美女的面前看花
去花中看雾
去一切沉睡的事物身边
躺下
2013-6-7
身体
把身体交换出去,在之上驻扎
火焰的身体,是它之上的热力
把自己交出去,成为他人
把影子也交出去
只在黑暗中前行,换取光
欲望在身体里,前冲后突
形成山丘峰峦与河流
它平息,一定要足够宽广
看自然界的一切,其实都是在看
自己的身体外景
身体养成在本体之外
是蓝天、花园、流淌的时光
和各种想象而复合成的综合体
往那一站,成为符号,在无字之书里
一个人接受了身体
他就接受了另一个自己
2013-8-25
桑地,河南省平顶山郏县人,1970年代生,早期写诗,中途辍笔,后再续前缘。少量文字散见于《星星》《诗刊》《诗林》《中国诗歌》《诗歌月刊》等报刊及年选。文字多抒写记忆中的故乡景色及县城生活感受,忧伤、神秘、苍凉、惆怅。认为写诗就是穿过词语的森林,无限靠近自己。
桑地的诗
如今,我不再祈求更多
如今,我不再祈求更多
一段庸常的时光,一本书就己足够
我不再穿过花草掩映的小路
独自出门
也不再去泛青的麦田闲逛
在这春天的风景中
我默诵着波兰大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章
“不再抱怨。你不可能逃得更远。”
“在一个句子里寻找我的家。”
时钟嘀嗒嘀嗒。生活啊!
我多想把我解救出的幸福也送给你一些
夜晚
春天的夜晚,又一次从梦中醒来
空气里有白梨花的香气
十七年前我也曾这样
说不清的冲动会涌起波涛
有时我走出屋外,独自感受花影的碰撞
而现在是多么的不同啊!
我问起自己究竟在岁月里追寻什么
头顶明月照临,我看见了
那个怀着梦想的新青年
最终不知不觉地弄丢了这一切
读史
许多年后,越王勾践的
剑,它没有消失。它平静、生动
它有自己的生命
我感到词语有时
和古老的青铜一样
比使用它的人更加强大
它的主人,征服者,或者大师
早已在时间中暗淡下去
而它却拨开腐朽
闪耀出,锐利的光
蓝河。雪
雪落下来。一朵牵着另一朵
落在池塘、斑茅草丛、沉寂的麦田
不远处的蓝河,转眼就有了臃肿的腰身
这会儿,我的心停顿在星火点点的
家乡。在幽暗中
雪,还是早年的样子,不紧不慢
一层又一层地挤压着这个世界
而我希望这时的雪,下得大些,再大些
它落在我的头上、肩膀
没有增加我的重量
反而使我感到如此轻逸,与辽阔
怀念雪
我曾怀念过许多的事物
它们都已逝去
这会儿,在一年的末尾
在一本书页中,在凛冽、清澈的词句间
我怀念一场雪
那是久远的日子,大雪封门
风在瓦项上徘徊
在夜晚,在简洁的梦里
在没有糊严实的窗前
有一盆火在跳跃
照着家园,和有关的一切
那时的雪依然年轻
那时的生活很小,而世界很大
那是另一片天地
另一种颜色。它闪闪发光
在我们内心,对抗着庸常的生活
草
我愿意慢下来。走进坡地
看草,在风中分开又合拢的样子
风过后发呆的样子
愿意看一棵平常的小草开成
一朵花。我喜欢它沉静的籽实
喜欢它簌簌的样子,不知把爱放在哪里
在我笨拙的诗句中,我曾不止一次
提到过草。提到它的暖、柔软
它的香。那些红色的,有时我也
把它们比作早年的爱情
包裹着某些秘密。但我从来没有拥有过
指尖上的月光
夜晚。变暗的天空解除了大地上
生灵们的不安和辛劳
一切都平静下来
心里那些波澜,也与这夜没什么两样
指尖上,月光轻轻移动
在寂静与寂静之间
指缝间流走的月光也是寂静的
很像青春的模样
我记得一个穿碎花裙的女孩
她指尖上也有蔚蓝的月光
一部分来自天空,一部分来自内心
却暗藏着猜不出的秘密
那是很多年前的日子,不缺乏光亮
但她指尖上的月光
是那么的少,那么的轻
似乎犹疑着
只是在很少的夜里,才出现
天渐渐黑了
在城南,在曾经熟悉的地方坐着,等待
看风,从多年以前起程
沿着我们走过的路
送来纯洁的眼神
身边修长的白杨林,擦着肩
在泥土之上唱歌
但只有我一个人倾听。秋天里
时光是澄澈的,果实在坠落
失去的孤单无人能懂
只有寂静在寂静中低垂着发梢
诉说谢幕的爱情
幽暗,却又清晰
更多的草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我认识这矮小的植物,它们有柔弱的身躯
和小小的籽粒,阳光下
垂着谦卑的头颅,生长在我童年
就熟悉的地方。狗尾巴草
长得挤挤挨挨,在乡下它叫野谷苗
米米蒿在路边最常见,它在五月
和麦子一起成熟,籽实可用来轧油
二花,一般生长在偏僻的坡地
夏初开花,稍后转黄,因为黄白间错
又称金银花,清香而苦
可入药,清明时节采集者众
它还有一个流传久远的名字叫忍冬
艾草,大部长在水边,它与屈原有关
马齿苋,酢浆草,地丁,野菊花,蒲公英
我数了数,大概也有三四十种吧
更多的草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但我常常在它们身边停下来
我深爱着它们,它们的色彩、芬芳
风起时的喧响,风过后
它们安静的样子,一尘不染的样子
就在刚才,我看见河滩地上
野菊花状的植物又开花了,灼灼灿灿
不远处的白杨林,叶子半青半黄
让我想起远逝的日子,以及那些日子里的笑声
忍不住怀念
天渐渐黑了,阴山像一只船
停靠在大河岸边。一片空旷泛出
陈年的往事和梦境
在一条长满荒草的路上
回荡。你的眼神,是不经意的花影
隐现于内心,但这注定不属于我
许多的事情永远也无法挽回
可忍不住还要再看一遍,忍不住怀念
任悲痛在坍塌的生活中展开双翼
抵达所有的过程与细节
它是不是就是多年前逃离我身体的那只船?
离开了清澈如水的好时光
因为怀念而搁浅
肖作华,男,1962年生。已在《诗刊》、《星星》等发表诗歌、散文900余首(篇)。作品多次获奖并被收入十多本文集,有诗被译到国外。出版过诗集《情旅》(合著)、《水做的苏州》。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诗歌分会主席。
肖作华的诗(5首)
大海尽头是故乡
女儿的问候,从遥远的
大洋对面传来
经过了多少风吹
浪打,多少颠颠簸簸
才能抵达此岸
月亮挂在秋天的中轴上
月饼在盘子里
面对一张餐桌如面对世界
吃,就使满月变得残缺
变成月牙儿,直至消失
思念使它从虚无中
圆满地重现
全球只有一枚月亮
但若是我们仰首,女儿,
青天就会给出两枚
不同国籍的月光
像热气飘渺的茉莉花茶烟
缭绕过咖啡的香气
今夜无眠,听远方的涛声
有一滴清泪,如泣如诉
大海的尽头,女儿
你是我挂在天上的小小故乡
父亲
灶膛里的火苗
一定映着父亲的白发
越来越深的皱纹
将他一生的疲惫收藏
在他弯腰拣起一粒麦子的时候
我能听到他急促的喘息
父亲老了
越来越弯的腰
如那根挑了一生的扁担
那扁担,曾一头挑着口粮
一头挑着他的孩子
缺油少盐的日子他挑着饥饿和愁怨
在岁月的肩膀上
磨生活粗粝的茧子
这个夜晚,月亮高悬
我想起曾经的土墙老屋里点起的油灯
想起消失在夜色中的炊烟
想起父亲的烟锅里烧了一生的沉默
时间之空荡衰老
如白驹过隙、无声无息
这个夜晚,我多想回到他身边
陪他饮几杯老酒
听他讲一讲今年的收成
尘封的过去和未来的打算
中秋。母亲的月饼
每年中秋
母亲用面粉、红糖、芝麻做月饼
那揭开锅盖后的热汽
几十年挥之不去
那时,月饼和孩子都围在她身边
沁人馨香是母亲的味道
爱的味道
今年,母亲已不能再做月饼
母亲老了,儿子也老了
惭愧的儿子却只能
把机器做的月饼捧到她面前
像捧着一盒盗版的亲情
倚在深秋
倚在深秋,看满街
落叶
携一生风尘
坠落
死亡
也是生之一种
倚在深秋
看从春天与夏天的巷口
走来的女孩
匆匆忙忙
赶路,来不及观赏
春花夏荷
便到了秋的桥头
对面是漫天大雪
倚在深秋
驮着沉重伴着苦难
干瘪的口袋
装着半个世纪的
尴尬
倚在深秋
一同上路的伙伴,风雨兼程
不知谁会在哪个站台
下车
不知还有几人
能把一生平安
设为终点
倚在深秋
与我最亲近的
玉米土豆
被装进粮仓和口袋
运上汽车与轮船
一如离开故乡的我
生存或消亡
倚在深秋
蹲在田边的父亲
一手端着长杆的烟袋
一手抚摸旱地里的麦苗
像抚摸他未长大的孩子
倚在深秋
一阵风来
将残荷吹动
将足迹吹成飘飞的落叶
多少陈年旧事
趁一阵风吹
又开始从陌生的码头启程
主持人语
章凯的诗有着纯正、饱满的抒情气息,又不乏宽广、沉静的理性,她仿佛秉有一种奇妙的力量,能够把欢悦与悲痛、艰难的清醒与酣然的梦、直面生命深渊的颤栗与谛视这颤栗的宁静,不着痕迹地嫁接到一起。她的独特气质或许正源于“我的呼吸区别开了我与其他众生”。“有些空壳,必得放下,/为自身的生长解除束缚”“我曾用一个空壳/成全生命对高处的渴望”,张巧慧的诗里涌溢着对生命的禅悟,用充满现代感的诗艺复活了古老的智慧。孙建娣的诗则有一种明显的躁动感,把生命换季时节的热爱与妥协、疼痛与克制、眷恋与决绝抒写得颇为动人。桑地的诗调子舒缓、沉静,这是一种适于回忆的调子,在克制的叙述中流露出生命的苦涩与微痛,但有时也表现出对命运断念后的轻盈与欣悦。
——黄玲君
诗歌月刊 2014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