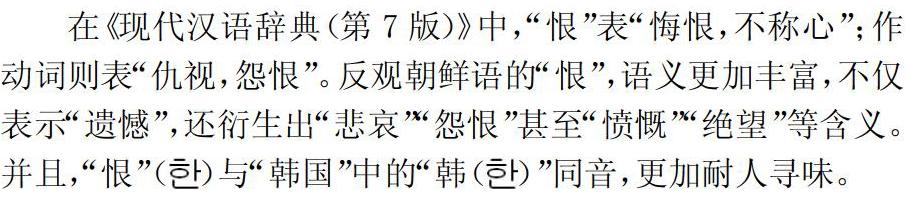
摘要:受儒家文化深远影响的韩国,骨子里却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情感:恨,突出表现为遗憾、隐忍、愤懑、绝望等种种复杂情感。作为韩国当代导演的代表,金基德执导过24部作品,在他的很多影片里,都有意无意地构建起一种封闭空间内人与环境博弈的旖旎景象,正是“恨”这一韩国人集体无意识心理的外化。
关键词:金基德;金氏风格“恨”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33-0115-02
一、引言
“我来自充满仇恨之灵的国度。”韩国妇女神学家郑贤镜的这句点评道出了朝鲜民族“恨”的精髓。“恨”在韩国电影中同样有所体现,也构成了其别具一格的电影叙事语言和审美方式。韩国导演金基德就以其特立独行的电影风格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卖春、性侵、自残、失语……其电影主題一直饱受争议,但剥开罪与禁忌的表象“,恨”的情结正是其电影迸发出鲜活生命力的土壤。
二、“恨”:韩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在《现代汉语辞典(第7版)》中,“恨”表“悔恨,不称心”;作动词则表“仇视,怨恨”。反观朝鲜语的“恨”,语义更加丰富,不仅表示“遗憾”,还衍生出“悲哀“”怨恨”甚至“愤慨”“绝望”等含义。并且,“恨”(?? )与“韩国”中的“韩(?? )”同音,更加耐人寻味。
朝鲜半岛三面环海恰如一叶扁舟,数百年来频遭侵略的历
史与国情,长期以来儒家文化的浸润,杂糅了各种复杂感情的“恨”,已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投射在韩国导演金基德身上,奠定了其浓烈的电影艺术风格:关注本我及个体的生存状态(电影主角多为边缘人物)、注重人生的底蕴和实质(电影中的悲剧人物和电影风格的悲剧色彩)以及对疼痛的极度敏感(女性角色、鱼钩等各种象征性符号)。
三“、恨”:金基德电影无法回避的主题
金基德曾在巴黎研习美术,这段异国求学的经历,使他遍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在其作品中烙下了深刻的个人印记。一方面,金基德作品聚焦韩国社会底层,尤其是对边缘人物的观照;另一方面,其早期游学欧洲的人生履历,赋予了他明显对抗好莱坞商业片路线的鲜明个人风格。
(一)边缘角色:自虐、受虐与施虐
欧洲求学期间亲身经历的穷苦、绝望、压抑,磨砺了金基德对生活的特殊嗅觉,深藏其内心的这种“恨”构成了其艺术作品混杂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独特风格——叙事上偏离逻辑认知、情节发展匪夷所思;影像空间支离破碎;镜头语言则突出表现为大量象征符号的不断涌现与堆砌——如梦呓一般扭曲失真的艺术语言给受众带来了强大的心理压迫感,这对早已习惯好莱坞经典叙事和宏大布景的受众造成了巨大的阅读障碍。
金基德信奉“哭与笑是最好的语言”,表现在其艺术作品中则是对白的极简主义,简短的对话之外是大段的沉默,连仅有的寥寥数语都显得十分干瘪甚至苍白,这正是“恨”的集体无意识下的产物。
比如,《漂流欲室》中的哑女,只身一人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言语交流的世界,一只破旧的小船构成了她全部的生活空间。冰冷的海水,烟雾缭绕的小岛,眉宇间不时透出一道凶光的哑女,再加上几乎患上“失语症”的男女主角,作品整体基调冰冷而压抑,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丝丝吊诡和淡淡的哀伤。为了挽救企图自杀的男主角,哑女将其吞下的鱼钩取出,用疯狂的性爱为其“疗伤”;影片结尾,为了留住男主角而将鱼钩放入下体的自虐举动,更加令人难以理解。
类似的还有那部充满金氏风格的《坏小子》,当爱情到来时,妓院头目亨吉想方设法使森华沦落为妓女,还要亲眼目睹其一次次被人蹂躏的惨状。正是这种负载着饱满情绪的类似写实的镜头不断堆积形成的强大能量,给受众造成了强烈的窒息感。
《雏妓》《漂流欲室》《坏小子》《撒玛利亚女孩》,边缘角色的戏剧冲突之下“,恨”成为挥之不去的情感元素,具体表现为爱要用恨来表达,有时恨又要通过爱来达到目的。就像金基德曾经说过的,“人生就是自虐、施虐和受虐”,在某种程度上精准地概括了他的电影风格。
(二)封闭空间:无处安放的内心隐疾
金基德的电影叙事习惯于向受众展示一个封闭空间内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片段,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孤立区域往往成为其电影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之一。比如《漂流欲室》中的孤岛,《坏小子》里的单向玻璃,各种符号隐喻下的封闭空间内,不安和压抑的气氛不断发酵,种种匪夷所思的行为暗流涌动,这或许与金基德儿时的经历有关(幼时常常为躲避父亲谩骂躲进农家厕所),实质是“恨”的外化。表现在影片中则是,金基德习惯于将叙事空间化为将人物紧紧裹挟的一个个“牢笼”。比如,在影片《海岸线》中,上等兵姜汉泽因为一次误杀,其内心的恨与压抑无法根除,始终未能突破内心的那道“海岸线”。
在另一部影片《坏小子》中,妓院黑暗闭塞的房间内,亨吉独自一人透过单向玻璃凝视森华肉体被践踏的全过程,全封闭的空间此时更像是一间绝佳的摄影暗房,同时单向镜面的窥视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镜头暴力,并不由分说地将受众卷入到这样的场景之中,真切地感受到亨吉深埋内心的压抑和躁动。这场暴力的“狂欢”是通过封闭空间内凝视的溢出完成的——“上帝视角”下,受众达成了与他者的欲望相通。导演通过这种方式,揭示了受众看到的一切皆是源于内心的幻觉,从而将“恨”的情绪具象化,这是金基德空间与镜头处理的内在逻辑。
(三)镜头语言:不能承受之美
在传统西方美学范畴中,真善美并举,假恶丑与之对立,前者是人们竞相追逐和赞扬的,后者往往遭到人们的贬斥和远离。现代之后,尤其是根据唯物辩证法,人们不再认为有所谓纯粹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了,而是认为,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出现吊诡。极而言之,理论上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真善美能构成对假恶丑的诱惑,在其激起的享乐冲动或主人能指中,真善美的追求会与假恶丑相遇,变成不能承受之美。
关于这些,可以参考金基德的《空房间》《弓》《春去春又来》等电影。其中,用镜头构建了世外桃源式的美景、美轮美奂的画面,可以说具备了一切美的要素,这种美令人无法拒绝,可一旦联系到作品中的情节和剧中角色,种种被精心营造出的美景突然就会显得诡异、孤寂甚至可怖。哲学家齐泽克有句名言“丑陋的享乐”,正是这种“丑陋的享乐”,颠覆了金基德作品中异于平常的美,从而唤起了另一种不能承受的美,或是残酷美。
金基德的电影画面美不胜收,像一帧帧推进的音乐电视镜头,但每一个镜头又莫不染上了一种凄凉和残酷,最美丽也最绝望的画面往往伴随着缥缈的大海或平静的湖面同时出现。电影
《漂流欲室》,开场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泓碧水,一缕炊烟从山间小屋中袅袅升起。同样的景象似乎又被原样拷贝到了另一部作品《春去春又来》中:同样是青翠悠远的群山環绕,同样是被包裹其中静谧平静的湖泊,湖心古意盎然的寺庙就是这部作品的整个
天地。精致的画面或许和金基德本人早年巴黎学画的经历有关,但这样的景色美则美矣,却总是透着一股令人心痛的凄美。事实上,在拍摄技巧方面,视觉上的美轮美奂只构成了第一层能指,即影视语言最表面最浅层次的直觉和观感;第二层能指就是反复涌现、穿插于叙事间歇的各种符号,比如在金基德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水”这一符号,为作品的内涵衍生出无限的可能性:《春去春又来》中湖面的形状和封闭性让人联想起充满羊水的子宫,其间丰茂的水草象征着主体纠缠不清的原欲本能,湖中漂浮的寺庙暗示着主体囚禁在欲望之笼中深刻的无力感……通往这座符号王国核心的,正是金基德内心之“恨”——对于原始本能的压抑和克制,在他的电影中,美仅仅是恐怖的开始。
四、结语
金基德的作品中往往充满了性与血腥、暴力与残酷,却通过轻盈唯美的镜头来表现,评论总是充斥着两极化的争议。多年来,金基德习惯了在人群中默默无闻地倾听和观察,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谈到,人生是极痛苦、充满矛盾对立的。他认为人自身拥有的原始的动力,是悲剧产生的原因,当人们将自身原始动力运用于艺术时,这种动力就得到了美化、提高。
面对生存困境、探讨个体实现,韩国导演金基德总是以一种轻描淡写的隐忍姿态,将“恨”文化诉诸其艺术作品。在他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尼采式的东方“酒神精神”,即典型的“恨”的悲剧情怀。
参考文献:
[1]王晓玲.韩国“恨”文化的传承与变化[J].当代韩国,2010.
[2]张崴淙.恨文化与现代韩国电影[D].保定:河北大学,2014.
[3]杜珊珊.电影符号学视域下金基德电影研究[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