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小时候老喜欢发呆,喜欢看天上云,看水中草,冬天为蚂蚁发愁,下雨担心麻雀被雨淋,天热了跑去菜园给黄瓜打伞,小姐姐叫我呆呆,呆呆待过的村庄,我固执地叫它槑村,还是我查了字典,好不容易碰到的字,手牵手背靠背呆呆的样子,憨态可掬。
我小时候老喜欢发呆,喜欢看天上云,看水中草,冬天为蚂蚁发愁,下雨担心麻雀被雨淋,天热了跑去菜园给黄瓜打伞,小姐姐叫我呆呆,呆呆待过的村庄,我固执地叫它槑村,还是我查了字典,好不容易碰到的字,手牵手背靠背呆呆的样子,憨态可掬。童年的村庄,总有一条小溪在梦里流过,溪水清浅可人,缓缓的,柔柔的,不远不近地跟着,有点不听话。水草里鲤鱼、鲶鱼啥的被草缠住,摇摇尾滑出去了,鲶鱼胡须长长的,总要纠缠一会儿。河里一半是沙,一半是泥,踩在脚下痒痒的,脚丫里的淤泥,扑哧扑哧蹿了出来,怪吓人。
太阳下山时,牛眼大小的鳖,大模大样地抬头出水,歪眼看一看天色。我躲在水牛背后,偷偷摸摸,不敢出声,悄悄伸出胖乎乎的小手。鳖倒不急,看我一眼,爬爬停停,我担心它咯吱咯吱咬手,我也不急。奶奶说鳖咬人不松口,要学叫驴叫才会松口,我看看水牛无辜的眼神,目光盈盈像小女孩的心事,湿漉漉的,甩甩尾巴自顾自地吃草。我学牛自顾自摆摆手,看它不紧不慢地划入水草深处。
村子四下都是河,西边有山,山下有西河,西河绕村转一个弯,水阔气了不少,改名南河。村北后河,也绕了弯,叫东河,在村东,水和水凑到一起,仿佛失散多年的姐妹相亲,那么缠绵,那么纠结,扭来扭去,歇一脚,一口气奔海而去。两条河就像老妈的双臂,紧紧搂住村子,摇一摇,睡了,再摇一摇,又醒了。
村子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四围都是山和岭,在村东留了小豁口,为了透口气似的。又有点像摇篮,远远望去,就像睡着了。眼惺忪地张着,可真会找地呀。
村子不大,七拐八拐都沾亲带故,常有背着筐拾粪的胡子老头,遇到大清早起来放鹅的小人儿,笑嘻嘻地叫爷爷,谁让人小辈分大呢。小人儿倒也坦然,若无其事地捉蚂蚱,串成串,山喜鹊蹲在肩上,叽叽喳喳,张开没长齐毛的翅膀,扑啦啦颤巍巍的,让人心疼。
地卷皮
溪水清浅,河里的小石头,被水推来推去。小河蟹躲到河畔的石头下,石头被我翻过来,蟹却害羞急匆匆跑了,还煞有介事地朝我比划下大钳。河边的岩石上,在清明后,会生出一种软软的暗绿色地卷皮,我们叫地耳,像长在石头上大地的耳朵,地耳支棱棱地竖起来,捕捉闪电、风声和鸟鸣。地耳比木耳小,滑滑的,娇羞,鲜嫩,太阳一出来,就会翘边,后来上了学才知道叫地衣。小阿姐常要我多采些给她,吃完地卷皮后,皮肤看上去有光泽,脸上细细的汗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奶奶说女孩都喜欢,可以出落得更美一些。
我喜欢藤条编的船形小花篮,采满了地卷皮,就把篮子放在溪水里,篮子顺流而下。地卷皮多长在潮湿的水边岩石上,采来不易,一小块一小块,小心翼翼地揭下来,扯得河水都变红了,红泥跌入水里,一缕一缕煞是好看。河畔柳条晃悠悠,常有翠鸟看着水面,我在水边筛洗,偶有小鱼咬我手指,我手指在水里一点,小鱼就围过来,簇动着小额头,都张着嘴看我。
地卷皮经溪水漂洗后,卷曲着,绿莹莹,仿佛涌动着春色和雨水,小阿姐挑出几片,贴在额上,看着铜脸盆的水镜子,一笑水就皱了,止水如春。地卷皮散在团箕里,一小朵一小朵像绿幽灵,偶有草木和泥土,越发衬托得出尘脱俗。这些野外捡回的生灵,每一片都有前世,容不得你不细细地挑。铜盆里盛着清水,好多细小地衣如莲花初见,清亮动人。
我能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灶里的火苗,还有桌子上的木碗,和我一起等。朝天椒的辣味,草鸡蛋的清香,地卷皮清炒后混搭在一起,想想就让人心软,口齿生津。如果用松木烤,味道也是极好的,那种焦味,透着松木的香气。我最喜欢的还是凉拌,啥调料都不放,把地卷皮切成细碎的块状,用清水、盐拌在一起,闻起来有淡淡的草木香气。我连舌头都麻了,骨头也酥了,小阿姐也不挑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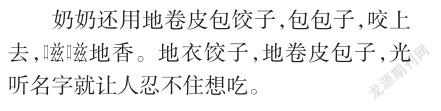 山水牛
山水牛夏天多雨,雷声像石碾子在天边轰隆隆碾过去,天空像玻璃一样,咔嚓嚓裂出缝,雨点乱窜,扑哧扑哧跌在黄土上,空气里有股土腥和草木味。我披上看山老爷爷送我的小蓑衣、小斗笠,提着大肚牙葫芦,穿着红肚兜,威风凛凛。隔壁小伢子穿了件剪开口的尿素袋子,把头和胳膊套进去就是披挂,小屁股一扭一扭,背后写着净重四十千克,含氮量保证40%,手里拿着竹编暖水壶套,下面垫上塑料纸,瞧他嘚瑟的。大人也不拦,笑嘻嘻地让他早去早回,大人都掐指算好的,就这么几天,能捉到山水牛。
山水牛不是牛,而是一种昆虫,属于天牛的一种,是天牛的“表弟”,与天牛血缘很近,却不像天牛那样危害林木,算不上害虫,因为力气大,叫它山水牛。山水牛有六条小腿,有一对长长的触角,一节一节的,长着一对大牙,咬人可疼了。
它浑身黑红闪亮,两对有一点弧度的翅膀,外面一对是坚硬的,里面一对是柔软的。公山水牛个儿大,浑身漆黑锃亮,两个大牙能截断木棒,长长的触角,神气得很。母山水牛的个儿小,性格温和,肚子大,有点黄褐色。雨小时,会飞。
山水牛多活动在夏至前后,下雨时从土中钻出,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完成恋爱产卵老死的一生。山水牛的幼虫要一直活在地下,靠啮食黄草、白茅等多年生长的草根为生。
我和小伢子像巡山的猴子,眼睛直勾勾看着田埂的草丛,原以为我们赶了个大早,山水牛满地乱爬呢,难道雨不够大,还没有爬出地面?
 突然,小伢子猛往前蹿,我一看,一只山水牛急从草丛里爬出来,振翅欲飞。小伢子机灵,伸手拍了下来,正好跌落在我脚下,我伸手捏住山水牛的触角,小伢子说是他发现的,应该归他,我说是我捉到的,应該归我,我不情愿地把山水牛给了小伢子。
突然,小伢子猛往前蹿,我一看,一只山水牛急从草丛里爬出来,振翅欲飞。小伢子机灵,伸手拍了下来,正好跌落在我脚下,我伸手捏住山水牛的触角,小伢子说是他发现的,应该归他,我说是我捉到的,应該归我,我不情愿地把山水牛给了小伢子。哇,前面草丛里有两只公山水牛在打架,纠缠在一起,我弯腰用手一扣,一下子捉到两只,扔到奶奶给我编的藤条笼子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
小伢子一蹦一蹦往上跳,头顶飞过一只山水牛,油亮亮的翅膀,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在空中飞来飞去,小伢子跟着山水牛跑,一边追一边拍着巴掌唱山歌。小伢子往上一跳,一不小心滑倒,沾了一屁股泥,手里还攥住那只山水牛。
捉山水牛可是个技术活,要眼疾手快,拇指和食指小钳子样,捏住山水牛的腰,“啪”扔葫芦里。小伢子胆比我大,伸手捻住触角,一拎一个准,两眼放光,我估摸着他回家要斗山水牛,个儿小的不要。雨大路滑,山坡上有蛇盘在酸枣枝上,幽幽吐着舌尖,迎风晃动,懒得理人。
捉回家哪舍得吃,挑个儿大的,嘴里给它衔个草棒,免得打起来。然后捉对厮杀,放在铜盆里,用草挑逗,我和小伢子玩得兴起。个儿大的就让他拖火柴盒做的牛车,上面放弹珠啥的,拉起来雄赳赳气昂昂,有股倔劲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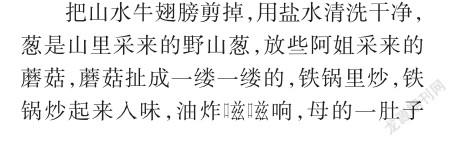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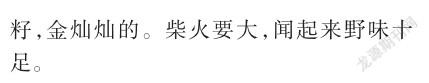 菜园子
菜园子步行约一刻钟,就到我家菜园子,隔河相望铺开,一茬一茬挤挤挨挨,畦与畦间可挨脚,多是卧牛大小,几步长短。也有靠坡开荒种些南瓜、向日葵。
河没有名字,小名也没有,流到哪儿就叫啥,西河、后河、东河、南河的,随你。河水都流了多少年了,比村子老,比爷爷的白胡子老,通透豁达,不通,绕过去即可,遇石头,水凿石穿,弯弯绕绕也通海。
一家一户地头田间说笑,坡下就是后河,棒槌捶打着青石上的衣服,有小伢子在旁戏水,挖水坑引水养鱼,养蝌蚪,额头上亮晶晶的汗珠滴答有声。
我欢喜去菜地捉虫子,喂养的灰喜鹊跳步雀跃,飞到我头上叽叽喳喳。小狗黄老邪嫉妒得不行,作势欲扑,灰喜鹊被我宠得不得了,我叫它灰姑娘,或灰灰,灰喜鹊依人,理都不理狗。黄老邪猛扑,急停,灰喜鹊急飞,悬在空中。黄老邪眼神欲滴偎我腿边,伸长舌头用幽怨的眼神看我扎弹弓。
鸭子的小碎步,显得局促小气,连声音都嘶哑,撕裂了布一样。哪有我家鹅大模大样,踱着步,腆着肚子,歪头看天,像披褂撑腰大肚子的生产队长。
有一次我吃馒头被噎住了,鹅看我手中黄澄澄的高粱馒头,想从人手夺食,忽闪着翅膀,凌波微步地朝我扑来,我呆住了,把馒头举到头顶,鹅抻长脖子,从我嘴里小口小口咬馒头,我吓得不敢动,眼睁睁看鹅耍流氓吻我。
那时我还小,还不懂得拒绝,刚好比鹅高。
我蹲在草垛边看它脸红脸白地下蛋,刚生出来的蛋天青色,烫着热气。
鹅淘气,下蛋没窝,随心所欲,我大清早要到河边、篱笆旁、丝瓜架下、石磨后和花圃中找蛋,鹅一看到我就知道没好事,故意磨磨蹭蹭,憋了半天,扑哧一地鹅屎,逗我玩。等我气急败坏撂挑子不找了,它却躲在一边偷摸下蛋。
捉迷藏哪,鹅,小瞧人?我躲在米桶里,扣上斗笠,米桶边撒上碎米,铺上稻草,舀半瓢清水,不一会儿,鹅大摇大摆地来了,左看右看,见没人,坐稻草上了。
我在米桶里透过斗笠看它挪窝,伸手偷蛋。咦——蛋呢,蛋哪儿去了?鹅疑惑地看看天看看地,甩甩鹅头自顾自走了。
钓蟹
从前呀,水瓢舀鱼,翻开石头就是石蟹,虾都没人稀罕,水缸里谁家都有鱼呀鳖呀虾呀蟹呀镇宅,过几天母蟹就生了几只小蟹,溜得贼快,小鱼呢,被蟹吃了,我还好奇它咋吃呢,拿油灯看了半夜,睡着了。
也有胆大的蟹,趁夜色浮水逃走,秫秸做的水缸盖子一顶就开,能逃到哪里去!见洞就钻,成了老鼠的夜宵,还送上门哩。
河上游石滩上,我随手翻石头,要找那种石头稍微松动,湿湿的,一翻,哇,纽扣大的小蟹急匆匆走,赶不急就入水了,要快,从两侧钳住,小蟹见有手来,摆开架势,亮钳,边撤边挥舞恐吓,初生螃蟹不怵人。
逃到水里就是蟹的天下了,蟹随意到水草里一躲,沙子里一藏,人那么傻哪里找得到。实在没辙,有洞先钻进去躲。正郁闷哪,小蟹刷地蹿出来了,后面跟出来一只拇指大小的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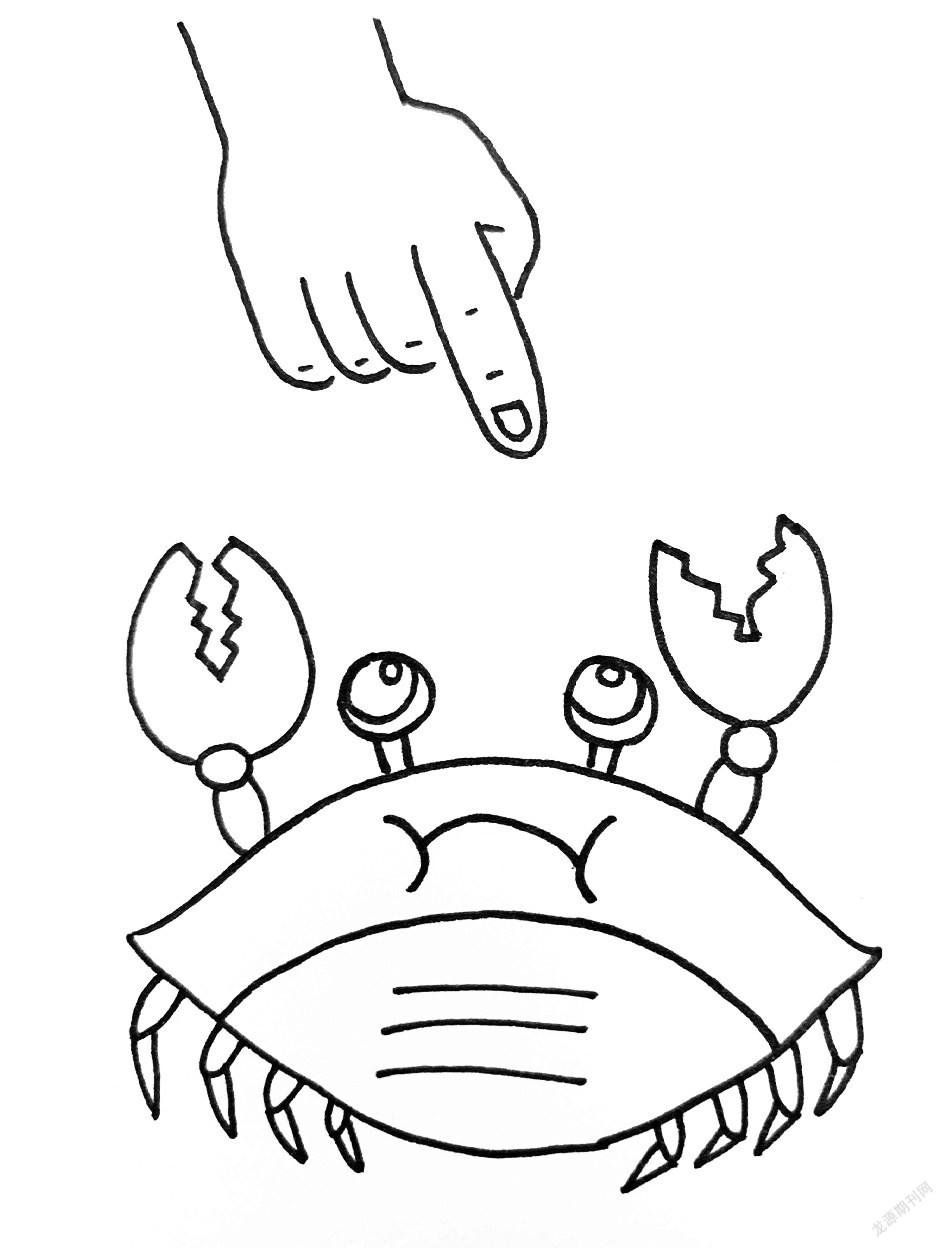 嘘,别吱声,我单膝跪地,脸贴着草,鼻子上蹭满了泥,裤脚都湿了,手伸进洞里,能听到水哗啦哗啦响,奶奶说跪地掏蟹掏不出来,男孩膝下有黄金,蟹受不起不肯出来。
嘘,别吱声,我单膝跪地,脸贴着草,鼻子上蹭满了泥,裤脚都湿了,手伸进洞里,能听到水哗啦哗啦响,奶奶说跪地掏蟹掏不出来,男孩膝下有黄金,蟹受不起不肯出来。使个大劲儿掏出一块鹅卵石,不知蟹怎么搬进去的。再掏,呀,摸到蟹腿了。啊,呀——手指被钳住了。
眼泪打圈圈,硬是没落,用手指把蟹拖出来,蟹钳人不松口。
刚把蟹拖到洞口,咦,它松口了,不急不忙退回洞里。
我那个气啊,食指都钳出血,血渍粘牙印。
再伸手,洞里的蟹也不客气,狠狠地钳,我忍住痛,慢慢抽出手指,一个大螯钳在手指上,随风而动,断了。我拿起大螯直往嘴里塞,嘎吱嘎吱吃,看谁牙齿硬。
哇,突然手一抖,牵出一条黄鳝,不,是水蛇,我一甩,水蛇摔我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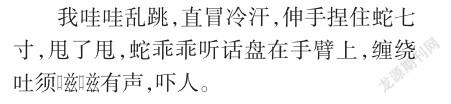 我脸都白了,后来撂在酸枣树上,蛇缠绕而下,灰溜溜走了,草丛被压出一条浅痕。
我脸都白了,后来撂在酸枣树上,蛇缠绕而下,灰溜溜走了,草丛被压出一条浅痕。捉鱼
前村有个拿鱼高手,个儿矮,话少,半口吃,嘴上毛茸茸,戴个网织帽,稀松平常一句话,对他来说好痛苦,憋得青筋暴露,额头冒汗。
手一指,“鱼鱼鱼——叉叉叉——”
“鱼叉子。”
“嗯嗯,走走——走——”
“跟上。”
小哥憋红了脸,在空气中咂咂嘴,晃晃公鸡头,左耳银耳环闪了闪,对我的配合忒满意。
小哥雄赳赳手持魚叉,身披渔网,在黄昏的余晖中慢慢走向村外,街拐角纳鞋底的奶奶推了推老花镜,顶针在发髻上磨了磨,倒吸一口气,“咦,呀——这是要出海啊,这披挂,捉龙王哪。”
“嗯哪,揪揪——揪——”
“揪泥鳅回来给您老熬汤喝。”
我提鱼桶,在后帮腔。奶奶喜笑颜开,“你唱,唱出来就好了。”
这也太离奇,小哥唱山歌好,说话像戏文,咿咿呀呀就差我敲桶伴奏了。
小哥水性好,据说能潜水三米捉鱼,会水下换气。辈分应该比我大一辈,大人让我叫小叔,和我年龄相仿比我牛的我都叫哥,叫起来近一层,谁管辈分。
我还在用瓶子蒙上透明塑料纸捉鱼时,人家都沿河结网了,等我学会挖蚯蚓钓鱼,他用青豆虫钓鳖了。服帖的,奶奶说会咬人的狗不叫,聋哑人都心灵手巧。
我会用网兜捉鱼,在河水浅、窄的地方,用网兜拦住下游,然后让黄狗一起在水里赶鱼,鱼往下跑,就落网兜里了,都是些毛毛鱼,连黄狗都看不上。
我呢,就沿着河边水草多的地方,掀水草,越是水浅的地方,越容易捉到食草的大鱼。不能猛掀,猛掀水草,最多捉些小鱼小虾黄鳝泥鳅啥的,大鱼一下子就窜到深水里去了。我看这一块水草较多,慢慢地掀起水草,一层一层地翻卷着掀,突然,噼里啪啦鱼尾击起水,喷了我一脸,哈,大鱼被水草困住了,好大一条草鱼,小哥赶紧过来帮忙,黄狗也兴奋地叫。
小哥不屑看我捉鱼,他用鱼叉刺鱼。看他漫不经心地站在河边,一动不动,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水面,四周一点风也没有,水面平静得像镜子。突然镜子水面晃了晃,小哥手中鱼叉旋风般刺出,刺入水中,我拖起鱼叉时,已经有一条三四斤重的大鱼扎在上边活蹦乱跳,比我刚才捉到的那条草鱼大多了,还是有点青黄的鲤鱼,小哥吹起了鱼哨,笑眯眯看我手忙脚乱地拖鱼。
小哥斜眼看了看天色,感觉要下雨,看来今天不能拉网捞鱼了,每次都是我和黄狗在河水两边拉网,狗用嘴叼着网拖着走,小哥在一旁看,他知道哪里鱼多,知道往哪里撒网。
“鱼鱼鱼——”
小哥吱吱呀呀朝我一指,我和小狗黄老邪扑向草丛渔网,小鲫鱼使劲跳,被狗爪子摁住,嘴闻闻,鱼又装死不动了。我一抓,鱼滑溜溜,我拎起鱼腮帮子,撇进鱼桶。鱼桶里面要放几条泥鳅,要不鱼撑不到家就死了,泥鳅在鱼群里扭来扭去,鱼动起来,就不容易死。
我看小哥在河里踩水收网,一个猛子扎到河里,黄狗也跟我跳入水,一头扎得深,裹到渔网里,挣扎了半天,身上还挂着鱼。
大鱼大人喝酒,小鱼小人尝鲜,鱼头给狗。
我们踩着夕阳回家,把泥鳅给奶奶熬鱼汤,一边烧柴火,一边看泥鳅在豆腐里钻来钻去,我那时人小,不忍心伤害比我小的生灵,又忍不住想吃,就半閉着眼睛给鱼祈祷,小鱼儿,对不住了,再忍耐一会儿就好了。
我沿着童年的小溪逆流而上,从冬到秋,至夏回春,从唐诗的鬓角出发,到咿呀咿呀的学堂前报到,慢慢退回去,我亦步亦趋地牵着小哥哥的衣角,陪我去呆呆待过的槑村,那里有我年少的囧事。有一条河流,叫童年。
我的童年,在河上游,在山里,在云上。小姐姐唱起清亮亮的山歌,带我回家,和大白鹅一起呆呆地歪头看云,看雁群在天空下教我识字,看萤火虫越来越高变成星星。
选自《十月少年文学》2019年第4期
韩墨,儿童文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