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旅客朋友您好,飞机将于23点10分抵达喀什机场……”广播里清脆的女声响彻机舱,郑澜依揉了揉惺忪的眼睛,伸手摸了摸确定安全带依旧扣得紧实后,开始安心等待不久后的飞机降落。
在郑州飞往喀什的航班上,郑澜依已经待了6个多小时,而在此之前,她还经历了一次争分夺秒的转机。她生活的北方小城与喀什相隔近万里,两地之间没有直达的航班,她从一早吃过午饭后便开始急匆匆赶往机场,经过近一天的奔波才终于抵达。
郑澜依一直对西北有着深深的向往。父亲是在西北读的大学,从孩提时代起,父亲便经常向她讲述那方遥远土地上的人和事。待她稍稍懂事一些上了学,在课本里,在地图上,那片神奇广袤的土地总是牵动着她的心。
去西北支教是郑澜依大一刚入学时就决定的事,为此,她从很早就开始关注学校的支教政策,原本打算在大二下学期就报名参加支教,但父亲忽然重病让她不得不推迟了这一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救治,父亲终因病情过重在那个秋天离开了她,弥留之际他拉着女儿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澜依,是爸爸不好,我这场病改变了你的计划。如果你有梦想,一定要去实现,爸爸相信你。”
父亲这番话一直盘旋在她心头。因此,大三下学期学校招募支教大学生志愿者时,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得知自己顺利通过选拔成功入选大学生支教团后,郑澜依有种多年梦想成真的感觉。
收拾行李时,她力求精简,却将父亲生前最珍视的一支钢笔带在了身边,父亲当年就是用这支笔写了入党申请书,给故乡年迈的父母写下一封封家书,给郑澜依的母亲写了一纸纸情书。他生命中很多重要时刻都与之相关,把它带在身边就如远走的父亲依旧陪伴左右。
2
抵达喀什机场时已是夜里11点多,由于存在时差,当地天刚刚擦黑,从机场出来后,她便开始张望搜寻来接站的人——从机场到她要去的疏勒县城还有近半个小时的车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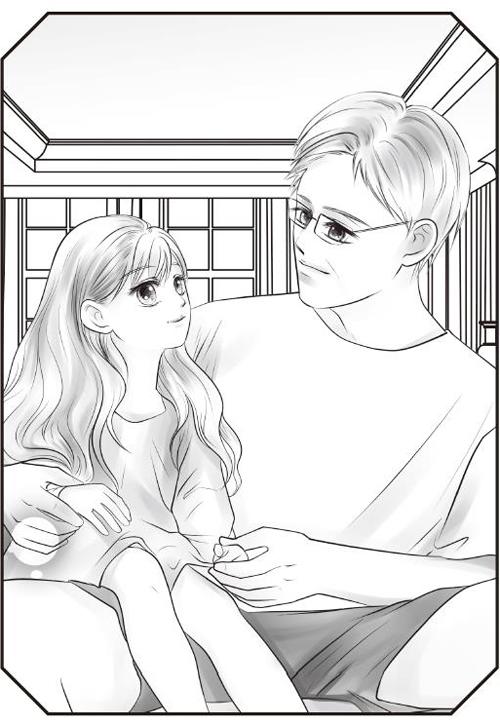
手机铃声忽然响起,显示是陌生号拨打来的新来电。“喂,请问是郑澜依同学吗?我是来接站的周远拓。我看到你了,你往你的左手边方向走,我穿蓝色冲锋衣,在朝你招手。”
郑澜依循声望去,看到了不远处正朝她使劲招手的周远拓,他高瘦挺拔,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从喀什机场到疏勒县城的车上,司机一路开得飞快,郑澜依在座位上被摇晃得东倒西歪,周远拓便轻轻扶住她。通过交谈郑澜依得知,周远拓毕业时被保送研究生,但他自愿提出推迟一年入学的申请,来到这里支教。比郑澜依早来半年的他俨然已如疏勒的“活地图”一般,一路上滔滔不绝地向她讲述着这里的风土人情。
郑澜依被分在和周远拓同一所学校支教,郑澜依教初一英语,周远拓教初三数学。当地的维吾尔族孩子们很热情,见第一面时便热情地抱住她喊“小郑老师好”,他们多数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来之前她担心的语言不通的问题也一扫而空。
受教育水平所限,这里孩子们的学习功底偏弱,有时看似很简单的知识点,要重复讲很多遍他们才能明白。可只要看到讲台下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站上讲台的他们便浑身鼓足了干劲。
由于当地天气干燥,自小在沿海地区长大的郑澜依没多久脸上、手上、胳膊上开始脱皮,鼻子里经常有血块。周远拓见状便给她买了一只粉色的保温杯,叮嘱她平时一定要多喝水。
有一次在课堂上,郑澜依给同学们布置了一篇以“我的梦想”为话题的英语作文,她鼓励大家写完后主动念给同学们听。一个瘦弱且终日沉默的男孩率先举起了手,他用有些磕巴的英语一字一句地说,他的梦想是好好学习,以后有机会能去山东上大学,因为那是小郑老师生活的地方,等学好本领以后再回来更好地建设家乡。
可能因为鲜少在众人面前讲话,男孩的脸颊涨得通红,眸子里也有晶亮的液体在闪动。就是眼前这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平凡男孩的这番朴素的话语,让郑澜依猝不及防地红了眼眶,她带头给他鼓掌,潮水一般的掌声在教室里不断回荡。
3
清明节小长假,有一同支教的老师提议去市区的喀什古城逛逛,郑澜依和周远拓也报名前往。
走进喀什古城,馕和烤包子的香气在街面流淌,街道两旁铁匠“叮叮当当”的重锤声成为一曲曲别致的背景音乐。望着琳琅满目的花盆、帽子、围巾、乐器、铜器等商品,郑澜依兴奋地四处来回穿梭。
后来她在一顶男士灰色裘皮帽子前停下了脚步,若有所思地摩挲着帽子上柔顺的皮毛。这顶帽子她再熟悉不过,她在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上见过这种帽子,当年父亲在西北上学时冬天便用这种帽子御寒,多年前有次搬家时弄丢了那顶帽子,父亲还心疼惋惜了许久。
是的,她想父亲了。相比母亲来说,她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向来更为亲密。人生的前20年里,他尽所能地给予她太多的宠爱与庇护,以至于在父亲走后的半年多里,她需要时常借助周遭人和物件的提醒才能恍然接受父親已经远走的事实。
郑澜依买下了那顶帽子,就像是完成了某种郑重的仪式。
回程的路上,周远拓见郑澜依始终紧紧抱着那顶帽子,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可以成为那个听你倾诉的人。”他轻轻地说。
后来郑澜依将父亲的事情同他讲了。自父亲走后,她心里好似始终紧绷着一根弦,别人无法靠近,她亦不能主动打开心扉,那种感觉好像她一旦同别人倾诉了,父亲离世便成了无法挽回的既定事实,她再也不能轻松地假装一切从未发生过。
可周远拓却成了那个例外的人,让她心甘情愿地打开自己的过去,等待他的检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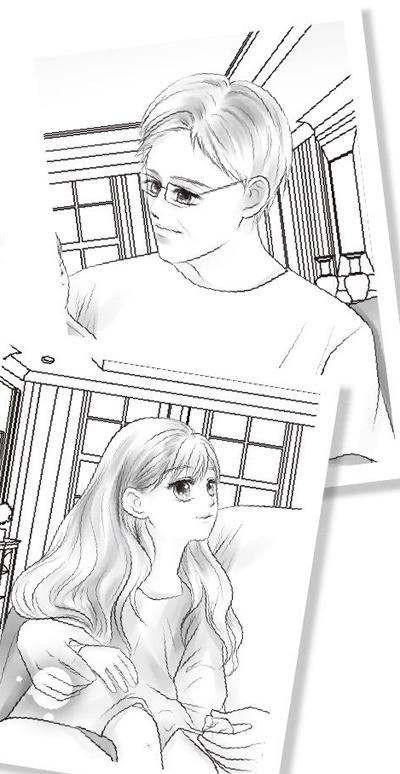
“我一直想来西北支教是因为我的父亲,由于从小他对我的灌输,让我对这片土地深深着迷,能来这里走走他年轻时走过的路,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月色如水,郑澜依缓缓说出这番话,夜色中即使近在咫尺的周远拓也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
4
郑澜依很快与班上的孩子们打成一片,他们除了会在课堂上与她积极互动外,课下也经常会有孩子跑来向她倾诉心声,她感受到一种实实在在、沉甸甸的信任感。
学校所在的这一片是老城区,路两旁经常有那种很粗的树,遮天蔽日的枝干为这座小城增添许多古朴与厚重。走在这样的街头,郑澜依时常生出她很久以前就属于这里、与这里浑然一体的错觉来。
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至于更深层次的奥秘,郑澜依说不清,只是连脚下的泥土也仿佛成为某种瓷实的佐證。于是,她便只能暗暗告诫自己,是因为她的父亲,初来乍到的她才与这片陌生的土地有了血脉相连的默契。
没有人知道,其实从一到这里开始,她便拍了很多照片,发送给那个再也不会收到任何回应的聊天窗口,这让她有莫名心安的感觉。
她想为这里的孩子们多做一些事情。她注意到班上多数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课外书后,郑澜依跟周远拓商量,在争取到内地教育部门的支持后,发起了一个募捐爱心图书的活动。很快一本本满载爱心和祝福的图书被运往这里,孩子们在五花八门的图书里,与梦想撞个满怀。
100多个日夜倏忽而过,来之前郑澜依曾以为这会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可日子竟好像是打了个盹儿的功夫就悄然溜走了。

眼看距离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郑澜依心底生出深深的不舍,她放心不下这群可爱的孩子,当然,这种不舍也因为周远拓。他们将于这学期结束后一起离开,新学期开始后,周远拓将在北京继续求学深造,而郑澜依则将在那座漂亮的海滨城市度过忙碌慌乱的大四时光。
他们之间还没来得及有故事发生,以后,也许永远不会有故事发生了。想到这里,郑澜依心底划过一丝不舍和怅然。
6月正是当地的杏子接二连三成熟的时候,往往是夜里一场急雨下来,第二天一早天光大亮的时候,钻到杏树下便会看到葱郁的叶子里藏着一颗颗被雨水冲刷得干净的杏子,黄澄澄的,咬一口透心甜。
郑澜依踮起脚准备去摘高处的杏子时,被一双手抢先摘走。她转身发现是周远拓,朝她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大白牙。他把杏子放到她手心里,笑笑说:“这是新疆特有的色买提杏,格外甜,但是当地人说要吃一颗杏子配一颗杏核,要不然容易拉肚子。”
郑澜依笑笑并不理会,一口一个吃得狼吞虎咽。
“澜依,离开这里你会时常想念吗?”周远拓猝不及防的提问,令她心跳仿佛漏了一拍,她只能极力假装镇定地回答:“当然会,这里的一切我都会时常想念。”
“我也是,在这里的一年我时时有被需要的感觉。最近这一阵子我时常会想,等将来研究生毕业后直接申请来这里工作。当然这不是一个太容易的决定,我得说服我的父母,毕竟我是他们唯一的儿子。”风吹过树叶有“飒飒”的声响,周远拓这番话像是一种发问,也像是响当当的回答。
5
离别的日子很快到来。很多孩子哭着送别郑澜依和周远拓,大家争相与他们合影留念,自发地跳起当地的舞蹈为他们送别。
“老师,谢谢你!”孩子们齐刷刷鞠躬致敬。郑澜依抹了一把眼角的泪,硬是逼着自己埋头向前走,不敢回头。
郑澜依拉着手中的行李箱,一切都像几个月前刚来时那样,一切又大不一样。
忽然,她踮起脚伏在周远拓耳边悄声说:“等大学毕业后,我想重新回到这里支教,如果可能的话,陪我班上的孩子们参加完中考,他们说,有我在,会比较安心。”
两人继续并肩往前走。他们都没再说话,远离了送别的人群,周围变得十分安静,周远拓从容地握起了郑澜依的手,而她亦没有挣脱。
几天前,郑澜依给班里每个孩子都写了一封告别的信,在信里她叮嘱他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有机会她还会回来看他们。最后,她也给周远拓写了一封,内容很简短:“周老师,一年后,小郑老师会重新回到这里,等你。我想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还有你。”
她用的是父亲留下的那支钢笔,一字一句,都无比虔诚认真。她知道,周远拓一定读懂了她信中的深意。

离开那日她穿一条大红色的裙子,头发随意挽在脖颈间,侧脸朝他温柔一笑,整个世界的美景仿佛尽收眼底。他把她的手握得更紧。
从此,眼前的人他们是想要一生一世的,而来偏远地区支教这件事,也将成为他们一生的职业和选择。
我想和你一起翻山越岭。
他们就这样手牵着手继续一路沉默地往前走着,不发一言,却分外明晰彼此的心意。
至于剩下的,都交给时间来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