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德里的4点。你消失的第365天。
我现在还算过得去——生活得不算好,但也没有很糟。我在你不见了的第二个月独自一人来了西班牙,现在算是半工半读,挣生活费。
我在la Puerta Del Sol 附近租了套小公寓,向阳,只能挤下一张单人床、一个房东留下的木书桌和堆了满地的书。每天凌晨都能看见广场上金色的通明灯光,隐约听见嘈杂的人声。这个时候我通常拉起被子紧紧捂住头,乞求般地追逐那点微弱的睡意。到底还是没能适应西班牙人的作息时间,总觉得昼夜颠倒,头昏脑胀。早上9点才睡眼惺忪地从被窝爬出来,用手机放el gran hotel,大抵是三刷了。Dona Teresa一如既往的精明强势,大饭店一如既往的富丽堂皇,开头音乐一如既往的符合古典悬疑的质感。
一切一如既往。

马德里真的很好。地处欧洲南部,气候温和,便捷、热情、现代却也不失古典、精致与优雅,虽然我偶尔会觉得恍惚和悲凉。它像极了我们的城市,有阳光,有艺术,有荒唐与迷茫。但是这里没有你,也没有我。还记得我们曾并肩坐在沙发上,我给你念“在最高的篝火上我的孤独燃烧蔓延,溺水者一般挥动臂膀”吗?我们都迷恋过聂鲁达。
靠近我住的地方,有一家中餐馆,我在那儿打工。或许是因为那里的鱼香肉丝里真的有鱼,或是因为老板虽然有着纯正的四川血统却连一句中文都讲不利索,这家饭馆生意实在不怎么样。但也还是会有老外路过时,笑着惊讶一句“jeh,la comida china!”(哇!中国菜!)来这家饭馆的大多是来太阳门广场周边参观的游客,还有不少国内旅行团,用餐高峰在晚间9点。天空像是漆黑一片的幕布上面撒了星星点点的颜料,好像出自孩子的手,天真和纯粹。孩子的无邪和可爱是被所有人喜爱的理由。美可以掩盖所有的缺陷,光彩夺目下,没有什么是不可忍受的,当我站在窗边择菜,望着遥远不可见的天际时,这样想着。
总有一种不可抗的力量,或许是永远倒不过来的作息时间规律,或许是周围人放鞭炮一样的语速,或许是夜幕降临时开始热闹起来的广场,或许是文学课上仿佛在听天书的茫然。它们用一种严肃而不留退路的语气告诉了我,我不属于这里。
我不属于这里。我曾一字一句地这样告诉你。你戴着耳机,里面嘈杂的显然没有放开你。我有些生气地拔掉了你的一只耳机,又重复了一遍。
“对,你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如来我们火星。”你又重新塞上耳机。
你说的没错,我确实该去火星。毕竟我是个怪胎。我们是怪胎。
从小到大,我是最不合群的那一个,我不愿主动跟其他人多说一句话,也没有人愿意跟我多说一句。书包被埋进雨后的沙坑,第二天要交的作业本被撕掉几页,被当作空气故意忽略,不爽了就被拿来当出气筒……老师们都不管,即便我语文分数没出过前三。我从不反抗,因为早在家里的那个醉鬼老爸那儿知道了反抗是毫无意义的。矮小、丑陋不起眼又孤僻,似乎我的境遇也理所当然。

颃之就不一样,她不屑跟她身边的人——除了我,一起玩。她总是用阿蒂尔·兰波的嘲讽之语“每一个才能平庸却还满心自得的作家都应该去死”,来描述喜欢围在她身边的苍蝇。我相信她其实也很想像兰波那样跳上桌子向苍蝇们撒尿。她天生丽质,有羊脂玉般细腻白皙的皮肤和远山般的眉,漾着波光的眼,这样的人,总是能让人忍不住多给予一份宠爱。她厌恶学校,每天上课无视老师在下面看书,所以成绩自然不怎么像样。但是她喜欢看的言情,不是郭敬明也不是匪我思存,而是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她最早对骑士的认识是来自大仲马而不是偶像爱情狗血剧。14岁时她沉迷的是基歇尔、艾略特、保罗·策兰和卢克莱修——就在她的同龄人还抱着湖南卫视不放的时候。
我和颃之的不一样就是一样。
因为她是我亲姐姐。
在我眼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子。即使会在语文课上让老师下不来台,即使会偶尔情绪失控开始摔东西,即使放学后会把所有的作业扔给我自己出去溜达。但是她笑起来眼里会闪烁流萤,跳起来的时候,会露出粉红色的草莓蛋糕般的脚踝。心情好的時候,就会给人念《安格斯漫游歌》,也会为了简嫃笔下的那段书信承载着的爱情故事的终结难过很久很久,还会在床上滚来滚去耍赖不还我的小说或是不愿去做家务。颃之还是我见到过的穿白色棉麻连衣裙最好看的女孩子。
我们的家就在机场旁边。我们喜欢在夜色沉沉、四下静谧时,在房间里隔着一层似有似无的薄玻璃,遥望在漆黑帘幕间倏忽向天际轰鸣而去的红色闪光点,用视线一点一点追随它,然后在心里默念圣埃克苏佩里的句子。我们常坐在那个白天苹果绿色到晚上被灯光染成深紫色的沙发上,沉默着思考,又或只是单纯地沉默,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用想。
那个时候,我是快乐的,你也是。我们快乐地弹着那把捡来的断了一根弦的吉他,快乐地哼唱一个叫陈粒的歌手Galen Crew的民谣,快乐地踩着梧桐树叶倒影间隙的小圆斑——它们像小姑娘脸上可爱俏皮的小雀斑,快乐地用滑稽的语调来朗诵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对白,快乐地讨论着《浮华饭店》里养眼的男主。少年不识愁知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我们提到未来时,你用向往的语气跟我说,总有一天要去看一看西班牙,看一看那里的古典和激情。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或多或少,对“远方”这个带着伊甸园苹果香气的词都会暗藏几分隐晦的迷恋和渴望。可有些人却知道,他们迷恋的也许并不是远方,而是他们幻想中的远方。真实的现实大抵是会让人失望的,远方永远在远方。风流子弟总少年。
2017年8月25日。
我会永远记得那一天的,我的颃之。
她用哄幼童入眠的温柔得发腻的语气告诉我,她要离开这个家了——我那个醉鬼父亲终于出车祸死了,她看起来快乐得又回到了她生命的黄金时期。我面无表情地问:“那我和颃之怎么办?”
沉默,是泛着冷光的匕首。
“颉之,明天我带你去见一下心理医生,好不好?”
“什么?为什么?”
她用一种打量怪胎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不是她生下来的那个乖孩子。
“没有颃之,颉之。”
好像有什么東西在我脑海中炸裂成碎片,带有岩浆般灼热滚烫的温度,把我所有的思绪和理智全都燃烧起来。我不敢去碰那些碎片,害怕它地狱熔炉的炽热,害怕有什么比噩梦比世界末日还要恐怖一万倍的事情,将要把我摧毁。
我从未像现在这般深刻地看到我所投影出的懦弱。
“你在撒谎……你在撒谎!你是个骗子!我不会相信你!”
我不敢转头去看就站在我旁边的颃之的反应。她也反常地一语不发。
“颉之,这个家里从来没有过颃之。我只生养过你一个孩子。”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刚刚的号哭和尖叫是我发出的。我像是个被抢走了心爱的玩具,坐在地上耍小脾气的孩子。胸口好像被凿开了一大口血洞,所有的幸福、温暖、希望、喜悦都在不受控地汩汩往外流,最后只剩下棉絮拼接的躯体。
很多事,突然有了所谓更贴切的理由。为什么所有人都躲开我,讨厌我,为什么我没有其他朋友。因为没有人能克服心里的恐惧,来面对这个永远在对空气说话的女孩,也没有人敢上前去把她叫醒。

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最后,曾像梦一样地出现的颃之也像梦一样地消失了。
我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认识了同校念建筑系的学长,我们慢慢开始熟络,再到后来成为好友。在某个秋意弥漫的清晨,他约我散步,然后向我告白。我心里迷茫着,也就没有回应,只说再想想。
被人喜欢着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我手足无措,所有的学识,所有读过的书通通从脑子里逃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心脏还在不知缘由地剧烈跳动,好像要冲破胸口,撕开故作镇定的伪装。
我可以去爱吗?我还能忍住颤抖,去拥抱我的爱人吗?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直到第二天黎明,熬到双眼通红的我在一片混沌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回答我:试试吧!
然后,我和César在一起了。
他不是我曾幻想过的爱人的模样。古铜色皮肤,深邃的眸子,笑起来仿佛有阳光洒下的典型西班牙人,性格仿佛是我的另一端。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未罗曼蒂克过。他不知道叶芝,也不知道阿蒂尔·兰波,他脑子里被建筑工地的数据和图表,以及如何健身塞得满满的。
每天上午去上班的时候,我总得帮他再系一遍领带,叮嘱他不要总是喝酒,早点回家,要是睡工地的话记得来个电话。
他总是一边“Vale,vale”(好的好的),一边给絮絮叨叨的女友一个温柔又略带敷衍的拥抱。
等他关门后听到电梯“叮”一声又“叮”一声,我的四周就又彻底恢复了寂静。我才会如梦初醒般惊觉,我的唠叨是曾经那个自闭而又自卑的我所预料不到的。我看着镜子里的身影,它是我又不是我,最后也只剩下一声“终于”的叹息飘散在空中了。
后来,我和César结了婚。
结婚那天晚上,我问睡在旁边的他:“你当初为什么会喜欢我?”
他想了一会儿,慢慢回忆。
“那天是Patricia老师的课。你趴在桌子上,看起来得了重感冒,鼻头红红的,一边用纸巾擤鼻涕,一边眨着眼睛。我路过的时候看到了你,就觉得你很可爱,像个亚洲瓷娃娃。我觉得你只是看起来不太好接近,但还是希望有人接近的吧。中国人刚到西班牙不适应又想家,也是不难理解的嘛。”
颃之,你看,这个呆头欧洲男有时候还是很可爱很温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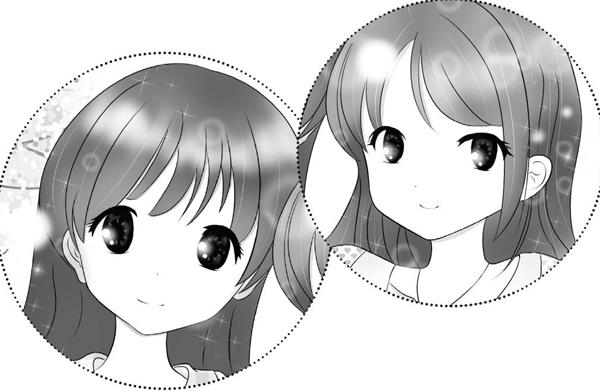
我也在那一刻突然想起被我遗忘了很久的画面,蕴藏着旧时光的温度。其实也没那么的重要,也没那么非记起不可。也不过就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原本温和亲切的父亲公司倒闭了,他开始酗酒,喝醉了就打人,家里没人敢反抗,原本温馨的家变得阴郁,变得让人憎恨。也不过是某天我躲在书桌底下,看着父亲暴打母亲,就在我咬着我的手无声号哭的时候,感觉到有一双温暖细腻的手,捂住了我哭到发疼的眼睛。
颉之的懦弱和颃之的坚强,颉之的平庸和颃之的闪耀,颉之的消极与颃之的乐观。可是究竟颉之是谁?颉之要找的,真的是颃之吗?还是那个坚强、闪耀、乐观的颉之?还是只是一个能给颉之希望和爱的人?
我对César说我到马德里是为了找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想再找了。我已经知道她在哪儿,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人爱她了。
César问我如果我见到她,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吗?
我想了会儿,如果见到颃之,大概会说,谢谢你。
谢谢你,我灵魂的另一半,我的颃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