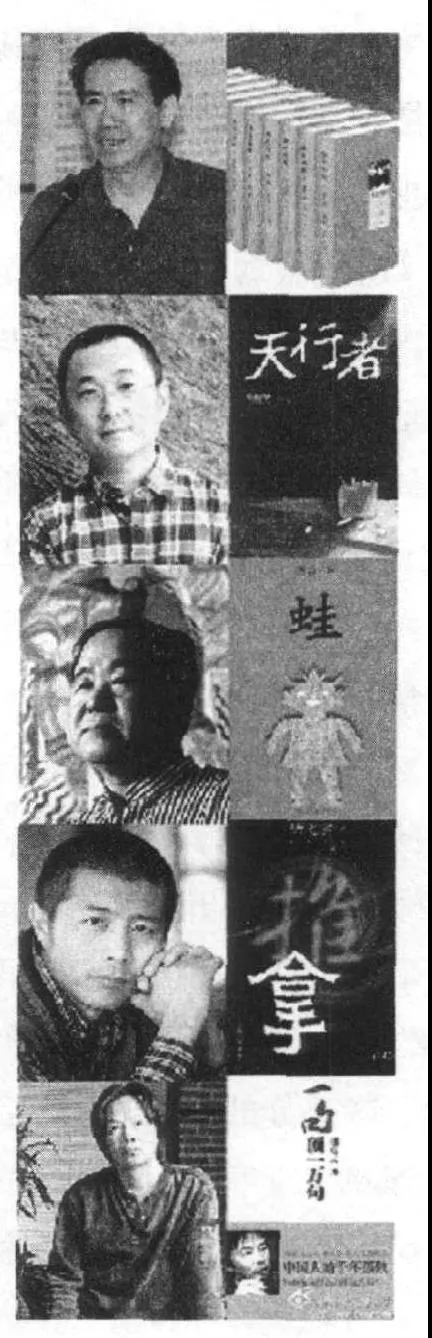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甫一公布,立即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切和热烈讨论。这其实是已经退居文化边缘的“纯文学”几乎唯一的成为公众议题的机会,也是公众期望通过这个奖来接触和了解“纯文学”的愿望的表现,也凸显了长篇小说在今天“纯文学”领域的关键性位置。作为文学界的同人,其实应该珍惜这个与公众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也珍视公众的讨论所表现出的关切和抬爱,因为文学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的事情,而是当下的文化的一个部分。“茅盾文学奖”其实是“纯文学”和公众可以交汇和沟通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没有这个“节点”,公众的阅读和“纯文学”之间早已存在的隔阂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应该以坦诚和谦逊来接受公众的批评,其实对于“纯文学”有批评总比漠视好得多。这其实从多个方面喻示了当下文学生态的复杂性。
实际上,当下的公众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已经远比十年前复杂得多,如何理解这种关系,如何了解公众对于文学的理解和想象,是一个颇值得深入探究的话题。
一、从“茅奖”的历史看文学之变
从1982年设立以来的八届“茅盾文学奖”,其实见证了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状况,也提供了一个对于文学进行观察和思考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个奖已经从一个以整个文学为对象的奖项,逐步转化为以文学的一个特殊分支——“纯文学”为对象的奖项。所谓“纯文学”指的是一种以“小众”为受众,以“高雅”的定位为诉求的文学类型。我们在八十年代所理解的“文学”经过了多年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一些对于文学有相当兴趣和爱好、有所谓“高雅”趣味的中等收入者的“小众”所构成的稳定但相对较小的市场,这个市场其实早已走出了前些年的困境,运作相当成熟和有序,这一部分的文学需求相当固定。这个“小众”市场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纯文学”市场。这个市场能够有效地运作,是文学出版的重要的方面,它既是传统的文学爱好者形成的稳定的空间,也是今天较高收入的都市白领所形成的。在这个市场中有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的作家也不超过十个人。在“纯文学”的空间中引起关切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对于“底层”的关切、由海外学者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学的价值问题的讨论以及对于“新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讨论等,一直是文学话语的中心。这说明纯文学虽然影响力已经变小,但在文学议题的设定等方面一直是社会所认定的主流。由此反观“茅盾文学奖”,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变化的复杂轨迹。从早期的“茅盾文学奖”,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可以说,当时的文学的全部代表性作品都在这一奖项的视野之中。而在当时长篇小说并没有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所以“茅盾文学奖”还仅仅是几个都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文学评奖中的一个,当时的全国中篇、短篇小说奖也极具影响力。当时的大众阅读和小众阅读也还没有分化,“茅奖”反映了整个长篇小说的走向。但到了今天,文学的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青春文学为代表的类型文学已经成为纸面阅读的重要部分,网络文学的崛起带来了新的阅读方式。当年我们理解的文学,现在就是文学的一个特殊的分支“纯文学”。而“茅奖”所反映的正是“纯文学”的现状和对于优秀作品的判断。当年的文学作品能够获得相当多的公众的阅读,“茅奖”只是对于这种阅读的肯定,而当今公众和“纯文学”的脱节十分明显,公众已经完全不熟悉“纯文学”作品,今天“茅奖”是向公众推荐作品。这里有三个方面的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它从反映文学的“全部”转化为反映文学的“局部”。其次,从反映文学的总体走向到反映“纯文学”的特定趣味。第三,从汇聚公众的阅读倾向到向公众推介作品。虽然这些年“茅奖”也力图扩大自己的领域,试图将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纳入其范围,但显然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本届有7部网络作品送选,其中的《遍地狼烟》进入第三轮,其他的第一轮就已经出局。据媒体报道,《遍地狼烟》作者李晓敏点出:“不论创作者还是题材内容与写法,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本就是两条道路,而现行茅奖评奖标准并没有因为接纳网络文学做过任何改变,想获奖比创造世界奇迹还难。”这些说法客观地呈现了茅奖是“纯文学”的专有奖项的现实状况。
从这个角度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文学格局这些年的深刻的和剧烈的变化。在“新时期”还出现了以类型小说为中心的“通俗文学”的写作,这是由王朔和海岩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打开的新领域。它指的是自“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与社会的市场化紧密相关的、更加面向市场的新文学。这也就是我们往往称为“通俗文学”的部分,这部分的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主要是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阅读市场中发展起来的。王朔和海岩的写作及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就是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市场中的现象。它包括一部分面对市场的作家,也有一部分在市场化中以市场导向运作的国营出版机构和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崛起的民营出版业,也包括在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诸如金庸、三毛等港台作家的流行。这一部分的写作和阅读是八十年代从传统的“文学界”中分离出去的。其运作方式是极为市场化的,是作用于一个八十年代以来构成的“大众”的市场的。这种文学在现在也形成了有较为固定的大众读者的稳定文学类型,如职场小说、官场小说、商战小说等等。像在文学界之外出现的,却在近年持续畅销,对于人们的文化经验有很大影响的姜戎的《狼图腾》就是一部跨越传统的通俗与纯文学的边界的作品。而像麦家这样以惊险悬疑的样态来观察复杂人性的作品也引起了人们的关切,而且还获得了上届的茅盾文学奖。而真正从其中分离出来的,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的是“青春文学”。
从21世纪初以郭敬明和韩寒等人为代表的“80后”作家出现到现在,“青春文学”在传统纸面出版业的市场中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影响力,“青春文学”已经逐渐成为文学中的重要力量,也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分支。如“第一届The Next 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就是由在传统的出版业界已经建立了声誉的长江出版集团的北京图书中心和以郭敬明为中心的柯艾公司共同组织的。这种传统的出版机构和郭敬明的团队的深度合作无疑显示了“80后”的市场影响力,并已经成为了文学的新的增长点。郭敬明本人创作的《悲伤逆流成河》、《小时代》及其团队所打造的文学杂志《最小说》一直在市场中有极好的反应。韩寒的小说创作虽然也在延续,但其风格已经和早期创作有了相当的差异,同时他也以网络博客的政论成为风靡一时的重要的言论作者。从总体上看,“80后”作家的青春是在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度过的,他们经历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和最活跃的时期。社会生活的发展让他们更有条件去表现从个人的日常生活出发到一种“普遍性”的人类的体验的可能。20世纪中国特有的经验现在逐渐被这些年轻人关切的人生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所充实和转换。他们的作品当然还有青少年的稚嫩,但其实已经有了一种新的世界和人类的意识,也表现出注重个体生命的意义,人和自然和谐等等新的主题。这些和我们当年的创作有了相当的不同。这些变化往往并不为成年读者所熟悉,但其所具有的影响力也不能低估,也是新兴的文化思潮的萌芽,自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青春文学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而庞大的作者群,他们的作品的特点就是青少年写,青少年读,正是由于“80后”“90后”的消费能力的逐渐展开而不断扩大其影响。这种“青春化写作”的发展乃是青少年文化的独特性的产物。这种写作具有非常明确的电子游戏和网络时代青少年的文化特征。
网络写作为中国方兴未艾的“类型”化的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园地,网络中诸如玄幻、穿越、盗墓等“架空”类型的小说给了许多青少年读者新的想象力的展现的可能,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忠实的读者。与此同时,如表现年轻读者在人生中所遇到的个人问题和挑战的小说,如感情、职场等小说也受到了欢迎。这些小说“类型”在现代中国由于社会的现实问题的紧迫性而一直处于受压抑的状态,没有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传统的文学评价系统中也地位不高,处于边缘。因为,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所具有的“感时忧国”的特点,对于这些或者“架空”的想像、或者回到个体所遇到的具体现实问题的文学类型往往并不注重。而网络的崛起,其实正是和中国的高速发展时期同步的,这就为这样一些小说类型在传统的纸面出版业尚未意识到其新的趋势的空间中有了重要的作为。网络文学和青少年读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其实会对未来文学的发展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网络文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其长度完全超出了纸面文学的限度,动辄以几百万字的篇幅出现,故事本身也有相当浩瀚的规模。这当然是网络的无限的容量和读者在网上阅读的状况所决定的。网络文学所走的路向,并不是许多人在当年所构想的实验性的路子,而是一种以浩瀚的篇幅和超越的想象力为中心的独特的写作。而“盛大文学”的出现,则努力统合华语网络写作,将主要的文学创作网站收入旗下,形成了具有巨大影响的新的网络文学服务平台,其所制作的电子书也已经在新的阅读方式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尝试。
客观地说,传统文学中的“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国内市场的现象,而“纯文学”具有的“跨国性”的影响力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目前看来,所谓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主要体现为“纯文学”。而在中国内部的读者中“通俗文学”依然保持了其本身的影响力,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也正在前所未有地扩大。这样,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学”模式已经被超越了,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框架已经被替代了。
二、“茅奖”是纯文学的晴雨表
从今年的“茅奖”看,五部作品其实集中地投射了“纯文学”的现状,既投射了它的优势和长处,也投射了它的局限和困难。五位作家都是多年来从事创作的文坛知名作家,他们获奖都不出乎人们的意料。莫言是中国文学界不多见的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作家。《蛙》通过一个中国本土的年轻作者和一位日本名作家的通信的方式,透过主观的折射穿透了中国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其中的独特的想象力和冷静的观察都有形式实验的支撑,附在后面的剧本也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莫言保持其一贯水准的作品。刘震云也是代表性的作家,《一句顶一万句》通过对漫长历史中个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经验的观察和思考,穿透了人类交流的复杂性,很值得一读。刘醒龙的《天行者》则以写实的方式,真切地描述了乡村民办教师的生活,延续和扩展了他的早期名作《凤凰琴》的主题,对于乡村社会的当下风貌有生动的刻画。毕飞宇的《推拿》通过写盲人来探究人类的感觉和生命的感受,也有其独到之处。这些作品都反映了“纯文学”对于阅读的丰富性的贡献,体现了“纯文学”的价值。由这些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纯文学”的基本形态,也就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形式”探索、“心理”描写和写实主义的结构所形成的一种“混合”风格才是“纯文学”的主流。“纯文学”受到赞赏和好评大多是定型在这样的表现方式上的作品,这几部获奖作品都体现了这样的风格。这其实是今天市场环境下“纯文学”的自身定位所决定的。八十年代以来的形式实验和心理描写的“现代主义”是技巧,是“纯文学”区别于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的“标记”,是“纯文学”可以识别的基本特征。而写实主义的结构,又会使小说不会因形式的激进探索而失掉和自己的“小众”读者接触的基本条件。因此这种“混合”风格已经是“纯文学”的主流。
这次评奖引发争议最多的是张炜的《你在高原》,这部作品长达450万字,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长的长篇小说之一,已经完全超出了当下读者可能阅读的长度。其中也混入了已经出版过的旧作,和新出版部分组合成一部小说,说明了作者强烈的企图心。那些哲理的议论看不出什么深意,似乎是文学的一个分支的“纯文学”用来彰显自己存在的表演,这么长,你们怎么比得了,其实网络文学里的长篇比比皆是。《你在高原》之平庸在于哲理思考其实撑不住,是些泛泛议论,人物如牵线木偶,在那里自怨自艾,不知所云。想写成哲人小说,却变成了高中生卖弄一点牵强平板的感想,一股酸腐又寡淡的气息,但和高中生不同的是卖弄得理直气壮。驾驭不了这么大的篇幅不是错,但偏要这么干就是错。 为《你在高原》辩护的有些理由实在牵强,如说作家写了二十年,很艰苦。但艰苦写出的作品一定要有价值,否则就是浪费生命。另外说长不应该被指责。长不是罪过,但长得冗长就是问题。这部作品其实就是一个“纯文学”的泡沫,关键在于讲哲理和人生的书,其哲理陈旧芜杂,思考空洞单调,语言嗦枯涩。这其实反映了“纯文学”在今天市场环境下的某种更深层次的浮躁,就是急于通过特殊的长度彰显自身的存在,用劳作的艰苦来标定自身的价值。就我的理解,这部以长见长作品的获奖所反映的是“纯文学”急切地希望得到社会认可的状况,也投射了一些从事写作者的复杂心态。缺少人阅读,连一些评委也未能读完的作品获奖,加重了人们对于“茅奖”的困惑,也阻碍了公众进入“纯文学”的意愿。当然,这其实也是“纯文学”面临的困难的一部分。
由此观察,莫言、贾平凹、刘震云、王蒙等作家都是在这个“小众”市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其中如莫言在全球华文的文学读者中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这样的新的内部格局和外部格局之间的越来越深入的互动和互相影响,形成了中国大陆文学的重要的新的形态。我们只能从这里切入对于“新世纪文学”的理解和分析。这些年来,如莫言的《生死疲劳》、《蛙》,贾平凹的《高兴》、《秦腔》,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余华的《兄弟》等等都有相当的影响。而王蒙的三卷本自传也是一个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的作家的人生历程的写照,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从“纯文学”写作的总体上看,它仍然有一个非常完整和有序的文学系统,其运作已经摆脱了九十年代时的转型期的诸多不适和困窘而归于正常。国家的支持使得原有的创作机制和通过期刊杂志发表以及较小规模的出版运作都能够有序进行。这样一个机制使得“纯文学”写作能够保持一个较大规模的作家队伍和较为稳定的组织和出版架构,这些都是在计划经济的原有的写作传统和新的市场结构之间协调的结果。“纯文学”作家的风格虽然各有不同,也受到不同的影响,但像八十年代那样较为激进的文体试验已经较少见到,写作趋于“常规化”,代表性作家的风格也趋于稳定,也就是在写实的基础上也容纳各种可能性的“混合”风格现在较为常见。有几个特色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掘和想象始终是其中心,如莫言、刘震云、贾平凹等人多专注中国历史和当下的扣连。二是对于特异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掘,如阿来、范稳、马丽华等人的作品在这一方面用力甚勤。三是对于当下社会剧烈变化中的阶层分化、女性问题等社会问题的关切,这在中短篇小说中居多,如具有左翼激情的曹征路的《那儿》等。在广东等地出现的“打工文学”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当然,像诗歌这样的文类,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更为专业和较小的领域,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公众阅读的领域,只能在一些新闻事件出现时进入人们的视野,如“梨花体”和“羊羔体”引起的讨论等。
但“纯文学”的国际性也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如这次获奖的莫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纯文学”的国际性的一面。华语写作的影响力其实已经是相当稳定的存在,这往往并不为中国国内的读者所充分了解。我们所知道的全球“纯文学”的空间实际上就是相当小众的,而在这个小众的圈子之中,中国文学其实已经被视为华语文学的主流。中国现有的“纯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小众化的国际阅读文化的组成部分。像莫言等人的小说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虽然“小众”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市场,而莫言这样的作家其实已经跻身于国际性的“纯文学”的重要作家的行列,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其实已经是海外华语文学和台港澳文学难以具备的。他们的新作出版后很快就会有不同语言的翻译,也由各个不同语言的“纯文学”的出版机构出版,而且经过了多年的培育已有了一个虽相对很小但相当稳定的读者群。在英语、法语、日语、德语等语种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出版和阅读机制。虽然这些作品的翻译文本的影响还有限度,但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文学空间。中国文学的国际性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的存在,也已经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性要素。当然,中国文学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市场也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学出版业的重要部分。许多重要的国际性作家在中国都有稳定的市场。这种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深入联系实际上已经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我们原有的焦虑。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球华语写作的最重要、最关键的空间,是全球华语文学的中心。像王蒙、莫言、刘震云、苏童等作家都已经是全球华语文学的最重要的作家,他们在海外华语文学的读者中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同样,我们可以从无论港台作家还是海外华文作家的中文出版作品在大陆市场的行销中看出。大陆的虽然从内部看相对较小,但从外部看极为庞大的“纯文学”市场,在开放的环境下其魅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域的华语文学空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港台的重要作家如张大春、朱天文等在大陆的文学市场中的影响已经相当大。同时,像虹影、严歌苓等从大陆移民海外,并在海外出版作品获得声誉的华语作家,在新世纪之后纷纷回归大陆,在大陆的文学出版中寻求发展,这其实也显示了中国大陆在文学方面的中心位置。像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虹影的《好儿女花》、张翎的《金山》等等作品,都是这些曾经或者当下生活在海外的作家华语文学的“跨区域”、“跨国”写作,这些作品都以内地作为主要的出版地。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中国写作中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张爱玲的未发表过的作品《小团圆》、《寻乡记》等陆续出版,也在全球华人文学空间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也说明华语文学的融合的意义。
因此,从“世界文学”和全球华语文学的角度看,中国大陆的文学本身已经是其中的有机部分,已经不再是在边缘充满焦虑和困惑的文学。中国文学已经无可争议地处于世界文学和全球华语文学的新的平台之上。它的形象和形态已经发生了独特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说明了我们今天对于它的评价和价值方面的困惑其实来自这个新的空间的新的要求。可以说,现在中国文学已经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独特形态。正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才会感受到新的压力和新的挑战。
三、“茅奖”与纯文学的未来
从总体上看,这次评奖大体反映了“纯文学”的现状。透过这些现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获奖作家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而“纯文学”为公众所熟知的代表性作家也屈指可数。从“70后”开始,除了葛亮等少数作者,纯文学尚未出现具有分量的代表性作家。“80后”的作者或在青春文学领域,或进入网络文学,与纯文学的整个机制相脱节。后继乏人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其次,这些获奖作品仍然是延续了传统的“新文学”写农村的长处,说明“纯文学”在表现不同的生活方面的困难。连当年《钟鼓楼》这样以城市为题材的作品也已经难以见到。这说明“纯文学”的表达仍然难以有更加深广的表现力和想象力。第三,“纯文学”如何在它的相对稳定的“小众”读者之外,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要求它像类型文学一样有相对“大众”的读者,但也需要更多的人了解和阅读,才可能永续发展。第四,如何从“国际性”的角度去处理和思考中国“纯文学”的问题。评奖当然各有选择,但这次的“茅奖”所激起的讨论,无疑会引发人们关于“纯文学”的新一轮的思考和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