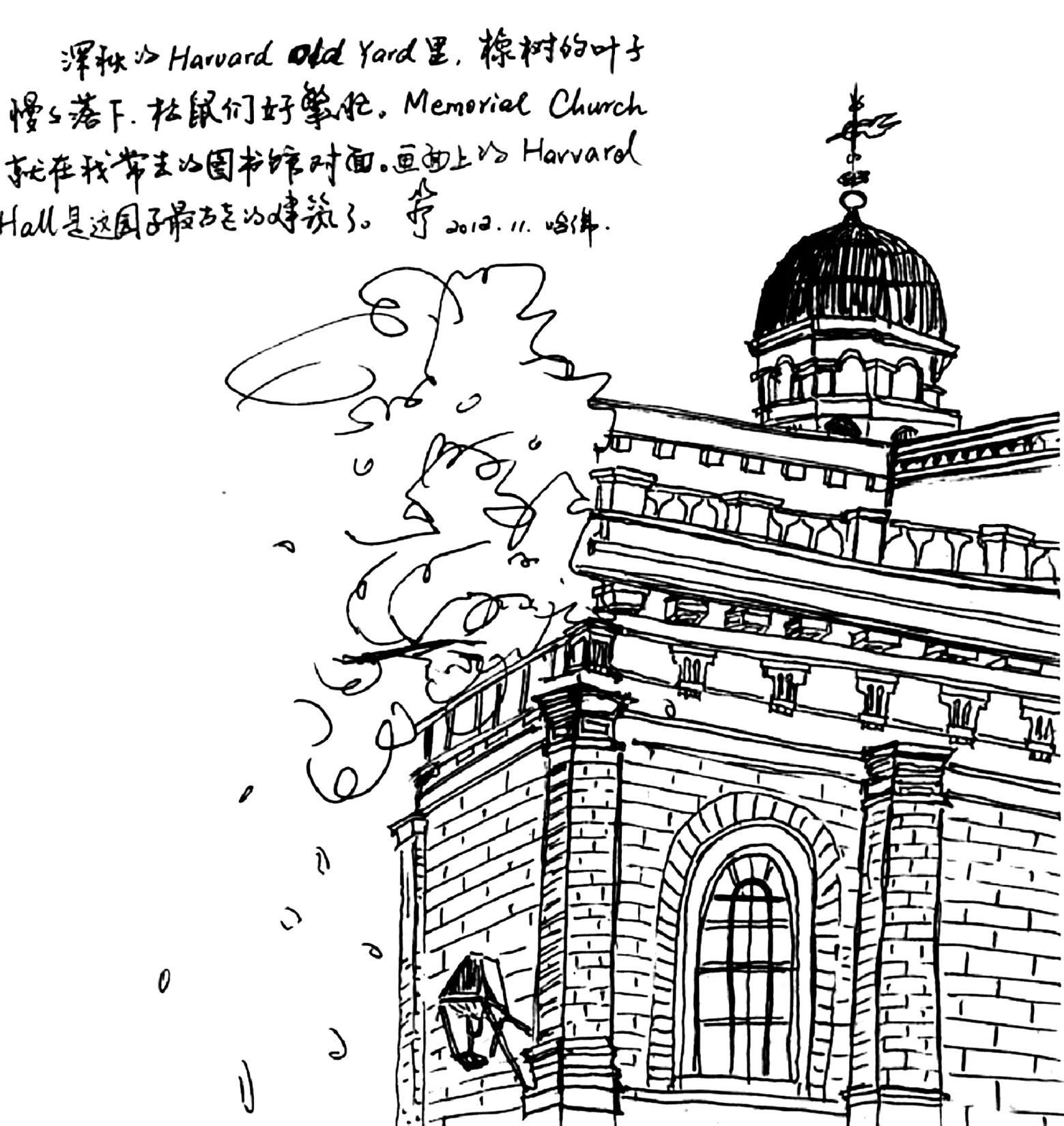
被稱作哈佛廣場的地方不過是一片三角地,常聚集著一些自命不凡的流浪藝術家、無家可歸者、自我放逐的年輕人,又或者未來可能一鳴驚人如今虎落平陽的人物。
一、 咖啡店裏的女詩人
在一月份劍橋的冷風裏,正值寒假,從街對面校園出來的學生少了很多,步履匆匆的行人和緩步悠然的遊客依然不少。肯尼迪街(JFK Street)和麻州大道(Massachusetts Avenue)把角的星巴克咖啡店常擠滿了各色人等。有多少人知道呢?早在哈佛建校前五年的1631年,就在這個地點曾住著一個婦人,名叫安妮·布拉德斯特利特(Anne Dudley Bradstreet,1612—1672) 。她是美國第一位詩人,而且是殖民地第一位在英國發表詩作的詩人。此人和丈夫是第一批來新大陸的清教徒之一,在麻州的撒勒姆登岸,之後一路向南,直到波士頓。在劍橋居住的這幾年,19歲的她雖然還毫不起眼,不過之後的歲月,這位女性没有被8個孩子、繁瑣的家務、做了殖民總督的丈夫所累,勤奮寫作了超過四百頁詩作。1650年,她的詩作冠名以《美洲新誕生的第十位繆斯》(TheTenth
Muse
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by
a
Gentlewoman
of
those
Parts)在倫敦出版。安妮的父親和丈夫都在當年哈佛建校時助過一臂之力,她的兩個兒子也都畢業自哈佛。1997年10月,哈佛在 Canaday Hall宿舍旁邊建了一個布拉德斯特利特門(Bradstreet Gate)紀念她作爲美國的第一位詩人。這扇門上鐫刻著她的話: I came into this Country, where I found a new World and new manners at which my heart rose.
二、 茱莉亞的厨房
我從我的住處每日步行30分鐘沿華盛頓街(Washington St.)走到學校,都會路過厄文街(Irving Street),這條街的103號,如今還是一幢整飭有序的白房子。我從週邊轉轉,看不見什麽。不過我知道,60年代曾名噪一時的美國廚神茱莉亞. 查爾德(Julia Child,1912—2004)裝修優良的著名廚房就曾坐落這裏,香港著名美食家蔡瀾因爲她的姓氏稱她“朱兒童”。自稱“生性爽朗、大嗓門”的加州姑娘茱莉亞37歲開始在巴黎學習法國廚藝,1961年,劃時代的《掌握法國菜的烹飪藝術》在美國出版。這本厚達734頁的洋洋巨著,以前所未見的、詳盡而精確的寫作風格迅速征服了讀者,至今仍在不斷再版。1963年,茱莉亞開始主持名爲“法國大廚”的電視烹飪節目,熱情歡快的天性和獨特的顫抖嗓音讓她成爲家喻户曉的名廚。1966年,她的頭像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四十年間,茱莉亞主持了數十檔公共電視節目,撰寫了大量烹飪著作。而她在劍橋厄文街家裏的整間廚房後來都被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館收藏。距離此處不太遠的哈佛大學拉德克里夫學院史辛格圖書館收藏了她的大部分手稿。你若不認識她,不妨去看看梅里爾·斯特里普扮演的茱莉亞,在2009年的電影《朱莉與茱莉亞》(Julie
&
Julia),你可以重新看到女性對廚房和食物的熱愛,如何可以幫助當代都市人尋回自我。我很喜歡電影的温情,那從日常和口腹之欲中教會你感受生活的美好,抗拒灰暗的輾轉,讓人覺得心底無限熨帖。據説有一次,茱莉亞在節目中把一隻火雞掉到地下,她毫不介意地拾起來,洗過了,繼續做菜。她説:“你在家裏廚房時發生這種事,也不是這樣的嗎?” 哈!不知道在這條街的美麗厨房裏,茱莉亞多少次把食材掉落又撿起,沖一沖,放進鍋裏,説不定順手放進了嘴裏也未可知。
三、 兩个詹姆斯舊居
依傍著茱莉亞的廚房不遠處,在Irving St. 95,曾住著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著名的心理學家、哲學家,詹姆斯家族的長子。
你還是没想起來?——好吧,雖然我這麽説他會不高興,不過我可以提醒一下,他是著名小説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有點印象?對,他也是我們所使用的一個詞“意識流”的最早發明者。
年輕的威廉拿到醫學博士之後,受當時流行於德國決定論哲學思想的影響,一度悲觀消極,最後得了抑鬱症。他一度相信,人生一切是註定的,在註定觀念束縛下生命毫無意義與目的。據説,他在最艱難的時日裏,是依靠閲讀《聖經》勉强維持活下來的。直到後來因讀到一篇雷諾維葉(Charles Renouvier, 1815—1903)有關自由意志的文章,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並決心通過對意志功效的信仰、對人類心理生理的研究治好自己的病。
詹姆斯熱衷於宗教經驗研究,不過,吊詭的是,他竟然也是實用主義的開創者之一。他説:“根據實用主義原則,只要關於上帝的假設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能令人滿意地起作用,那麽這個假設便是真的。”這當然讓他和正統教會關係緊張。1890 他完成了《心理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兩卷,其中第9章題爲“思想流”。在這一章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意識流”概念:“意識本身並不表現爲一些割裂的片段……它並不是什麽被連結起來的東西;它是在流動著的。‘河’或‘流’乃是最足以逼真地描述它的比喻。此後我們在談到它的時候,就把它稱之爲思想流、意識流,或主觀生活流(the stream of thought, consciousness, or subjective life)。”這一概念後被廣泛而準確地描述了類似的維吉尼亞·伍爾夫、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他的弟弟亨利·詹姆斯不喜歡波士頓,早早移居歐洲,後來乾脆入了英國籍。亨利的小説熱衷描繪人物的内心活動,頗享盛名。不過作爲心理學教授的詹姆斯文筆也出奇的優雅、曉暢。據説有人到圖書館借來他寫的書,管理人員略帶風趣地問:“你是想借寫小説的心理學家詹姆斯的書,還是想借寫心理的小説家詹姆斯的書?”
還有一個值得一提,寄居巴黎的美國著名女作家葛特魯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1874—1946)被稱作“現代主義之母”。她的沙龍名流雲集,當時的無名小輩後來都成了現代主義文壇上的耆宿,就是她命名了海明威等一批美國作家爲“迷惘一代”(Then Lost Generation)。此人在1890年代就學於拉德克里夫女子學院(現與哈佛合併),就曾在威廉·詹姆斯指導下進行普通電機全自動現象的實驗,研究人的腦活動分爲不同區。這或許刺激斯泰因後來寫出“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這樣的奇詭句子。
四、 還有厄普代克

1950年入學哈佛的“新鮮人”(freshman,即一年級新生)中有一位名叫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8),當四年後從哈佛畢業那一年他也在《紐約客》上發表了處女作。再之後,他勤奮的如同“文學蜘蛛”,32歲即入選爲美國國家藝術文學院院士,創作生涯中60多部作品的成就讓人尊稱他爲“美國文學中的巴爾扎克”。厄普代克的作品大多熱衷描繪他的家鄉賓州或者乾脆就是費城,對哈佛吝於筆墨。他在回答1967年《巴黎評論》的採訪時説,哈佛不缺他一個讚美者,不過他還是回憶説:“我記得弗格美術館明亮的窗户,記得我未來的妻子推著叮叮作響的自行車走過白雪皚皚的校園,記得當我走進前廊時《諷刺》雜誌地下室裏鑽出的老雜誌的那股潮味兒就會沖進鼻孔,還有無數在教室裏的愉快發現……”白雪皚皚的校園雖然我也有幸走過,不過弗格美術館與比較文學系的小樓在同一條昆西街(Quincy St.),但我從没見過它的窗户,因爲它一直在整修。《諷刺》雜誌的編輯部被稱作“城堡”(Harvard Lampoon Castle)在不遠的Bow St. 44,我帶家人專門去轉過。6歲的J 很喜歡“城堡”的外形,敦厚,滑稽,兩隻大眼睛,還帶著消防員一樣的帽子,漆成彩色的門如同惡作劇地咧嘴在笑。這個可愛的東西不恰當地坐落于兩條路的三角地帶,城堡的大眼睛正對著Mt. Auburn St。厄普代克當年住的宿舍就在城堡旁的Lowell Hall。我們在冬季走進去,庭院裏沉寂落寞,只有兩個男生邊抽煙邊交談。
在《基督徒室友》中厄普代克少有地描寫了哈佛的生活: 冬季期中考之後,“日子静謐綿長,會有一場暴雪,也許兩場……磚樓、拱門、古老的講經臺、陳舊的宅邸沿著布拉圖街(Brattle Street)一路向前。一年級的新生逐漸感知他暫時擁有的這份遺産……家鄉的來信不再那麽重要。時間展開了,日子還長著”。
厄普代克後來的回憶録中説,50年代的哈佛曾經有一批諸如T·S.艾略特、羅伯特·弗羅斯特、狄蘭·湯瑪斯和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那樣的文學名流親臨講壇。可以想象,得以親炙大師,這對懷抱一腔文學激情的學生來説是何等彌足珍貴的經歷。
我像個一年級新生,在布拉圖街逐漸感知這份暫時屬於我的遺産。
五、 瓦爾登秋思

“瓦爾登湖的風景是卑微的,雖然很美,却並不是宏偉的,不常去遊玩的人,不住在它岸邊的人未必能被它吸引住……”1854年37歲的梭羅記下他隱居兩年的經歷,當時不會奢望,一百多年後,這片深緑色小湖,會成爲那麽多中國人到美國之後的生態朝聖地。
雖然瓦爾登湖的確算不得景物非凡,但在美這一年我竟然三訪瓦爾登,而印象最深刻的,却是第三次秋訪瓦爾登。與我春夏兩季的造訪相比,11月的再訪雖則少了初見它時的興奮與浪漫,但從容的行程、悠然的心情讓我有可能在漫步湖邊的時刻細細體味自然帶給我們的啟示。
記得那日清晨下了些小雨,午後開車到湖邊的時候,瓦爾登湖寧静明麗,籠罩在坦誠温暖的新英格蘭陽光下。孤獨怪癖的梭羅痛恨城市文明與教化對自然的改變。愛默生曾轉述梭羅的話説,斧子總在砍樹,“幸而它們不能把雲砍下來”。他真有見地,他死去一百多年了,今天的瓦爾登碧空中低垂的大朵白雲,正擁鏡自攬,懸在湛藍的湖水上面。濃密的樹林已經有了秋的模樣,但還不完全。巨大的松樹兀自蒼翠著,完全不顧身邊其他的樹種的變化,即使到了冬天它也不打算有何遷就。它真是一個倔强的物種,難怪中國文人因其傲骨稱之爲“歲寒三友”之一。不過橡樹就不同了,枝椏上它綫條流暢的“手掌”婆婆娑娑伸向湖邊,有的翠中帶黄、有的黄中帶紅、有的紅中已顯深褐……要知道不是所有樹種都會在秋天變成紅葉,也不是所有可以變色的樹種每年都有機會展現他們内在豐富,甚至就是在同樣一株樹上,因光照、晝夜温差和酸性變化條件不同,“本是同根生”的每一張樹葉都會有自己的生命顔色。到底哪一片會被“眷顧”,會被“揀選”,樹葉們永遠也弄不清,却不妨礙它們酣暢淋漓地盡情展現它們生命最後的風采。
沿著湖逆時針漫步一周並不需要多少時間,不過,可以細細品味的還很多。
湖邊小徑上,稀稀疏疏早早落下了一批批葉子,踩在脚下,綿密厚實,質感柔軟。它們大多都還是緑色的或者半黄的,生命還没有綻放完全就從母體離開了。遊人只顧目光向前,向上,被藍天白雲、緑水彩葉吸引了目光,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些脚下的落葉其實已爲我們的風景鋪上了大地的底色,提供了林中漫步的窸窣聲。但又何妨呢?“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爲美好。”(傳道書2: 11)所有被造物的生成與結束都有其定時定期,每一個個體也都各有其美。
天高雲低,樹林矮矮的,爲這泓卑微的湖水鑲嵌了一條彩金的花邊。我們繞過梭羅的小木屋遺址,轉過鐵路的邊緣,林中的小路兩側雖然還没有白樂天所謂“連行排絳帳,亂落剪紅巾”的漫山紅遍,但是那超越了語言、眼睛、畫筆所能觀察與表達的色彩,仍然讓你有著一種衝動: 帶走瓦爾登的一片秋葉吧!我一路不斷搜尋,拾取又扔下。它們要麽顔色不均匀,要麽形狀不周正,又或者受過蟲咬風侵,落下了點點疤痕……這些葉子,遠看氣勢非凡,色彩飽滿,近處挑揀時,竟然不會有一片完美!
從湖岸的小路漫步向回,轉到東南。陰翳舒爽的樹林突然更加振奮了精神,我猛抬頭,午後的陽光正刺眼。無遮無攔的陽光從西北斜射過來,照的我睜不開眼睛。我躲進一片樹蔭,却發現剛剛如同絢麗油畫的景致突然躍升出奇景,變换了材料——逆光望去,在太陽的照射下湖水瀲灩,像是藍寶上撒著金片;黄緑相間的樹葉被透過來的陽光變成了上等琉璃,晶瑩剔透、流光溢彩;剛才橘紅、深褐的葉片也被這奇妙術士轉瞬間點化爲金珀、血珀,斑斕的色彩裏帶上了歲月沉澱出的豐厚……我有些出神。我們,何嘗不像這湖水和樹葉,雖則外表絢爛豐富,也不能掩蓋我們的平凡和短暫。唯有我們願意轉向光,願意折射光,才能改變和提升這有限生命的意義與品質。你,不覺得嗎?
具有超驗主義思想的梭羅,在大自然中尋找到了“更高的法則”。他雖然與正統的基督教有著根本的隔閡,但是當梭羅驚歎“這湖當然是一個大勇者的作品,其中毫無一絲一毫的虚偽”時,我們還是會情不自禁不斷頷首。他知道認識真理和體味自然不需要山高水遠,家門前的這一捧水中便可尋見。於是他一時興起,在文章中插入了幾行詩,開頭幾句,在我第三次造訪之後,才升起了同感:“這不是我的夢/用於裝飾一行詩/我不能更接近上帝和天堂/ 甚於我之生活在瓦爾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