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戴遂良的耶穌會士身分
在中國文學早期的海外傳播中曾起過關鍵性作用的是那些來華耶穌會士(jésuites)。耶穌會(jésuites)是與詹森派(jansénistes)針鋒相對的一個宗教團體,耶穌會士們認爲任何國度、任何民族的人都有資質和權力聽到上帝的聲音並被受上帝的恩澤。耶穌會創立之初衷便是拯救世界各地尚未歸依天主教者(拉丁語爲:infideles)。而且爲了傳播上帝的福音,耶穌會士們樂於學習當地的語言和接收當地文化的洗滌;耶穌會的創立者羅耀拉(Ignatius de Loyola)曾叮囑信徒們要懂得“從他者的門進去,將他者帶出來”。這“他者”自然是指尚未歸依者。不少耶穌會士通過對中國典籍的研究來佐證上述“資質”之存在,或者他們乾脆研究起中國本土文化中的基督因素或基督情結。這些耶穌會士中較爲著名的就有戴遂良。戴遂良在《中國哲學思想及宗教信仰》(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一書的初版前言中將研究動機説得再清楚不過了:“我是應巴黎天主教學院之約撰寫這個讀本的。來華三十年,我爲上帝開疆拓土,孜孜研述;本書即集三十年來探究之心得也。謹呈之於天主教學院,忝列鴻庠,或能對宗教與科學有所芹獻。”戴遂良認爲中華民族的意識中有天生的基督情懷。先他三百年來華的另一名耶穌會士利瑪窦(Matteo Ricci)在傳教受挫後,花十幾年功夫學習中文並研讀中文典籍。利瑪窦學習中國文化是一種宗教行爲,他力圖從中國的文化典籍中找到儒教同天主教間的契會之處 ;他得出的結論是:1. 中國人所信奉的“天地”即天主教的“上帝”;中國人的“祀”僅僅是爲了對祖先表達緬懷之情和孝敬之意而已,不屬於偶像崇拜。2.所謂的“祠堂”祇是簡單的廳堂,“宰牲”祇是爲了烘托節日氣氛,主持“宰牲”的人祇是屠夫而已。有些學者將這種來華耶穌會士入鄉隨俗的現象稱作“中國化”(sinisation des jésuites)。作爲耶穌會士的戴遂良秉承的是利瑪竇以來的耶穌會精神和傳教手段,其文學翻譯活動應該亦屬於這一宗教範疇。二、《現代中國民間故事》的命名由來
戴遂良的《現代中國民間故事》於1909 年在中國獻縣出版,共收集了222 篇中國志怪類文章。文章分别來自以下作品:《江行雜記》《聊齋志異》《三國志》《西遊記》《紅樓夢》《暗室燈》《新齊諧》《續新齊諧》《桂苑叢談》《冥祥記》《宣室志》《兩京記》《潇湘録》《搜神記》《搜神後記》《紀聞》《洛陽伽藍記》《擴異志》《酉陽雜俎》《幻異志》《原化記》《幽明録》《太平廣記》《松江府志》《異聞總録》《集異記》《稽神録》《靈怪録》《聞見後録》《春渚紀聞》《龍興慈記》《墨莊漫録》以及《剪燈新話》等。全書共計422 頁,正文採用豎排版式,每頁左側印有中文原文,右側是法語譯文。《現代中國民間故事》所録文章之間的排序頗爲肆意,我們看不出作者刻意安排的痕迹。與戴遂良同時代的學者、“漢藏語系”這一術語的創立者普茨路斯基(Jean Przyluski)當時就評論戴遂良的這部作品説:“如果故事間的排列不是任意爲之而是經過系統的處理就好了[……]。”其實戴氏完全可以爲故事間的排列定一個標准(如原文的成書時間、原文的體裁等),但他似乎並不在意這些細節。在翻譯編纂其他書籍時他這種不拘小節的特點也常常爲同行所詬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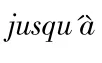



當然,戴氏認爲文學在客觀上有教化民衆的功能,這一點不無道理,且與周作人的觀點相吻合。周作人的觀點是:“影響中國社會的力量最大的,不是孔子和老子,不是純粹文學,而是道教(不是老莊的道家)和通俗文學。因此研究中國文學,更不能置通俗文學於不顧。”周作人所謂的“道教”不是“老莊的道家”,則一定是民間的道教“迷信”和道家故事了。文學家周作人和傳教士戴遂良在這方面都無視了意大利符號學家艾柯(Umberto Eco)所謂的作品的意向(intentio operis),我們將在下文作更詳細的分析。
三、是詮釋文本還是使用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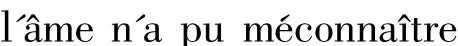
這一出發點決定了戴遂良在處理中國文學文本時的一些傾向。在《中國哲學思想及宗教信仰》中,戴遂良難以按捺其作爲耶穌會士的衝動且每每插入自己的評價,有時還將中國的某些信仰與天主教的教義進行比較,或找到共同點,或尋找差異,目的是方便傳教士讀者對中國信仰的理解和日後的傳教工作。在《中國哲學思想及宗教信仰》中提及基督性且對中西信仰差異作出説明的地方有25 處之多。在《現代中國民間故事》中,戴遂良也處處插入自己的詮釋和讀後感,在譯文最後還不忘加註説明(brève note explicative),這更意味着他所構建的文本是封閉的。一個封閉的文本有專門的用途,有固定的使用方法,有固定的讀者群。相反,文本的開放性是文學文本乃至一件藝術品的重要價值所在。一個開放的文本可以由讀者進行多種解讀,一個文本期待著一個有可能對其意向進行各種體驗的合格讀者(Model Reader)。但是這種解讀應該限於文本意向範圍(intentio operis)。文本的意向實際就是“文本的内在連貫性”(internal textual cohenrence)。如果文學文本意向的一個方面是作爲文學文本存在,我們便不能把這個文本當成廣告詞或宣傳書解讀。我們甚至不應有意識地去審視文本的性質。文學文本的合格讀者應沉浸於故事(如果作品形式是小説)中不能自拔,而不應該去揣摩作者爲何要採取某種寫作方式。超出文本意向的解讀在艾柯看來是對文本的使用(use)而已。具體來説,面對一本色情雜誌,一個合格讀者會陶醉於雜誌帶來的這樣或那樣的情色愉悦。又譬如説,在讀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時,假若一個讀者據書推測歐幾里德有喜好晦澀黑暗事物的癖好,那麽這個讀者已經超出了遵循文本意向進行解讀的範圍,他是在使用《幾何原本》這個文本。戴遂良對《現代中國民間故事》中一系列名著節選的限定性説明(這些説明在該書前言中分門别類地列出)、所加的註解、法中對照的排版方式以及閲讀注意事項的標識等,這些都是屬於文本外部的行爲,破壞了原著的文學性,應歸入使用文學文本的範疇。這同時也是一種呼籲讀者使用而不是解讀文本的舉動。
四、《現代中國民間故事》的翻譯策略——以《牡丹燈記》爲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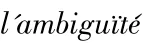

戴遂良對中國文學的改編調整既體現於文學主題與故事上,又體現於敍事方式上。例如,在故事情節上,戴遂良在《現代中國民間故事》中祇將《牡丹燈記》的前面一部分譯介給法國耶穌會士讀者,卻删除了喬生、符麗卿以及紙人金蓮後來被押赴“九幽之獄”的結局以及魏法師因泄露鐵冠道人之行蹤而患失語癥的故事。這一部分之所以被删除大概也是因爲戴遂良認爲它缺乏質疑精神和缜密的推理過程。魏法師僅僅因爲泄露鐵冠道人的秘密就患上失語癥在耶穌會士看來是缺乏邏輯條貫和理論依據的。自然,這更是因爲戴遂良未能從根本上接受中國的那一套形而上學的體係。
在涉及志怪文學時,敍事方式自然又同故事情節密不可分。本於自身所處的話語體係,更是出於傳教的需求,戴遂良除了訴諸肢解原文本、大段删掉無用部分這樣粗綫條的手段外,在翻譯決定保留的部分文本時,主要採用的是敍事和語義上的歸化譯法(domestication)。下面僅擇戴氏節譯之《牡丹燈記》爲例分析説明這種歸化的具體體現。
1.通過改詞、添句和修改標點等方法來實現敍事上的歸化
《牡丹燈記》開篇喬生與符麗卿相遇本身就是異常荒謬和違反常規的:
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妍妍媚媚,迤逦投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顔稚齒,真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持,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事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敝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攜手至家,極其歡昵。自以爲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淑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殁,家事零替,既無兄弟,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耳。”生留之宿。態度精妍,詞氣婉媚,低回就枕,甚相歡愛。
至正庚子年,即1360 年,一個國色天香的妙齡女子(符麗卿)在深夜輕易跟隨一個陌路書生回家且與之“低回就枕,甚相歡愛”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事。在戴遂良看來,西方讀者未必能夠適應這一情節安排,於是在翻譯時作了一些添詞添句處理。他將“女忽回顧而微哂曰”一句譯成“La jeune fille remarqua ce manège. Tournant la tête et souriant au jeune homme,elle lui dit”。其中,“La jeune fille remarqua ce manège”是戴遂良加入的句子,中文意思是:“這位芳齡女子發現了喬生的把戲”。有了識破喬生伎倆這樣的鋪墊,下文的進展就顯得順理成章些,譯者就可以安排女子利用喬生想占便宜的心理施展各種實際有利於女子自己的計劃。相反,如果没有這個鋪墊,故事顯得甚至不符合一個陰謀的發展順序,正如戴遂良自己所説,作品原文作者“從不質疑,從不感到詫異”。
又如“女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一句中的“金蓮,可挑燈通往也”譯爲“Sans répondre,la jeune fille rappela la bonne qui marchait devant.‘Revenez,Kinn-lien,lui dit-elle;éclairez-nous’”。Sans répondre(中文意思是“没有回答”)是對“無難意”的翻譯。譯者選擇這樣的翻譯同樣是爲了讓情節顯得不是那麽突兀,讓讀者不會覺得女子無來由地過分主動。
戴遂良還在譯文中用替换標點符號的方式彌補原文意義上和敍事上的缺陷或不連貫。例如在翻譯《牡丹燈記》女鬼符麗卿“初無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事非偶然也”這句對話時,他在法語譯文的末尾以省略號替代句號,形成敍事上的留白,在不中斷敍事的前提下將女子到底還説了什麽或向喬生暗示了什麽留由讀者去想像。經過讀者自己補充這個過渡後,下文喬生“趨前揖之”並邀請女子回家的更大膽舉動才不顯得突兀,省略號發揮了一種複調(polyohony)作用。這種複調功能還在於,我們透過戴遂良改句號爲省略號的行爲隱約看到他想改善志怪文學敍事唐突的缺陷,讓《牡丹燈記》這份素材更符合培養年輕耶穌會士的需要。
2.通過語義義素(sème)的擇棄與拆解實現文化負載詞的歸化
一個詞往往具有多個義素,對其中某個義素的選擇和對其他義項的捨棄體現著譯者的某種主張。下段中的“鬼”這個文化負載詞被戴遂良簡單翻譯成了morts(死亡的,死人),意在弱化中國文化中的非基督色彩:
鄰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妝髑髅,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駭。明日詰之,秘不肯言。鄰翁曰:“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日真元洩盡,災眚來臨,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爲黄壤之客也,可不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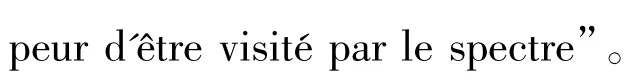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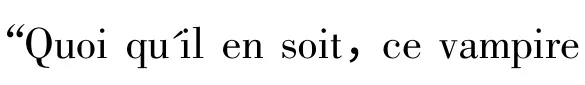
但無論如何,戴遂良對中國神祗、鬼怪和妖魔這些範疇又是表示理解和尊重的,《現代中國民間故事》中的每一篇幾乎都涉及這些範疇,如河神、女鬼、城隍、社公等。因爲這是理解傳統中國無法規避的思維模式。在無法迴避時,戴遂良在譯文前寫有一系列導論,在導論裏他儘量用天主教甚至是新教的一些名號來翻譯中國的神祗鬼魅。例如,他將關帝譯作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l'Etre suprême。而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l'Etre suprême 在天主教裏又是對教皇的稱呼。在談及閻王時,他所使用的術語所包含的義素則更能體現天主教色彩,如ame,réincarnés,bilan des existences précédentes 以及communion。而這每一篇導論又約束和解釋著後面的譯文。
結 語
通過上述對《現代中國民間故事》的分析並結合我們對其他法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學譯介研究的觀察,我們發現法國研究中國文學者大致可分作兩類。儒蓮(Stanislas Julien)和雷威安(André Levy)等人屬第一類,是對中國文學深懷摯愛者。另外一類法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學感興趣的出發點則是超出文學範疇的。這一類包括伏爾泰(Voltaire)和于連(Fran?ois Jullien)。伏爾泰寫作《中國孤兒》(L'Orphelin de la Chine)是爲了用他者的言行理論來印證自己的哲學觀點。而于連則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另類空間(hétérotopie)理論的實踐者,他企圖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尋找與西方思維對立、未受西方思維侵擾的他者性(altérité)。他們關於中國文學的探索充滿了實用主義色彩,文學於他們是工具,是到岸時該捨棄的筏。戴遂良則因傳教需要而涉獵譯介中國文學。第二類中國文學研究者,有時爲達到目的甚至不惜改造中國文學這個工具,上述戴遂良的翻譯便是最好的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