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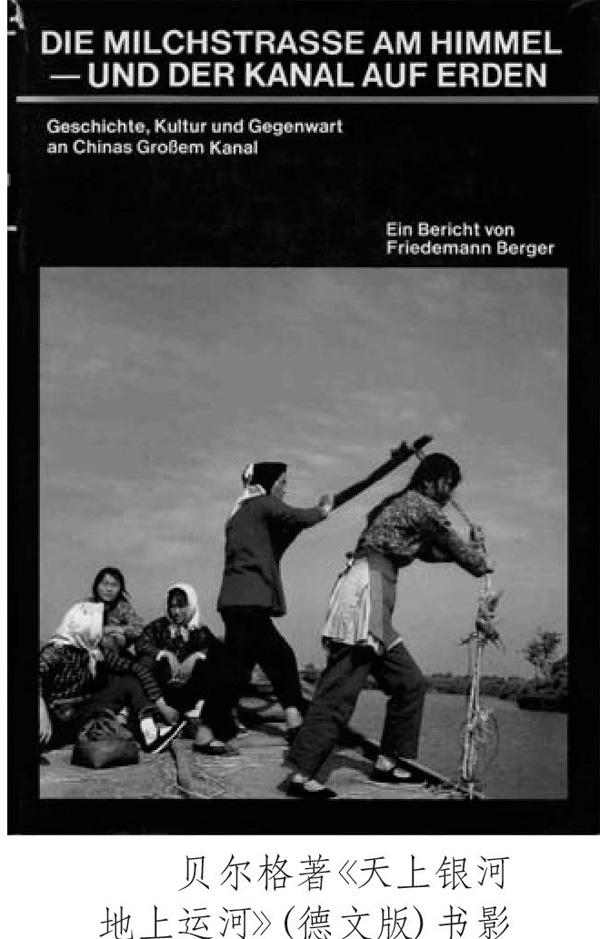
1986年金秋时节,应江苏省委宣传部之邀,原文化部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的民主德国专家费里德曼·贝尔格,由该社德文部主任霍勇擔任翻译,沿京杭大运河江苏段采访一个月,拟写一部反映古老大运河历史和现状的纪实性作品。我当时在镇江市委宣传部对外宣传科工作,他和霍勇在镇江的采访活动由我和有关同志陪同。
一
省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处预先在南京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研究讨论如何安排沿河各市的采访活动。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王霞林在会上说,以外国人的视角观察和体验大运河及沿河地区的改革开放状况,对外国读者应更具吸引力。他举例斯诺当年赴延安写出引发轰动效应的《西行漫记》,说明外国友人写中国的优秀作品所产生的影响。
按照行程安排,贝尔格于9月下旬抵江苏后从苏州沿运河一路向西,到南京后再转向扬州,并由扬州北行,从徐州返回北京。贝尔格是莱比锡基彭豪尔出版社总编,并任东德全国作协理事。他以抒情诗和政论闻名,创作的小说、杂文、游记文学等作品甚丰,对表现主义艺术也有相当的研究。对这样一位既不同于走马观花的外国旅游者,也不同于新闻记者的客人,我们有意识地将大运河的历史、人文和现代化建设等内容融合起来,有机穿插在采访日程中。
在常州,我见到了贝尔格,略显稀疏的金色卷发和“马克思式”的大胡子让我一眼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但那双蓝眼晴闪动的光泽一下子就让人感觉到他的睿智和激情。我热情地称呼他“贝尔格先生”,“不!不要称我先生,你应该知道,我们是同志”。贝尔格刚才的微笑变成一脸的认真。在中国,“同志”的使用频率已越来越低,除非是特殊的时刻和严肃的场合。呈流行趋势的正是“先生”“女士”这些消逝已久的称呼。想不到一个外国人竟然这样执著,真让我心头一热。
汽车由常州去镇江没有直接进入市区,而是先去新建的大港港区,乘港务局的快艇溯江而上。这是贝尔格平生第一次见到长江并航行在长江之上,镇江4天的采访以这种方式开始,让他兴奋不已。快艇驶向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只见茶色的江水与素练似的运河水渐渐融合,江上的舟、河中的帆,穿梭争流,江南运河连接长江的枢纽工程谏壁船闸近在眼前。“在欧洲,一提起中国的大运河,很多人就像着了魔似地激动……世界上很少有这样伟大的工程,1000多年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贝尔格端起照相机兴奋地说。我知道,德国的基尔运河虽然沟通北海,是波罗的海的交通要道,但它毕竟是近百年前才开凿的,长度也不足100公里。在京杭大运河面前,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了。
二
大概因为彼此是“同志”关系,贝尔格很少拘泥于主宾之间的客套和矜持。面对焦山碑林六朝至清代的一方方碑刻时,他眉头紧锁,我以为他识些汉字,在真草隶篆中看出点中国历史兴衰的奥秘,未想到他是对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很有看法:“这些碑刻最早的比德国历史上的法兰克王朝的年龄还大,太珍贵了,不用玻璃罩起来的后果是很可怕的……”直到时任市文化局分管文物工作的副局长刘昆告诉他,碑林保护方案已制定好并将付诸实施,他的目光才从碑林长廊里的黑白色调中移至庭园斑斓的秋叶间。
贝尔格看到金、焦二山正修复千年古刹,热情赞扬宗教政策确是落实到寺庙里了。登上金山楞枷台,只见波光山色、亭台楼阁都被夕照辉映得金灿灿的,充满了诗情画意,贝尔格风趣地对迎候他的慈舟法师说:“这样美丽的地方,连我也想来当和尚了。”
贝尔格是莱比锡大学60年代的历史学博士,对大运河沿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风俗民情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环境幽雅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贝尔格与著名蚕学家吕鸿声所长倾心交谈。他说:“丝绸是民德人民喜爱的珍贵物品,我一定要把这个著名的蚕桑研究中心介绍给他们,因为从古到今,丝绸之路都是一条友谊之路。”无论是在千年古渡遗址西津渡和梦溪园、北固楼等名胜古迹,还是在店铺林立、顾客盈门的大市口商业区,他流连忘返,边看边问边记。贝尔格以行家的眼光参观镇江博物馆“馆藏古代生活艺术文物陈列”,认为这种分专题的陈列,改变了常见的编年体的展陈方式,足以证明镇江文物资源丰富。他驻足于南朝陵墓石刻图片前,倾听馆长陆九皋讲述这一古代艺术瑰宝,表示今后如再来镇江一定要到实地观赏。
这位来自东欧的客人在镇江发现许多“吃”的方面的“新大陆”。在品尝了百年老店宴春酒楼的水晶肴蹄、蟹黄汤包后,贝尔格说:“这是到中国后最值得回味的一餐早点。”吃焦山华严阁的素餐,他说:“由此理解了江南的饮食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在恒顺酱醋厂的会客室里,他听了关于镇江香醋有健身作用的介绍后,大为惊奇。贝尔格谈到欧洲迄今主要食用的是一种白醋,但这种白醋却不怎么受到富裕人家的喜爱。至于镇江香醋以及它奇妙的保健功效,欧洲的知晓者还不多。为祝愿大运河畔的这枝奇葩早日在欧洲广为飘香,热情奔放的贝尔格端起了放在茶几上的一小杯香醋,与厂长轻轻碰杯,一饮而尽。
三
东方文化的神韵,江南山水的风姿,似乎要让贝尔格沉醉,但他更关注的是大运河两岸正在兴起的改革浪潮,更关注人们现实的生存状态。
坐落于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的谏壁发电厂是上世纪80年代全国最大的火电基地,总装机容量达162.5万千瓦。这原是5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建项目,后国际风云骤变,援建国片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并带走了发电机组的关键部件和图纸。对这段历史,厂长显然考虑到贝尔格的身份,只是作了轻描淡写式的介绍。但是我还是发觉贝尔格的尴尬,当年进口的那台2.5万千瓦的机组仍在运转着,它与10万千瓦、20万千瓦、30万千瓦“中国制造”排列在一起,委实是相形见绌,中国人民在当时及后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贝尔格是无法感受的。但当中国打开通向世界之门时,他发现中国的步伐追赶的已是一个更加高远的层次和一个更加美丽的希望。贝尔格伫立在巨大的“中国制造”前,若有所思地倾听着机轮发出的轰鸣声……好一会儿才对我们说:“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某些问题,我有了理解。你们其实在开拓另外一条大运河呵!”时任镇江市长的高德正会见他时,他说:“现在才理解中国江南之所以这样生机勃勃,是因为得到了江河长流的灵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要写中国发展所不能离开的有用的人。”
贝尔格每天晚饭后回到房间,都将白天参观的内容再作回顾,对一些现场未记下的東西,再补写在采访本上。有天早晨,他对霍勇和我说,前一晚写到半夜,竟伏在写字台上睡了一会才醒来。
四
这位洋同志虽是多才多艺的名人,却没有一点派头。他采访用的圆珠笔是当时几毛钱一支最普通的那种,一台相机也是旧的。按照规定,贝尔格在下榻宾馆的用餐标准比我们陪同人员的要高,因此我们与他几乎都是分开就餐的。他希望与我们同坐一桌,说分开坐让他脱离了中国同志。
临行前的晚上,他一定坚持自己花钱买了瓶“洋河大曲”,招待我和市外办的青年译员刘玉录,还有当天陪同参观的市园林管理处副处长石炜,他特别强调:“请驾驶员同志一起参加。”席间谈到一同来华也在外文局工作的妻子和在北京上幼儿园的儿子,脸上带着幸福的笑意。谈到远在故乡的亲人,他的语调变得沉重起来:“最让我不安的是哥哥,因为他的信仰发生了变化,已经去当了牧师……”
分手的时候,我有点郑重地道了声:“贝尔格同志,再见!”还紧握了下他的手。因为在平时交谈中,他知道我爱好写诗,说:“小赵同志,别忘了写首诗给我,关于大运河的。”不过,未待我的诗寄赠他,他邮来一本他的抒情短诗集《简单的句子》。不久,从省委宣传部外宣处的工作简报中获悉,霍勇来信称贝尔格对这次沿大运河采访非常满意,回京之后,持续几天整理了笔记,已制定了写作计划,还考虑到这本书应是图文并茂的形式,内容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
贝尔格离开江苏两年后,也是金色的秋天,他的德文版著作《天上银河,地上运河》由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相当于中文33万字,第一次印刷8700册,主要面向德语国家。该书在法兰克福国际图书节上颇受欢迎。回国休假的贝尔格,在基彭豪尔出版社举行的读者座谈会上介绍了写作该书的经过,接受了东徳各大新闻媒体的采访,并亲自到广播电台朗读书中部分章节。东德一次性订购的6000册很快销售一空,希望重印或再版。外文出版社考虑将该书译成英文出版对全世界发行。
1988年底,外文出版社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及新闻发布会,祝贺贝尔格撰写该书出版和发行成功,为一部书举行这样的活动,以前在外文出版社是少有的。
《天上银河,地上运河》不是一部普通的游记,贝尔格匠心独运,以生动、诗意的笔触,真实、形象地展现古老大运河的灿烂历史、深厚文化、经济发展、美丽风姿等,描绘了运河两岸人民的创造精神,从江苏改革开放近10年的成果反映出中国的快速发展。对面临的一些难题如何突破,书中亦有思考与展望。就连书中每个章节的标题都对读者散发着诱惑力,如:“中国文化的格局”“丝线的力量”“宝塔——运河边的指头”“天堂问题”“纸上的世界(剪纸艺术)”等等。描写镇江的这一章的标题是“神奇的山峰”。为增强直观感,这部书配有116幅彩图,40幅黑白图、示意图及地图。其中许多图片是贝尔格一路拍摄的,唯一有他自己形象的一幅是在谏壁发电厂的留影。
当苏联东欧的局势山雨欲来风满楼时,贝尔格的任期已到,该回国了。这时,我对贝尔格的命运真的担忧起来。那年冬天我从北京获得信息:两德统一后,贝尔格任职的出版社从国有性质迅速变成了私有。好在贝尔格因其自身的才华和人品仍赢得了员工的拥护,他拿出包括稿费在内的所有积蓄成为出版社最大的股东。贝尔格从无产阶级的“同志”几乎一夜之间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版商,大概是他始料未及的吧。后来,出版社房产原产权拥有者找上门来索要房产,并且到法院打起官司。如原房产主胜诉,贝尔格就再无回天之力……此后,有关方面告诉我已与贝尔格失去了联系。
10多年时光流逝,我早调离原来的单位,意想不到与贝尔格因为大运河久别重逢。那是2001年春和景明时,贝尔格应江苏省新闻办公室的邀请,从德国来到中国,仍以大运河为轴线,用一个外国重访者的视线再写一本书,反映江苏新的发展、变化。他在南京大学一位德语老师的陪同下,抵达镇江采访的当天晚上,市新闻办公室主任陈春鸣约我与他餐叙。我写的诗《走向大运河——给贝尔格》和散文《贝尔格同志》先后刊登在《雨花》杂志上,多年来因不知他的地址无法寄出,终于有机会当面交给他,只不过一见面打招呼时,我将当年的“贝尔格同志”改称为“贝尔格先生”了。
(责任编辑:吕文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