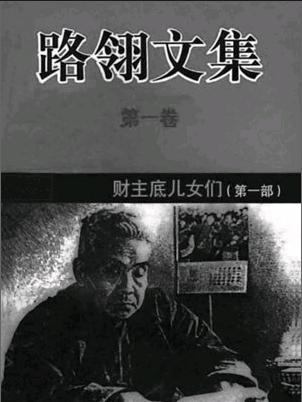


“文革”结束以后,社会各个领域的变迁也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在这个阶段,文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先后成为文坛主流。
在80年代的作家队伍里,年轻的一代纷纷登上文学舞台,老一代的作家虽然还有人在从事创作,但作家队伍的分化很大。并且在80年代文学界通过非政治的因素对作家队伍进行重组。许多作家的创作已经很难再引起文坛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中老年作家来说,就面临着一个转型问题,转型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文坛对其的认可和评价,广而言之,还关系着一个能否被写进文学史的问题。而被写进新时期的文学史著作,无疑是对其创作的一种权威“认可”。在当时的文坛,转型成功的中老年作家,比如汪曾祺,就迎来了一个创作的高峰,获得了文坛的一致好评,像《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成了新时期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当然,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中老年作家仍然在从事创作,他们也对自己的创作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引起文坛的关注,但是,这时候的文坛已经对他们那种显得“陈旧”、“过时”的作品很难产生兴趣,所以就有了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晚年现象”。这里的“晚年现象”并不单纯针对生命的晚年,更主要的是指一种在作家晚年创作的,但是显得比较“陈旧”,已经失去轰动效应的作品。比如路翎,在进入80年代以后,他虽然仍在从事创作,但已经难以进入文学史的叙述。他的创作试图和时代一起“合唱”,却被当时的时代而忽略,最终只能归之于落伍,自言自语。
晚年的路翎經过了几十年的规训和惩罚之后,在文学上被一再强调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这些东西已经深入他的灵魂中心,紧紧扼住了心灵做任何自由思想的可能。晚年路翎虽然身体走出了监狱,但他的心灵却永远留在了那里,受着喷水与喷烟的告诫与惩罚。二十多年的监禁生活,不仅驯服了身体意义上的路翎,使他中规中矩,丝毫不敢做出反抗的姿态,稍有不慎即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同时作为思想和精神意义上的路翎,从五十年代被捕后,被一遍遍地要求改造自己、彻底地毫无保留地检讨和反思自己。尽管八十年代改革春风步步吹彻神州大地,文学界也纷纷发出新的声音,但对于路翎来说,他在写作中一步步失语。所以,在路翎晚年留下的少量诗歌和回忆性文章虽然可以窥见路翎真实的经历和心态,但绝大多数写作都与真实的路翎是分裂的,虽然当时已没人要求写什么和怎样写,但路翎已不可能走出这种画地为牢的创作状态。在现当代作家的遭遇中,路翎虽然看似具有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其实路翎的一生最具有代表性,也因此具有普遍性。
其实,在言及“说”与“不说”问题时,也涉及别人对待路翎晚年创作的态度上。路翎在晚年从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写作,写作几乎成了他生命中支撑他赤膊搏斗下去的理由。他为了写作,戒掉了多年养成的烟酒,他几乎不和家人说太多的话,他太忙了,他的思绪紧张构思着他作品中的人和事,甚至连一起共患难的妻子也“忽视”了,他晚年500余万字的作品就是在这种状态中写出来的。然而,他创作水平的衰退已是一件不争的事实,他“着力追逐的是社会公共的主题”,试图以获得时代的认可,融入到整个沸腾的时代洪流之中。但是,“认真说起来,他这样的创作状态基本上是50年代思想的继续,是50年代大干快上轰轰烈烈情景的回声,与时下他的要反映的八九十年代也已经相去甚远”,他晚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野鸭洼》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有好友牛汉的帮忙,但艺术上实在无法达到出版的要求,这部书中的过分粉饰灾难岁月的书写方法已经不是文学市场所认可的,一直到路翎去世,这部作品一直放在出版社,编辑不忍心因退稿而伤害晚年寂寞的路翎,但除此之外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亲人、朋友们在该不该告诉路翎他作品水平的真相问题上陷入了“说”与“不说”的困境。如果告诉路翎,你不要再创作了,你的作品已经不符合当下文学标准的要求了,你的作品艺术性和思想性都不行。那么,对路翎来说,这种真实的话语无疑剥夺了他活下去的理由。但是“不说”,路翎始终对自己的创作抱有很大的信心,他要通过作品来反映这个时代,用曾经政治上合乎要求的语言和结构,来塑造新的时代和人物,他要写“史诗”,他要一部一部地写下去,从最初的每部书十几、二十万字写成每部三十几万,再到一百多万,最后一部小说居然写到了一百九十余万字,他完全沉溺在写作之中,他所做的这种工作其实只是对五十年代文学创作观念的不断重复,这种“蓄意的欺骗”又是多么残忍,它对每一个知情者的折磨不亚于告诉路翎真相。于是,晚年的路翎犹如堂·吉诃德,在文学的道路上一次次地向目标进攻,头破血流,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其实在别人眼中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写作既无法超越自己,也无法超越别人,对晚年路翎用生命一点一滴写就的作品的否定,换言之,就是对其晚年生命价值的无法承认。人的生命注定是有一天要结束的,但像这样无望地结束,对路翎来说,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无法一一细细言说。当然,我们也无法排除晚年路翎对这种情况的些许清醒认识,“以自己生命最后的光和热孕育出来的作品,大多发不出去,这对再坚强的人都将是最沉重的打击。路翎坚韧地承受着,有时他很焦躁。但他表现出来的不再是喊叫,而是沉默。他能说什么呢?又能跟谁说呢?跟妻子说?她已经做了她所能做的。跟朋友说,朋友们都关心他。谁能代替自己写作?这一切怨谁?怨刊物、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对自己也都不错。晚年的路翎陷入了正如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在路翎的晚年创作问题上,朱珩青说,“记得有这样的一个寓言:人们虔诚地向往天堂,也感觉自己在往天堂飞升,只听得天堂的门‘哗啦一声大开,但人们一看是地狱。知道是地狱了,可以赶快往回跑,而路翎却一脚迈了进去,以为进了天堂”,“文革”后,好多作家都“赶快往回跑”,许多人因此留下来一些优秀之作,比如汪曾祺,但路翎却没有办法再回到原先的天地。因为还有一种说法是当你打开一扇门的时候,原先的那扇门会在你身后砰然关上。到了最后,路翎也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据朱珩青回忆,1993年10月,路翎的长篇巨制《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终于创作完成了,路翎允许朱珩青看稿,路翎的手稿是比较特别的,“好多地方被画掉、修改的地方出现杂乱的、粗笔道的骂人话:大狗、小狗、二狗、狗屎、特务之类。陪着我看稿的余明英不经意地拿起一些稿子,也发现了这个现象。她很懊恼:一天天写,鬼知道他写些什么,怎么能骂人?还是真名真姓?这怎么了得?于是,我没能看见路翎最后的这部手稿,很遗憾,但我完全理解余明英的心情。我在写这些的时候,心里是很不好受的。路翎的心太苦了。他的晚年经历着两个路翎的撕扯:一个说,要正面写,不能写阴暗面,要塑造英雄形象;一个说,要写真实,没有真实文学就没有生命。英雄也是人,不是神。两个路翎在心底里,以致潜意识里不断地搏斗,弄得路翎难以招架,于是就出现了乱删乱改,以致骂人的情形。到了后期,路翎的创作已经进入焦灼不能自持、趋于崩溃的边缘了”。于是,从路翎,到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处于一种“说”与“不说”的两难境地,这大概就是一种“晚年路翎式”困境了。
在亲朋的回忆中,年轻时的路翎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在现代作家中,曾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巴金、汪曾祺等人。只是巴金、汪曾祺晚年还能够写作,进入文学史叙述,说他们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毫不奇怪,巴金在晚年留下了《随想录》,汪曾祺在晚年留下了《受戒》、《大淖记事》,有作品为证,他们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是属于晚年的,然而没有人会愿意说晚年的路翎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凡是看过青年路翎的照片和晚年路翎照片的人无不惊诧于这巨大的变化,晚年的路翎基本上不会笑,在许多场合,他都一副木讷迟滞的神情,然而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却有许多欢愉的场合和笑声,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用滴着血的心来一个字一个字来构筑这些“笑的场合”。可能路翎晚年的作品不会引起文学史家们的兴趣,也很少能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面对这五百多万字的作品,可能丝毫影响不了文学史的书写,但是他有可能影响作家心灵史和思想史的书写,文学史从来都不会只是简单的作品的罗列。晚年的路翎究竟在想着什么,他没有说出来,别人大概也无法知道,我们可以理解,在路翎心中,是否当时已经觉得无法言说,此事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作为后来者,真的希望路翎能够言说真实的遭遇和“经历”,并诉之于文字和文学,可能太残酷了。当受难者还能够有能力、有兴趣地娓娓而谈他的经历,其实他并不是受苦受难最多的人,真的受难者,或者由于灾难本身的折磨,或者由于语言和思维的巨大落差,他们其实往往已不会或者不能诉说。真的受难者,要么早就死去了,要么成了路翎这样,他们的遭遇和历史往往是一部无字书。路翎晚年留下的五百多万字的著述,他可能会被人们迅速忘掉,“1955年平地而起的政治风暴,把路翎从我们中间席卷而去。这以后便开始了压抑而惊恐的、流血和流泪的、漫长而痛苦的二十五年。我在绝望而动乱的年月里常常怀念起路翎,为他祝福。二十五年以后我终于重见路翎,但我悲哀地看到了一个神志不清、满面皱纹的老人。路翎是一个强者,他没有死去,没有背叛,他保持着一颗纯洁的心,活到了新时代。但他毕竟是一个被欺凌的弱者,他终于抵挡不住那过于沉重的精神压迫,他的脑神经失常了。作为一个人,他是那么地強大;作为一个作家,他又是多么悲惨!”(杜高:《一个受难者的灵魂》)当文学书写的规训经过了二十多年之后,在神志已不太正常的路翎那里还是表现得那样彻底、那样顽固,虽然没有人再来批评他、指责他,但他在写作时还是念念不忘地坚持着当年的标准,这样说来,我们应该理解晚年的路翎。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