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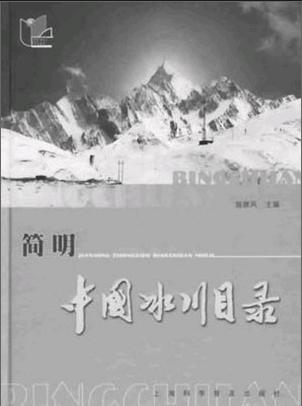

施雅风(1919—2011),江苏海门人,中科院院士。他是地下工作者,白色恐怖下甘冒风险为解放军猎取情报;他是科学工作者,大跃进年代率中国第一支高山冰雪考察队发现并命名了“七一冰川”。他用激情投身冰雪的开发研究;他用理性的科学精神大胆质疑权威。他开创了中国冰川的考察,倡导了中国冰土与泥石流的研究。他是中国的“冰川之父”。
求学立大志
施雅风,1919年3月21日,出生于海门县新河镇(现海门市余东镇启勇村)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5岁即开始上学,由于贪玩加上生病常缺课,他曾经留过一级。1931年秋天,12岁的施雅风进入海门麒麟镇附近的启秀初级中学就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号深深地烙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哥哥施成熙也每周寄来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给他以“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正面教育。起初由于他阅读课外书太多,成绩平平,受到哥哥的严厉批评。到初中二年级时,他真正意识到求知报国的重要,于是刻苦用功读书,到1934年初中毕业时,施雅风地理考了98分,历史得满分,总分名列全班第2名,考上了省立南通中学。
日军的侵华激发了施雅风学习地理课的积极性。从此,他爱上了地理学,并暗暗立下志向,还写信给哥哥表明长大后当地理学家的决心。他一边用功读书,一边积极参加“史地研究会”等兴趣组织,写了《战时中国的生存线》等文章,以5天连载方式发表在南通《五山日报》上,给他很大的鼓舞。同时,他自发地组织同学下课后晚饭前打篮球,大大增强了体质,对以后工作产生长远的影响。
1937年,施雅风如愿考取浙江大学史地系。因抗战爆发,入学后即过上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1938年1月,他随校来到江西樟树镇,看到报上登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招收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消息,他认为国难当头,战地抗日比读书重要,于是独自一人去南昌报名入校,而后在湖南、江西与安徽作抗战宣传,后因未能上战地服务而告退。施雅风于1938年9月回到时迁广西宜山的浙大复学,接着又迁往贵州遵义。从此,他刻苦自励,用功学习,不是在教室听课,就是上图书馆自习,至大三结束已学完大学的全部必修课。在大四一年中,施雅风自带生活用品,坚持每天步行三四十里到野外考察,掌握了遵义市附近地区大量地质地貌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长达6万余字的毕业论文,受到指导教师叶良辅教授的赞许,受到国家教育部的奖励,其简称为《遵义附近之地形》论文在著名的《地质评论》杂志上发表。通过毕业论文的撰写,他初步掌握了在大自然中进行科学考察研究的方法,受益匪浅,为以后从事冰川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走上革命路
在浙江大学求学时期,施雅风不仅亲身体验了师生颠沛流离的生活,更有机会看到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特别是竺可桢校长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像一盏雾海夜航的明灯,启迪师生们追求真理不光是做学问,还要端正政治思想态度,做任何事情,要不怕困难,不畏险阻,要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大学里,进步学生运动蓬勃开展,优秀进步学生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進一步打开施雅风观察和认识旧社会本质的视野,感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没落,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走上民主富强之路。施雅风说:“在浙江大学学习的那几年,我在多方面受到了教育和启迪,应该说是培养我成长的黄金时期。”
在校期间,他还有幸结识了早在193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吕东明。在多次交往及一同参加的调查中,施雅风受到吕东明革命思想的熏陶。1942年大学毕业后,施雅风继续在校读研究生,直到1944年硕士毕业,才来到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助理。1946年,因建设岷江电站需要,施雅风有机会去川西进行社会调查,又一次看到了贫雇农受压迫和剥削的血淋淋的事实,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来到重庆工作后,他更有机会阅读到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还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使施雅风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47年,在国民党统治最黑暗、最残酷的时期,施雅风向吕东明提出入党申请。吕东明对他说:“入了党,你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了,要一切服从党安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能做到?”施雅风坚定地表示:“能做到!”不久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接纳施雅风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在敌人军警特务严格控制的心脏地区干革命,被人称为“把头颅挽在裤带上”——十分危险。有一天,吕东明传达党组织的决定,要求施雅风以中国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公开身份,从事收集敌人的机密情报工作。在吕东明的具体策划和指导下,施雅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缜密细微地做好党外情报对象的工作,向党中央有关部门传递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对敌斗争情报,为解放军顺利渡过长江,以至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一定贡献。
难舍冰川情
南京解放后,施雅风结束了秘密的地下工作。1949年,他参与创办《地理知识》杂志,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务秘书。1953年,施雅风调往北京,参与《中国自然区划》研究任务中的中国地貌区划编写工作,并兼任新建的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1957年6月,施雅风和两位年轻同事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他们穿过茫茫戈壁,翻越祁连山西段,进入青海柴达木盆地。经过寸草不长的戈壁荒漠,施雅风深感祖国幅员广阔,地貌丰富多彩,但严重缺水制约着大西北的经济发展,心中不禁产生一种必须改变现状的强烈责任感。
第一次与冰川面对面,施雅风的心久久难以平静。他躺在蒙古包里,脑海里翻腾着一个问题:“祁连山有那么好的冰川水源,西北却有大片大片的干旱荒漠,这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西北干旱缺水,水、水,无价之宝的水!应该把冰川水很好地利用起来。”一整夜,施雅风就这样思考这个问题。从此,施雅风几十年如一日,爱冰川,考察冰川,与冰川结下难以割舍的情缘。
发现“七一冰川”
1958年6月,那是大跃进的年代,施雅风再次来到兰州。和他一同来兰州的还有苏联冻土科学家道尔古辛。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开发高山冰雪,改变西北干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接见施雅风时问他“你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考察完祁连山的冰川?”施雅风答:“需要3年。”张仲良说:“祖国大跃进,你也要大跃进啊!3年太长,要在半年内完成,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当晚,施雅风就写出报告,第二天报送省委,第三天就批了下来。人员、物资悉数就位。6月26日,施雅风带领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高山冰雪考察队100多人,分6路向祁连山进发。他们首先集中到一处较易接近冰川区的地域进行练兵。7月1日,在祁连山腹地柳条沟地区的托赖山脉,考察队带上水壶、干粮,拄着冰镐,脚蹬长筒钉鞋,登上海拔5143米高的冰川最高点。“整个冰川就像银雕玉塑一样,大家越看越有兴味”。据初步考察和观测,估算出这条冰川的含水量有两个北京十三陵水库大。这一天是党的生日,他们向北京中国科学院发电报报喜,建议把这条冰川命名为“七一冰川”。
冰川考察初战告捷,施雅风发扬“开拓创新、连续作战”的精神,分兵6队对祁连山作进一步深入考察。当时设备简陋,没有登山靴,就穿高帮套鞋;没有轻便的羽绒服,就穿粗布老棉袄;没有精密仪器,就用手摇钻和罗盘;没有完整的地形图,就靠自己观察和航片判读;队员们缺乏考察基本知识,就以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在施雅风带领下,考察队分为6个小分队,对祁连山东起冷龙岭,西至柴达木北山,包括10个冰川区,2个冰川群,125个冰川组,941条大小冰川,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不仅描绘了冰川的形态、类型和分布,而且估计了储水量,进行了人工融化冰雪的试验,最后在施雅风主持下写出了长达43万字的《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冰川考察报告,它填补了我国冰川研究的空白。
为了进一步促进现代冰川的研究,中科院接受了施雅风的建议,于1960年在兰州建立了“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由施雅风负责组织工作。为研究冰川方便,施雅风毅然决定把全家从北京迁到兰州。
为攀登希夏邦马峰打“前站”
1963年,施雅风接到了中科院的一项任务:查明希夏邦马峰的情况,为中国登山队登顶做准备。在当时的国际登山界,希夏邦马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主脊线偏北约10公里、海拔8012米,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征服的8000米以上高峰。国际登山界对攀登希夏邦马峰的活动十分关注。1960年中国登山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之后,下一个重大目标就是希夏邦马峰。
施雅风等一群冰川学家穿行在希夏邦马峰北坡的冰塔林中,每天置身于阳光照耀下的银白世界。冰塔林是低纬度高海拔山区特有的大陆性冰川奇异景观,吸引了施雅风的关注。考察结束后,施雅风和同事们编写了《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对冰塔林的成因做出解释,还对冰川形成、冰川特征、冰期划分、古冰川、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变化等许多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将我国的冰川学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一步。而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登山队于1964年从北坡成功登顶希峰,在中国登山史上书写了又一个辉煌。这次考察,成为1966年开始的珠穆朗玛峰和西藏地区大规模科考的前奏。
“文革”中一怒跳黄河
1966年初夏,为完成成昆铁路定线的任务,施雅风带领十几个同事到西昌地区调查泥石流可能对成昆铁路产生的危害和预防办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单位电报催回,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施雅风1947年入党的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后来又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他以往的科学研究被全盘否定了,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反分子”。施雅风难抑悲愤、难耐凌辱,感到生不如死。在1968年8月的一天午后,施雅风趁监视的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牛棚”,走上黄河大桥,跨过栏杆,从桥上跳了下去。
施雅风想这么高跳下去,必死无疑。没想到一落水,打了一个滚,施雅风浮起来了,这时他脑子清醒了,他想起母亲,想起了家庭,想起了事业,覺得不应该死。于是,他顺着河水游去,河水把他冲到河心的沙洲。追踪而来的人群急切地要下水解救他。他却大声阻止:“这儿水大,不要过来,我回去了,我要活下去。”经过这一折腾,施雅风因祸得福,被“恢复”了工作。
给中巴公路“把脉”
1973年春夏之交,盘桓在喀喇昆仑西南侧巴基斯坦境内的巴托拉冰川洪水暴发,接连冲毁了中国和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一路段和两座桥,通车受阻。中巴双方深为焦虑:原址修复,恐此类事端再次发生;公路改道,无疑耗资巨大。
为科学决策,中巴议定由中方派出冰川考察组进行可行性研究,预报今后数十年间该冰川的变化,以确定是否必须改道。这项具有经济、政治、学术三重意义的国际性任务历史地选择了施雅风。由外交部、外贸部和中科院几家部委联合决定,让施雅风亲赴国外处理此事。1974年4月,施雅风率领一个专家组(成员有王文颖、张祥松、蔡祥兴等)前往巴托拉冰川进行实地考察。
在异国他乡的帐篷里,一张小板凳,一个石头垫起的木箱作书桌,就是施雅风的工作环境。巴托拉冰川神秘莫测、性格多变,它是在前进呢还是在后退?在为时两年的野外工作和一系列复杂的计算之后,施雅风等专家组预测巴托拉冰川还会继续前进,但它的极限前进值仅为180米,最终将在距中巴公路300米处停止前进。冰川前进年限从1975年算起为16年,其后将转入退缩阶段,这一退缩将延续到2030年以后。专家组提出修复方案,公路无需改道,只需变动桥位、放宽桥孔即可。这一安全、经济的修复方案为中巴双方所接受。1978年,这条连接中巴两国的友谊之路恢复通行,为国家节约资金1000万。
挑战权威,质疑李四光
1980年,施雅风发起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的讨论,这引发新一轮争论。李四光早在1931年就提出以庐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地区存在第四纪冰川,当时引发很多人质疑。
1937年,李四光撰写专著《冰期之庐山》对自己多年的第四纪冰川研究进行总结,认为此说不容置疑,他的观点被不少人接受和支持,此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地质界最有成就的著作之一。抗战期间,李四光对鄂西、湘西、川东、贵阳等地考察,在他的带领下,一个学派逐渐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担任地质部部长,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推广得很快,李四光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不少人对李四光的观点不赞同,但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1981年,刚刚被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地学部副主任的施雅风邀请十来个地质专家,包括英国学者戴比雪、李氏学派地理学家景才瑞等人,对庐山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考察。考察后施雅风公开撰文《庐山真有第四纪冰川吗?》,认为庐山等中国东部中低山地没有第四纪冰川,是李四光搞错了。他又联合许多专家学者,对南起广西,北至大兴安岭,西至西螺髻山,包括庐山在内的广大地区进行考察,最终结论是中国东部地区除了少数高山有确切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外,李四光所说的中低山地却没有。针对这个结论,施雅风和其他三十多个研究者合作撰写了60万字《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与环境问题》。
2011年2月17日,92岁高龄的中国冰川之父施雅风驾鹤西去。施雅风是我国地球科学领域卓越的科技开拓者,在冰冻圈科学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冰川事业的创始人,发展和完善了冰川学理论体系,摸清了中国冰川资源家底——中国冰川编目,领导推动了冰雪灾害理论与防治研究,发展和丰富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科学成果,并将中国中纬度山地冰芯研究推向世界前列,亲手创建了天山冰川试验研究站,为中国冰川学体系的孕育与发展起到了基石作用。同时,施雅风还是我国冻土研究的开拓者,我国泥石流研究的奠基人,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冰川冻土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