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2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电视台、中央党校文史资料室、北京人民出版社等先后派员来沪向我母亲了解先父俞颂华生前与瞿秋白、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交往。中央电视台的同志还为我母亲录音录像。由于父亲在世时关于瞿等人的遗闻逸事,对家里人也都守口如瓶,母亲自难详告。隔了不久,母亲说:“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来信来人,要我们家属为先父写一长篇传记,并说:‘党不能湮没俞老先生的革命业绩。”但是父亲生前同家人聚少离多,加之他平时不但极少谈及自己过去的事,而且又不苟言笑,我们也就不敢轻易向他问长问短,所以这一传记任务怎样进行,一时难以落笔。
1986年夏,母亲突患中风,医治无效,也与世长辞,我们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赴苏访德
就从我父赴苏访德说起吧。他留学日本时,就倾心向往马克思主义。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他在张东荪和梁启超的支持下,如愿以偿,偕瞿秋白、李仲武两位,以上海《时事新报》及北京《晨报》特派员名义,同赴苏俄作实地考察。
1920年10月16日,他们三人从北京火车站起程时,我随外婆去送行。母亲怀孕即将临盆,留家未去。耿济之、郑振铎等多人亦去送行。我父亲此去苏俄约待了半年左右,写了许多通讯,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作了如实报道。此后,他和瞿、李两位依依惜别,独自到柏林去了。他的旅俄通讯是在柏林写完的,北京《晨报》连载后,深受读者欢迎,后又汇编成《游记第二集》一书,并多次再版。
在柏林,他又继续写了《柏林通讯》,并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逻辑学、欧美各国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还常到柏林大学旁听,曾听过爱因斯坦讲课。
1921年8月,留德同学会邀请他去作了一次访苏观感的演讲。这期间,他遇到了曾和他一起留日的老同学郭虞裳、笔友刘秉麟夫妇等;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如朱家骅、吴经熊、金井羊等先生,也认识了朱德。德国总统兴登堡会见了他。离德后,又游历了欧洲各地,并两赴法国巴黎。在巴黎,他认识了周恩来。
那时他写给北京《晨报》的报道,是计稿论酬的。他唯一固定的薪金仅靠上海《时事新报》提供,经济来源渐生困难。1924年春,资助他的张东荪离开了《时事新报》,受此影响,他不得不搭船回到久别的上海。途中他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译述了德国斯登堡著作《柏拉图政治教育学说今解》,同年8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海外归来
1924年初,父亲终于从海外返回上海。记得在1928年的一天,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钱智修(字经宇),前来面邀相帮编务。父亲进了《东方杂志》后,又先后兼任了沪江大学等校的教授。在我9岁入培成女校读书时,母亲生下了我弟彪文(已于1957年去世),加上父亲广交游,家用渐增,母亲就经人介绍,也进了培成女校初中讲授语文课。
父亲过去撰文,署用“澹庐”笔名为多,进《东方杂志》后,发表了许多国际问题的文章,均署名为“俞颂华”。于是声誉鹊起,被认为“国际问题专家”。在该社,他和同道胡愈之、武堉干、黄幼雄等抵掌论文,成为莫逆之交。

主编钱智修自离社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后,特来信相邀,许以监察委员,月俸大洋600元。父亲不慕荣利,复信谢绝,仍当《东方杂志》编辑。因他兼课,《东方杂志》社的月薪总是被七折八扣,只剩百元左右。商务总经理王云五要他主编《东方杂志》,他不愿将老朋友的“主编人”位子取而代之,借故推辞,仍居编辑之职。王云五就改请胡愈之为主编人。
1931年,上海“中社”创办了《新社会》半月刊。该刊从第二期起,主持人李孤帆请父亲兼任主编,月薪50元。父亲接任后,开辟稿源,革新版面,主张革新政治、抗日救国,使它在当时的沪出版界成为颇有影响的刊物。同年年底,我家搬到了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邻近闸北宝山路中兴里一楼一底的石库门内。母亲因离校路远,只得辞去了培成女校教务。
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夕,闸北宝山路上居民群相避难。父亲则听到接近官方人士的内幕消息,说是国民党当局已和日方妥协,将闸北地区拱手让人,不会打起来,因之不肯离家。母亲苦苦相劝,一家四口才住进租界外公家中。当夜,遥闻枪炮声,那是国民政府十九路军奋起抗敌,商务印书馆等以及我家旧居都毁于敌人炮火之下。
《东方杂志》不得不暂停发行。其时上海不少报刊也相继停刊。“中社”的《新社会》也难于维持,乃由俞寰澄提出愿意负担纸张、印刷费用,父亲自告奋勇,愿尽义务,继续主编《新社会》,该刊遂得以照常刊行,积极支持和宣传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事迹。
“黄金时代”
1932年5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接受黄炎培建议,邀父亲进馆,筹办兼主编《申报月刊》。当该刊第一、二期发行后,均供不应求而再版,成为当时销量较多的一个大型刊物。
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不少学术专家的作品,还刊登了茅盾的《林家铺子》和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原来取名“倒闭”,经我父亲去信征得作者同意后,改以“林家铺子”为篇名。又约请鲁迅为该刊撰文,当时他用“洛文”、“罗怃”等笔名,在《申报月刊》上发表了多篇杂文。
那时我家已迁到福煦路国民里。其间,瞿秋白到沪隐姓埋名进行地下工作时,曾来探望我父亲,并在我家住过。
1933年5月,《申报月刊》发行了第二本丛书《苏联研究》(第一本为抗日名将翁昭垣著《淞沪血战回忆录》),介绍苏联各方面的新建设。出版后不久,苏联驻沪领事馆举行上海各界招待会,申报馆方面仅我父亲接到请柬。那天傍晚,父亲偕母亲一起抵达领事馆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也在场,相互亲切握手后,郑重地对我父亲说:“我在莫斯科时曾见到过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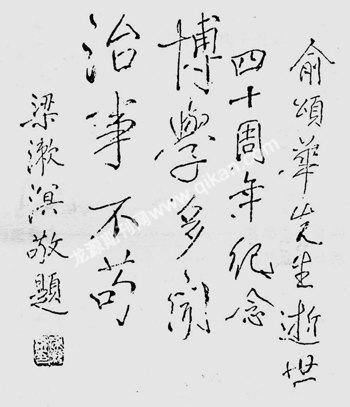
史量才遇害后,马荫良继承《申报》总经理。1936年1月,《申报月刊》改为《申报周刊》,仍由父亲主编。这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期刊。其间父亲一度还任《申报》总主笔,仍兼编《申报周刊》。他每天午饭后去报馆编《申报周刊》,然后到《申报》总主笔室办公,到深夜看了大样后,再写一篇社论,至清晨方能回家休息,如是达三个月。后因种种原因,他自动卸去《申报》总主笔之职,专心主编《申报周刊》。
1937年4月的一个早晨,马经理坐自备汽车,先接了《申报》记者孙恩霖后,再到我家来接我父亲,我也跟随他们一起驱车到龙华机场,送别父亲和孙恩霖登上飞机。那时我却一点不知道他们是专程去延安采访,只知道他们是到西安去。
他们到西安七贤庄,由叶剑英去电话和延安联系后,即安排他们搭车到达延安。当晚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父亲一行,谈了8个多小时。孙恩霖到了延安方知我父亲和毛泽东早在1919年主编《学灯》时就已相识了。我父亲带去照相机,摄下了许多照片,有的是和中共领导人的合影,还有拍摄的肤施(即延安)城墙的照片,城门两侧“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大字标语清晰可见。后者刊载在1937年5月9日出版的《申报周刊》封面上,而中共领导人的一些照片,新闻检查机关不准刊出。这些极其珍贵的照片,因八年抗战离乱,未能保存下来。
父亲和孙恩霖回沪后,即以“本报记者”名义联名写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报道,后因新闻检查机关的阻挠而未能在《申报》上刊出。于是父亲以个人署名,以游记形式,又写了一篇《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刊载在1937年5月23日的《申报周刊》上。这篇通讯之所以刊出,是父亲先向邵力子请示通过的。但是负责新闻检查的陈训畲,又请出潘公展亲自到《申报周刊》社和父亲“协商”。父亲那天回家后对我们讲:“我同潘公展吵得面红耳赤,我不许他来删稿,但结果还是删去了一些重要内容。”可是这篇报道仍向读者介绍了陕北根据地的许多真情实况,并指出在延安看到了国难危重中的一线曙光。父亲还说:“我前几次曾去湖北、四川等地采访,到处见到的都是官富民穷;唯有延安的领导人,都是军民同甘苦,毛主席吃的也是黑面片。我看,将来在国内取得最后胜利的,必是共产党。”
流离颠沛
1937年“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后,父亲向马荫良建议到汉口去发行《申报》汉口版。一天他回家来对母亲说:“日本报纸上说我俞颂华是抗日分子。我预料上海今后即使租界地区,也将为敌人所控制,我就要到广州去了,帮胡文虎创办《星粤日报》后再说。你们去不去,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们母女商量后,决定全家都去广州。
其时,先已到广州并将任《星粤日报》副总编辑的孙起孟,已将筹备工作办得基本就绪了。但因日机连日轰炸,报纸无法出版。孙起孟等由粤汉铁路赴汉口,我们几个搭船北上,于10月初到达汉口。全家居住在俞寰澄伉俪家中,他家待我们亲如骨肉。到汉口后,父亲就着手《申报》汉口版编辑部的筹备工作。
同年年底,南京沦陷,汉口吃紧。寰澄先生设法先把两家家属一起送到桂林。想不到父亲因为和筹办《申报》汉口版的负责人意见不合,1938年春,随寰澄先生也到了桂林。
晚上,他向我母亲说,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已由南京迁到湘西芷江,该校新闻系教授马星野来信要他去该校任教授,并和新闻系学生一起编《芷江民报》。接着还说:“该校是国民党的党校,我是无党无派者,马星野在南京时曾屡次来信要我去,我都未同意;这次你看,我去呢还是不去呢?”这是我父亲一生抉择就业时和母亲唯一商量的一次。母亲看了马星野的来信,情意恳切,信中称父亲为半师半友,就说:“我们不能全家总是依赖寰老生活。我想,你最好带了湘文先去政校试试看,我和彪文暂时仍留在桂林如何?”父亲就带了我于1938年春搭广西省专送画家徐悲鸿的轿车到了长沙,之后我们就到芷江去了。
一到芷江,该校实际负责人陈果夫大摆筵席,宴请全校教师,硬把父亲推到首席。以后,除请他任新闻系教授并和学生们一起办《芷江民报》外,还为他设了一门各系学生均可选修的逻辑学课程。
同年暑假,政校将迁重庆南温泉。马星野派人送我到长沙迎接母亲和弟弟,母亲和弟弟则由建国后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江东平陪同到了长沙;接着,父亲来电要我们暂留长沙,马星野则又来电叫我敦促“俞师母”即去芷江。我们当时进退两难,最后还是决定去芷江。因此父亲一度动辄大发脾气,也不讲清情由,想来是我们打破了他的什么计划。接着,我们随校到了重庆南温泉。
1940年暑假前,父亲终因在该校不合心意,便只身先飞香港。母亲变卖了一些首饰,随后带了弟弟也飞到了香港。我则因在复旦大学尚未毕业,未能同往。
母亲到达香港时,父亲已担任夜报《星报》的总主笔。他到机场去接她们时,见到孙科同机到达。以前两人曾有过接触,此时孙科不复相识,父亲亦不去打招呼。回到报社,父亲当夜就发出了“孙科由渝飞港”的独家新闻。孙科这次到港,对外是秘而不宣的,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到报社责问,后因为《星报》的后台是孔祥熙,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数月后,父亲带了母亲和我弟弟去新加坡任《星洲日报》总编辑。他每晚看了校样后再写一篇社论,鼓励侨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胡愈之随后也到了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笔政。两报原先时常互不相容。《星洲日报》副刊主编郁达夫曾在朋友面前盛赞我父亲和愈之先生是两个“大人物”,说是自从这两位老朋友分别接办《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后,两报就不再互相攻击了。岂料父亲在那里工作了9个月,当局命《星洲日报》把我父亲辞退了。1941年9月父亲只身去香港。留在新加坡的母亲和因病住院的弟弟,受到各方面的照顾。女作家李葆贞向英政府为我弟弟争取到了免费住院治疗。郁达夫向报社交涉到一笔父亲的遣散费交给了母亲。愈之先生其时的未婚妻沈兹九女士介绍我母亲到中华女中任教;还有一位陌生妇女到母亲家中,放下一百元叻币也不留名姓;父亲的政校学生周开仁、开坤兄弟俩也给了资助,母子两人得以维持生活。陈嘉庚、胡愈之两先生都曾向我母亲说过,新加坡若吃紧时,可带同我的母、弟,一起避到南洋群岛去。
父亲到香港后,原拟应其学生之邀,往泰国曼谷办《侨声报》。因在香港遇老友梁漱溟,定要他留港任《光明报》总编辑,黄炎培又请他和俞寰澄一起兼编《国讯》香港版,所以就留在香港了。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父亲和母亲音讯隔绝。新加坡即将沦陷时,母亲带着足疾尚未痊愈的弟弟,和刘尊棋夫妇、陆诒先生的夫人和女儿,长途跋涉经缅甸由滇缅公路,到重庆和我相聚。
香港沦陷前,遭到敌机的大轰炸,《光明报》总经理萨空了在永安街16号租到一间空屋,硬把父亲和军事记者羊枣(即杨潮烈士)拉去避难。过了几天,又把父亲的老朋友邹韬奋也送去。三人同处一室,席地而卧,白天谈论时事,一日三餐,由羊枣夫人煮熟后送去。过了些时,该处四周也遭轰炸,羊、邹两位只得他迁,父亲则到跑马地住在寰老家中。寰澄先生后来在悼文中说:他们同伏于飞弹重炮下时,父亲说:“吾人所重者,志节。身命土苴耳。今其试验时矣。”
香港沦陷后,寰老去沪;父亲则乔装为商人,在我弟弟的友人店中当司账员。后打听到我母亲已到重庆,才于1942年春,仍乔装打扮离港辗转至桂林。
生前预言
我母亲总以为我父从香港脱险后,将会到重庆的,想不到他到了桂林,《广西日报》社长黎蒙请他任该报总主笔,他就留在桂林了,并帮助科学公司编辑丛书。1943年,他又不见容于国民党当局,黎蒙挽留他不居名义仍在该报工作。据父亲生前说起,那时也有一位素昧平生的人,送给他一笔款子,他坚不接受,那人才透露:“这是党要我来送给您老的。”父亲以“无功不受禄”,还是婉言辞谢了。
接着,衡阳《大刚报》社长毛健吾亲自到桂林,聘父亲去主持《大刚报》笔政。毛健吾和编辑王淮冰、严问天等均以师礼相待。其时父亲身体已虚弱不堪。1944年,日军发动了湘桂战争,衡阳撤退,他才又和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同仁,回到重庆,重和家人团聚。
黄炎培知道父亲到了重庆,就和杨卫玉同来邀他住到中华职教社的张家花园宿舍内,主编《国讯》,父亲欣然允诺。
抗战胜利后,张东荪从北京燕京大学飞渝,担任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临时秘书长。在重庆,北京派来了师生为张庆贺六旬寿辰时,父亲由我弟弟搀扶着前去祝寿,坐在不受人注意的角落里。周恩来等见到父亲后,就到面前问候,父亲才站起来和他们一一握手。他回家后,不吭一声,这情况是彪文弟告诉我们的。
这期间,位于四川壁山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陈礼江,到张园聘父亲去创设并担任该校新闻系系主任。父亲以体弱辞谢。陈院长说是请他挂个系主任的空名也可以。他答应以后,却时常不顾长途汽车的颠簸,去壁山办理系务,并仍主编《国讯》。
1946年春,父亲和我弟弟彪文先飞上海,我们随后也复员到沪。他那时感到白色恐怖严重,有的报社要利用他的“无党无派”,请他去办报,他一概谢绝。此后常常由沪前往已迁到苏州的社教学院主持系务。母亲和彪文弟则在上海,分别在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工作。我先生葛思恩亦在社教学院协助系务,并任新闻系教授,我则在常熟中小学校里教书。
1947年暑假,我到苏州陪伴父亲。因为校方要开除新闻系的进步学生,常见他拄着手杖,去向学校当局交涉。回宿舍后,就气呼呼地向我说:“国民党真是倒行逆施,不长久了!你现在把自己充实充实,新社会到了,需要人才而不是奴才。”他要聘刘尊棋等进步教授,校方又不予批准。为此他忧愤交加,不数日,肺病转剧,连日大量呕血。
常熟学校即将开学,我不得不回到常熟,但总是心神不宁。父亲呕血后,母亲常在星期六到苏州探望。是年10月10日,刚好是星期六,母亲依旧前去。不料第二天上午10时许,长途电话打来了,说:“俞先生在是日上午10时病故了!”我们慌忙奔丧,我弟弟随后也赶到。那天寰澄先生专到苏州来探望我父亲,突闻噩耗,悲怆不已。这年,父亲虚龄仅55岁。
我们赶到苏州殡仪馆,母亲边哭边讲:“我昨天下午到达时,他还向我说:‘我一辈子东奔西跑,常常顾不到你,很对不起你。又说:‘共产党快要到了,新社会就将来临,我怕见不到了,也不能按我原定打算,带了第一批毕业的新闻系学生和你再到南洋去办报了吧?”母亲又说,看来他没有料到第二天就撒手西去,连一句遗嘱也没有留下。大家听后,肠断心碎,悲泣失声!
先父逝世的噩耗传出后,驻苏州的《大公报》记者,发电到上海报社,翌日起就广传各地,解放区报纸上也刊出了父亲逝世的消息。特别是上海《大公报》上,接连刊发了父亲好友悼念他的文章。苏州《大江南报》、上海《人物》杂志都出了纪念特刊。学生们筹备了两周,在社教学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无锡江苏教育学院也举行了追悼会。
社教学院发给父亲六个月的薪金,我们在苏州灵岩山麓的乐园公墓内买了一块坟地为父亲安葬。落葬那天,许多学生同去送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