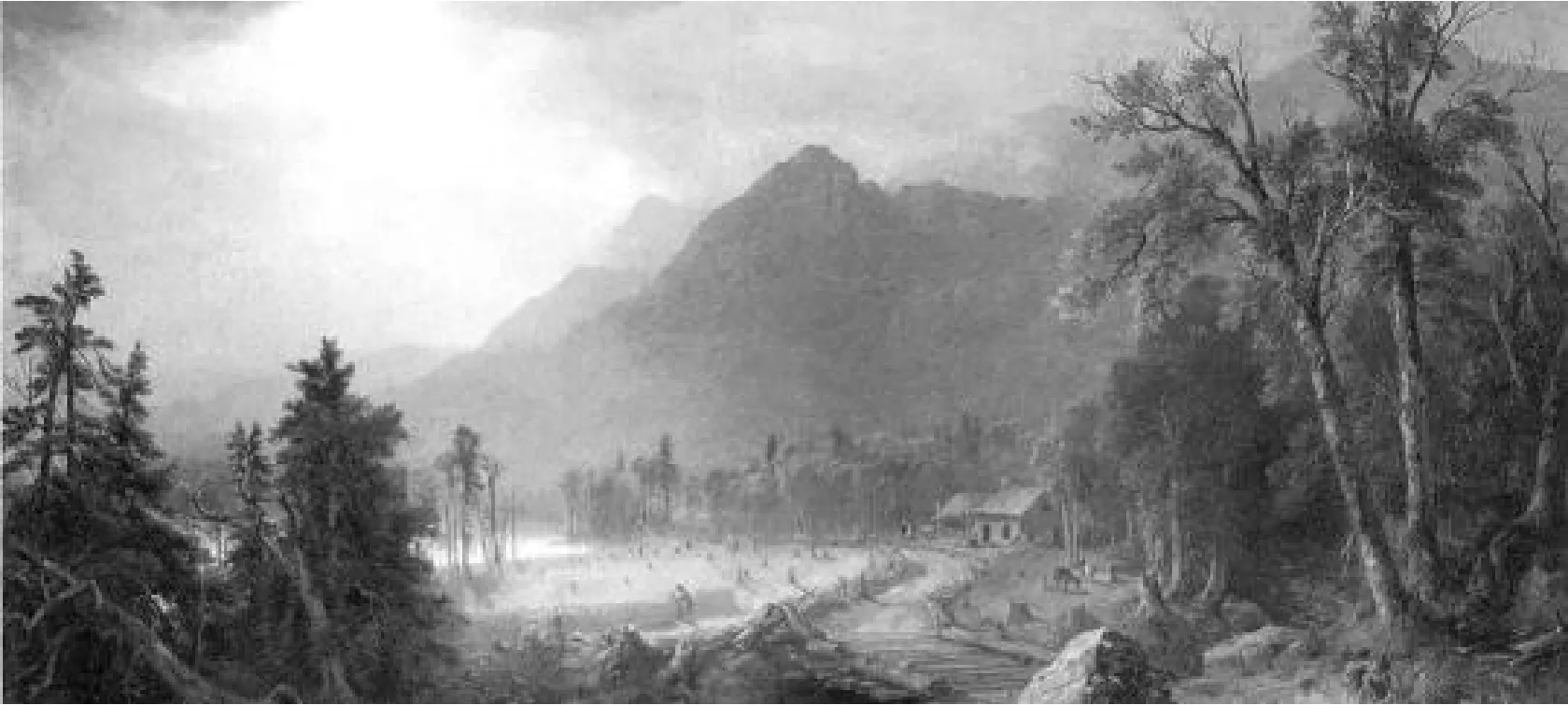诗情与历史的对话
□张清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从东晋以来的一千四五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化的重心已经渐渐南移到这里了。这不是夸张,相对于北方作为政治中心,南方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读一读唐诗宋词,那些典范的景致,无不与这块土地有关。烟雨楼台,人文汇集,这里不再仅是迁客骚人失意江湖的地方;春花秋月,朱颜豪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一个民族的精神烙印,都与这块土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人面桃花,惊鸿照影,这里积淀了太多的诗情画意,衍生着太多的浪漫想象,也留存了太多的凄婉与伤悼……毕竟美丽的山川与感伤的故事总是结伴而行。在现代中国,这里也书写了革命的风云际会,志士仁人的悲欢离合,启蒙思想者的喋血途程,没有比这里更适合这样一部书的诞生的了——《文化浙江》,这是一个有着丰富思想和诗意蕴藏的题目,一个想象和历史交汇、艺术和文化碰撞的绝好的吟诵对象。诗人柯平正是靠了他的敏感、智慧、丰厚的艺术文化修养,在这一广阔的思想空间里,展开了他的诗情与历史的对话,艺术与诗性的想象。
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诗作,《文化浙江》可以说是一个包含了文化地理、人文风物、历史传统、民俗遗迹、物产旅游等等方面的综合的课题,要想驾轻就熟、收放自如地将这一切融合起来,相当不易。它对写作者的要求可以说是苛刻的,因为首先它必须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诗人不可能完全按照主观的想法去进行演绎,他必须循着一个历史与地理文化的线索,按照各种给定的材料,去挖掘其中的人文意义和精神内涵,而且还要进一步将其升华为诗歌艺术,而不只是文化和考古的报告,抑或旅游观光的说明资料。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调和能力与“妥协”的功夫可以说是运用得淋漓尽致,对宏大历史叙事和个体的心灵性探察的关系、历史之“实”与诗意之“虚”的关系,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因此,读它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次美妙的神游,一次文化的盛筵。从河姆渡文化到当代西湖博览会的开幕式,作者引领我们完成了一次穿越7000年苍茫历史的神奇之旅,一次与众多伟大灵魂的不间断的精神对话。某种意义上,它既是对浙江历史文化的一个集中发掘,也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一次诗意探寻。
在获得了文化的广度和历史的纵深之后,最重要的是完成一部诗歌作品所应该具有的精神深度,在这方面,诗人柯平没有令我们失望,他对众多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的探究和发掘是深刻和感人的,这是一个成熟诗人的最老练之处,他知道只有抓住了人、抓住了心灵性的东西,与历史人物展开生命意义上的交流,才是抓住了最容易出彩和感人的要素。比如《兰亭叙事曲》中他对书圣王羲之的描写,就充满着这样的精神体验与心灵交汇:“就像潜思的蚌王无声下沉到河流深处/当他终于找到真实的自己时/他离周围的世界,距离多么遥远/也许,一生的冰雪/就为了这一刻燃烧/袒腹东床的放任,不称心的官职/世俗的荣耀与俯仰随人/此刻他已经全都忘了它们……”这样的诗篇可以说是真正获得了“咏史”的品质和深度,因为他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唤醒了那些已然沉睡的灵魂。他对骆宾王的凭吊,也充满着这种心灵的关怀,对生命的怜悯,和对历史、胜败、是非、荣辱的反讽和消解:“真的,一个天才诗人/臣服于激情,喜欢用身体写作/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变换角色/一会儿是神童,一会儿又是革命家/……当我在家乡义乌父老的悲痛泪水/与灵隐寺顶逃亡者的风尘倦容之间/反复辨识你一生的行迹/并打算在精神中将它们确认下来/一个激进分子,才华挥霍者的叛逆形象/于是呼之欲出。”这里,个体生命的深度还原了历史的鲜活和真实可感的情景。在《青藤先生小传》中,作者对另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徐渭的描写和表现甚至达到了令人震撼的程度,活画出了这位才华横溢的狂士一生潦倒的命运,他的深渊般的性格,一往无前的悲情和充满创造力的愤懑,简直是一个中国版的荷尔德林:“他一生飞行的目标,究竟在哪里?/……剑上的锈迹,脸上的老年斑/涕泪在风雪中挥洒……//即使患白内障,他也知道国家的病症在什么地方。”
作为一部当代性的咏史诗歌作品,也由于作者的个人气质和艺术追求,《文化浙江》当然地具有了一种“先锋”色彩,这不但表现在语言的陌生风格、艺术和细节的处理方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作者的历史与诗歌的观念上,比如作者对历史文化中的多向性内涵的发掘,其对通常历史伦理的反思与大胆僭越等等,这就使得作品中的诗意不断胀破原有的历史视阈,而获得了新的可能性。比如在《岳坟雪景》中,他就大胆地越出了对历史人物的脸谱化和二元论的简单处理方式,对即使是像秦桧这样的鬼魅化和概念化的人物,作者也将其放到人性的天平上,给予其一丝怜悯——这当然不是对历史大义的背弃,而是对人性深渊的反思:诗人宣称自己要“拒绝两分法,热爱英雄/同时也坚持用手绢/大胆擦去跪像头上的唾沫”。这与其说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举动,不如说是对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一次反思,因为唾弃奸佞可能是容易的,但如何剔除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种种劣根,却是最困难和最重要的简单地将历史道德化,反而会导致一种人性拷问的缺失,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除此之外,作者对传统咏史诗的庄严风格也有刻意的突破,他的《孤山访林和靖》就几乎使用了“后现代”式的诙谐,来处理这个人物;在另外的一些篇章中,他也使用了拼贴叠加等等手法,取得了意外而丰富的效果。
总体上,虽然这部作品还存在着在实与虚的关系处理上的不平衡、在吟咏历史时还有某些概念化的痕迹等问题,但整体的探索应该说是成功的,对拓展当代诗歌的艺术空间应有着多方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