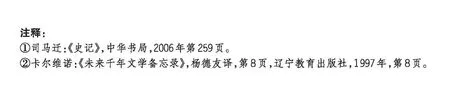野莽一直对古庸国怀着浓厚的兴趣。他常常不辞辛劳地奔走在历史的尘烟里,重返时光隧道,以期解开掩映在庸国之上的神秘面纱,展示它那雄浑而又不失娇美的丰姿。这种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源于他对故乡的热爱,因为庸国的旧址就在野莽的故乡,书写庸国,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为故乡“树碑立传”;另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不断驱使他对逝去的历史进行现代性的反思。他曾以煌煌五卷本的《庸国》,全方位展示了“庸国”之地几千年以来的风土人情和历史面貌的变迁。最近,他又再次以庸国为背景,完成了长篇小说《神鸟》(《芳草》2011年第2期)。在这部小说中,野莽以雄浑而放达的笔调,再次展示了庸国从强大走向灭亡的历史悲剧,并对这一悲剧进行了颇具穿透力的反思。
一
在《神鸟》中,我们看到,虽然处于“礼崩乐坏”的年代,但在庸君身上,先贤们所立身行事的“仁义”作风依然保留着。修订法律,惩恶扬善;不违农时,不劳民伤财,与民休息;不纳妾,宫中不置太医,把医生下放民间,以便他们能更好地为百姓医治病痛;严格执行“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条例。
对外,庸君则“以诚善待天下”,不轻易发动战争,不干涉别国内政,不监视邻国;并通过和亲的方式,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对待不公平的事件,庸国总会仗义执言,甚至不惜出动军队,帮助弱小国家讨回公道。
如果故事就停止在这里,庸君便是一个完美的仁君形象。可惜的是,庸国在庸君的治理下,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这不能不带给人无尽的沉思。在小说中,我们发现,庸国的败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庸君忽视了器物、技艺这些具体的、形而下的东西在保家卫国方面巨大作用。昼鬼精心制作的竹鸦,也即“庸之神鸟”,不但能飞临别国,探听消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声音和图像的方式传送回国,还能感知别人心中的意念,探知人们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昼鬼把神鸟敬献给国君,建议用它去获取别国情报,没想到遭到了庸君的断然否定。庸君认为,刺探别国的情报,就是违背盟约,“干涉对方内政”,如此“出尔反尔,必将遭到人家的当面笑话,背后辱骂。”以此为由,庸君否定了神鸟的合法性存在,禁止昼鬼制作神鸟。
庸君的这些做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仁义之君那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但是,在那个强权战胜公理的时代,权力(权术和谋略)和力量才是主宰一个国家命运的首要条件。因此,当“仁义”与“权术”相遇时,“仁义”显得不堪一击。在善于玩弄权术的楚庄王面前,庸君节节败退。
小说中,作者倾心塑造了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楚庄王形象。他既有吞并天下的雄心,又有满腹的谋略,把“阴阳术”玩得炉火纯青。
表面上看,楚庄王在最初即位的三年里,荒淫无度,沉迷于酒色,宠幸郑姬和越女,不理朝政。《史记》上曾有记载: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①这样的楚庄王,不但欺骗了楚国的大臣和百姓,以至于伍举、苏从冒死觐见,痛斥楚王;也蒙骗了天下人,以为“庸人善战,秦楚莫敌”的威胁消除了;甚至还把最为宠幸的两个妃子——郑姬和越女蒙在鼓里,她们也弄不清楚,在沉溺于酒色和在床上排兵布阵的楚王,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面孔。面对伍举和苏从的痛斥,楚庄王用“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豪言打消了士大夫们的担忧;而面对庸国追讨的战争赔款,他表面上满口答应,承诺尽早归还,暗地里却一拖再拖,甚至称病拒绝接见使者。与庸国不派间谍监视邻国的做法相反,楚王费尽心机探取邻国情报,不但在庸国安插间谍,把能言善辩的令狐冷推进了庸国权力的核心层。还从天下招募能工巧匠,治世能臣,发展壮大楚国的力量。并不惜花重金从庸国招募受到贬斥的若磐,在楚庸边境修筑城墙。为了麻痹和愚弄庸国国君,他把假公主羽许配给庸国三王子子惠,把假玉当成稀世珍宝作为陪嫁品,以此换取庸国的感激,从而免除战争赔款。
当楚庄王的这些伎俩被“神鸟”识破之后,庸君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反而认为三王子子惠私自放飞“神鸟”的这种举动,破坏了盟约,从而用“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条例将他羁押。而楚庄王则不放弃每一个消灭庸国的机会,他分别与郑越两国联姻,赢得了良好的周边环境,然后举全国之力,一举消灭庸国。
这样的结果让人唏嘘不已,这是暴力对仁义的一次完胜,是非正义对正义的一次扼杀。然而,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暴力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存亡的决定性力量。在这种情况之下,仁义可以被嘲笑,被扼杀,正义可以被颠覆,甚至被强者的“非正义”所取代。庸君秉承了“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立身的箴言,把遵从先贤之道视为“本”,这种做法,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庸君用“诚”和“仁”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却忽视了器物、技艺的巨大作用,放弃了对强大邻国的警惕,终于把庸国带入了亡国的悲剧性命运中,这不能不让后人扼腕叹息。在这里,野莽对逝去的“诚”和“仁”的古代遗风唱了一曲挽歌,对中国文化的变形做出了批判性的思考。庸国的灭亡是一个国家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
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鸟》是作者在有限的史料基础之上虚构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借用历史叙事来表达对现实的反思,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方式,所谓“以史鉴今”。但这并不是这部小说成功的标志。《神鸟》真正让读者感到耳目一新的地方,在于它独特的叙事视角。
小说的叙述者是“我”,也即主人公昼鬼。从第一句“安葬师父的时候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开始,小说便奠定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整部小说,就是在昼鬼的讲述之下完成的。有意思的是,昼鬼讲述故事的时候,庸国已经亡国几百年了,作者用这种“后设叙述”的方式,让昼鬼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和反思者。昼鬼这两种不同的身份,为小说文本铺设了一个巨大的张力场。作为清醒的反思者来说,站在几百年之后的某一天,来回望当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但天然的具有了一种批判性的思考,同时也在变幻莫测的世事面前感到了命运的荒诞,一种无可奈何地宿命感油然而生。
从整体上来看,《神鸟》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但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作者又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需要,有意识的进行了视角的切换。如面对庸君的时候,作者采用的是“我”和“您”对话方式,在一种限制性的叙述视角里完成了对亡国原因的探寻,而对于发生在楚庄王身上和楚国的事情,则采用全知性的视角。
我们知道,叙事视角的转变,不但能影响到叙述主体的立场和观点,同时还影响到叙述者对于事物的感知和态度。在“我”和“您”的对话方式中,作者成功的拉近了读者和庸君的心里距离,获得了对庸君的一种亲近感,从而感受到庸君以仁爱为本的巨大魅力。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平等的对话过程中,“我”把亡国的事实一一说与庸君,对庸君的治国理念进行了一番批判,使庸君意识到,一个君王不但需要有一颗仁者之心,还要有胸怀天下的战略眼光。而对楚庄王和楚国所使用的全知性叙事视角,则切断了读者对楚庄王的亲近之心,从一开始,就自然的把他推到了一个接受审判的位置上。
另外,这种“后设叙述”的写作策略,还有效地洞察了和亲所造成的人性劫难。在《神鸟》中,不管是讲求“仁义”的庸君,还是惯于玩弄权谋的楚庄王;不管是实力强大的秦国,还是国力相对弱小的郑国,都采用了“和亲”这种策略,以牺牲女人的方式,或者换取国家的和平,或者为国家的发展赢得时间,或者等待最佳的时机发动战争。
但是,这种政治性的和亲,在“我”看来,不但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和平,相反,它是对女人的个体心性极端蔑视的一种做法,是漠视和侮辱个体生命的表现形式。在君王面前,她们只不过是“生物”般的存在,随时都面临生命的威胁,她们唯有在君王的淫威面前强颜欢笑,才能维系没有自我灵魂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之下,她们柔弱的肩膀上,又如何能肩负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沉重使命?
庸君本来想用和亲来换取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但是,对于像楚庄王这样的君王来说,和亲只不过是他们玩弄的一个政治游戏罢了,女人的生命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与其说和亲能制止战争,不如说它为野心的君王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这样,野莽对叙事视角的巧妙运用,在多重时空,多重叙述的结构张力之下,把小说的审美意蕴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深化了它的主题思想。
三
如果说,“后设叙事”的成功运用把《神鸟》的审美意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意象的选取和语言的使用,则是促使小说成功的另外两个因素。野莽选取了会飞翔的“竹鸦”,即“庸之神鸟”作为揭开古庸国神秘灭亡原因的一个道具,体现了作者对轻与重这对关系的辩证性思考。在小说中,作者借用南山叟之口说出了“轻,即是重,重,愈须轻”这样具有深度哲理性的话。小小的“庸之神鸟”确实有能力担负起使国家强大的重任,因为它能在敌人发动进攻之前就已经探取了敌国的军事情报,庸国完全可以以逸待劳,提前部署打击敌人的策略。如此知己知彼,焉能不百战百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飞翔的“庸之神鸟”还代表着一种活力,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只要神鸟能在天空里自由飞翔,庸国就能发展壮大。而一旦神鸟的飞翔受到了限制,甚至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庸国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可能。遗憾的是,庸君并没有意识到神鸟的重要性,他否定了神鸟飞翔的合法性,甚至把三王子子惠私自放飞的神鸟也射了下来,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宣判了它的死刑。由是,滞重的庸国再也飞翔不起来。
野莽对“神鸟”这一轻盈意象的选取,和卡尔维诺的观点取得了惊人的一致。卡尔维诺对未来千年文学的展望中,给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轻逸”。他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变得如石头般沉重,面对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实,作家们应该用笔努力消除这种沉重感,使世界重新获得一种轻逸的诗性特质。当然,卡尔维诺并不是要求作家们逃避现实,把自己关在一个虚幻空间里自娱自乐,他所谓的“轻”,是指在“严肃的轻”中感受世界的“重”。因此,他特别行赏卡瓦尔康蒂轻盈的一跃。他说:“如果让我为新世纪选择一个吉利的形象的话,那么,我要选择的就是:超脱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学家诗人那机敏的骤然跳跃,这表明尽管他有体重却仍然具有轻逸的秘密。”②野莽选择轻逸的“神鸟”这一意象,正体现了“诗人那机敏的骤然跳跃”。
除了选取轻盈的意象之外,野莽还在小说中使用了一套特殊的语言,寥寥数语之间,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便跃然于纸上。
《神鸟》中人物众多,除了那些重要的人物之外,如昼鬼、庸君、楚庄王、子惠等,还拥有一大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由于小说篇幅的限制,大多数人的活动范围有限,要把塑造这些人物的性格,如果只是从行动上来体现,显然无法做到。这里,作者最大限度的激发了语言的功用,赋予每个人以不同的语言,使他们各自操持一套不同的话语。这样,作者便在他们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
野莽所使用的语言并不具备诗情画意,无法给读者营造出一个诗意盎然的艺术世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独特的语言,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结果。在这里,他不需要描绘出一个诗意的世界,而是要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即便这样,小说的语言也别有一番风味,它带着一股平实的幽默色彩,令人回味无穷。
通过《神鸟》,野莽生动地再现了一个被历史尘埃淹没的传奇古国。面对它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过程,作者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喟叹。在很大程度上,庸君这个人物形象寄托着作者的厚望:他是一个少见的讲求“诚”和“仁”的君王,庸君通过这种柔和的治国手段,使得人们真正享受到了安居乐业的人伦之乐,给血腥的政治添上了几许温情的色彩。然而,当庸君以“诚”和“仁”的方式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放弃采用民间智慧,把昼鬼等人制作的巧器视为非法的东西,将其扼杀,终于把庸国带入了亡国的境地时,又遭到了作者的强烈批判和否定。《神鸟》讲述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但由于作者不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只是把它作为思考的一个入口、一个历史背景。这使得小说脱离了具体历史事件的限制,从而获得了整体象征的效果。因此,它更像是一个传奇,一则寓言,一个警示。庸国的灭亡,对于今人来说,依然有警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