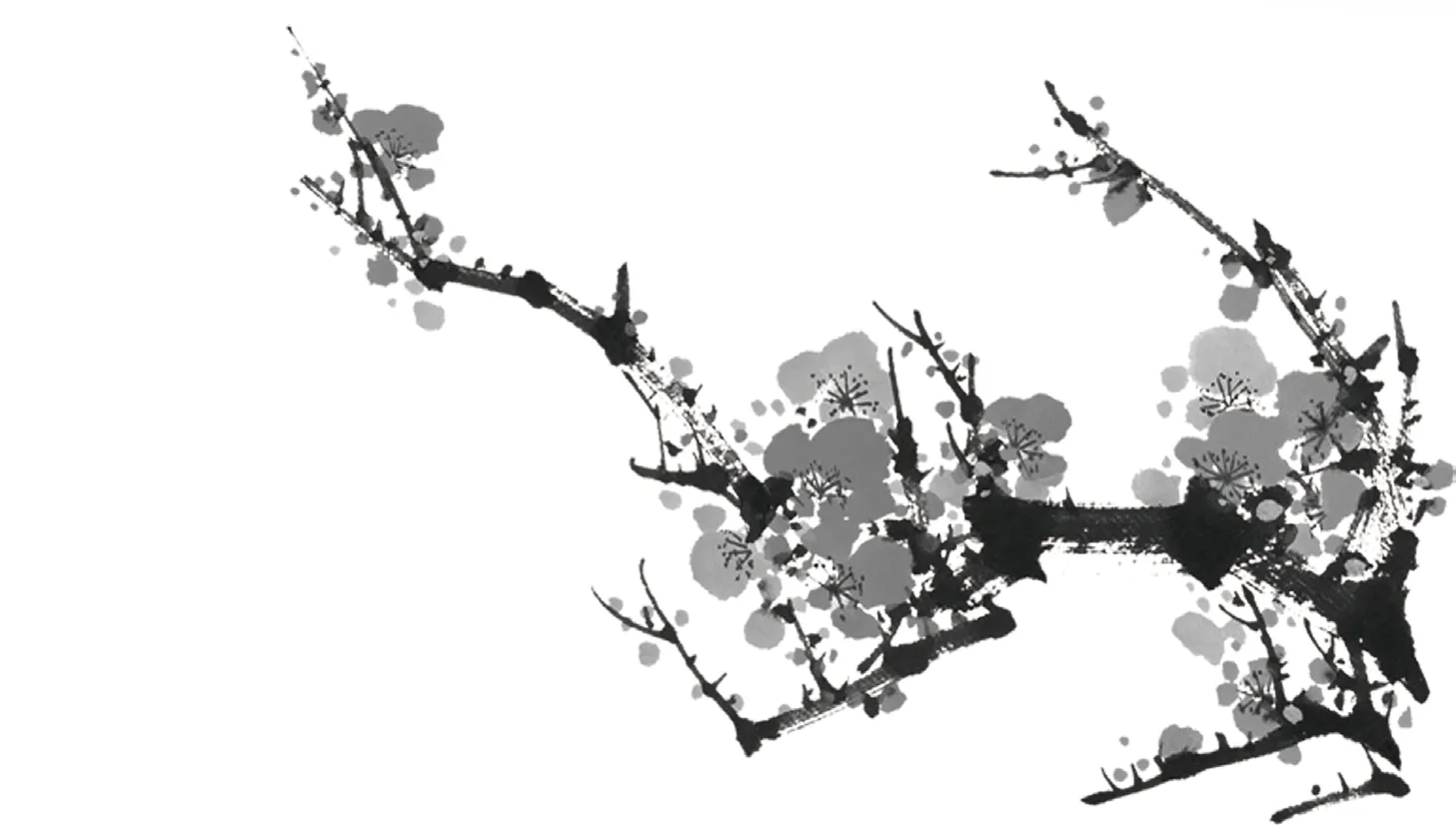我们如何回首往事
王家惠
读罢张金池先生新著《陈光碎影》,便想起这个题目,想借此说几句话。其实这个题目很可笑,回首往事,还需要“如何”吗?怎样想就怎样写就是。可是如果细说起来,也并非没的可说。起码张金池先生这部新著就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真实地回忆真实事件
事件是往事回忆的主体,没有事件的回忆难称回忆。因而事件的真实就成为回忆往事的首要标准。这就要求回忆的事件必须是回忆主体亲历亲闻之事,街谈巷议,道听涂说之事绝不能进入回忆。如今回首往事的著作日渐其多,仅友人赠我的著作就是一个不小的数量,这其间自然有许多进入老年的朋友,来日无多,唯有往事如烟,故而动笔写下来,总结一生,或者仅为娱乐晚年。更有一些三、四十岁的朋友,居然也来回首往事,回忆儿时如何过年,如何上树掏雀,下田扒瓜,等等。这就让人不懂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也许是当今的生活节奏太快,目标太专一,大家都奔着房子、车子、票子去,生活太枯燥,没有诗意,故而到儿时的生活中寻找一点诗情吧。这样的著作未始不好,但是就怕多,一旦写得人多了,你也掏雀,我也掏雀,你也扒瓜,我也扒瓜,就形成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惹人烦厌了。金池先生这部新著没有这种弊病,可说是别开生面之作,他的“往事”主要集中于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这一段,而且笔墨集中于农村集体化这一段,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是“生产队趣事”、“生产大队往事”、“人民公社旧事”,这一段时期还少有人写,故而在取材上就有新鲜感。这三十年的时间,正是他血气方刚的年代,所写都是亲历亲闻,最重要的是他是真正以个人的身份,个人的感受为基点,来回忆那个时代。他是农民出身,当过生产队会计,大队会计,大对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县工商局局长,县政协副主席,今年差两岁七十。他人生的主要经历,全在那三十年间,因此回忆起来就很接地气。他也不回避自己的身份,自己怎么认识就怎么写,这样一来陈年往事就转为新鲜了。比如他写文革当中,上面号召学焦裕禄,公社干部平时下村要背着粪箕子,边走边拾粪,走到那个村办事,就把粪倒在哪个村集体的粪堆上。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插曲,没过多长时间就不实行了。可是他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的始末,分析了这件事的利弊得失。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可算得一篇不错的东西,至少使我们知道当年还有这种事情。可是他由此生发,接着写起毛泽东同志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由他的文章我们才知道,从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发现干部队伍中滋长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因此从那一年一直到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同志几乎每一年都有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而当时中央也据此采取了相关措施,以至于当时的干部队伍确实形成了自觉参加生产劳动的习惯,文中写到:“在农村,不论是县委书记,还是公社书记下乡指导工作,身背一个粪筐,有粪就拾,随手放到生产队里的积肥场。包村干部与民众一起打早战、打夜战、黑夜白天连轴转,在田野里耕播的拖拉机手就有可能是当地的公社书记,在手挎斗子忙着点种,或手拎粪箕子施粪的也不一定是社员。因为当年干部参加劳动是必修课,老百姓掏心窝子的话愿意跟干部说。”我相信这种记述是真实的,因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我没少作为工作队下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这个老传统记忆颇深。我记得吃的第一顿派饭是十七岁那年,到一个村子搞外调,午饭吃的派饭,饭是杂交高粱米饭,菜是熬大葱。杂交高粱据说驴都不爱吃,可是尚可忍耐,惟有那熬大葱,可说闻所未闻,勉强吃了几口就赶紧告辞了。后来当了工作队才知道,各庄派饭大有讲究,村里把村民分了等次,条件好的,好客的,作为第一等,给公社领导留的,次一点的给住村的工作队,最次的留给外调人员,因为这些人吃一顿就走,对村子毫无用处,我就吃了最次一等的派饭。最难忘的是一九八六年,我作为扶贫工作队进驻丰润北部山区一个贫穷村庄,全队就我一个人,住在一个老光棍家里。别的还好说,我最怕干活儿,尤其是农活儿,从小就没干过,更懒得干。可是不干也得装。夏收大忙时节,村干部分了工,我负责全村两个麦场的工作。一个麦场在我住所的前边,一个在后边。我到一个麦场转一圈,往脱粒机里扔两个麦个子,便对老乡们说去那个麦场看看。到了那个麦场往脱粒机扔两个麦个子,又对人说去那个麦场转转,便回到住地,躺在炕上看书,静待中午开饭。后来一位在开滦上班的工人星期日回家,回去上班时遇到正在村外散步的我,跳下自行车笑嘻嘻地说:“我说你这个工作队真会抢镜头啊。”我问此话怎解。他说:“你在这个场扔两个麦个入,在那个场扔两个麦个子,就回屋躺着去了,全庄都知道你干活儿了。”我把脸一板说:“就显你奸啊?你敢说出去,我跟你没完。”他笑嘻嘻地说:“放心,我不说。我不说大伙儿也都知道。”说罢骑上车走了。不过虽然全村都知道我很懒,却认为我懒得很真诚,故而对我印象颇佳。吃饭也很好,中午晚上两顿饭必有酒有菜,我是既来之就喝之,大家认为我很接地气。当然,也不能光喝酒,也需干些正事。比如正在夏收大忙时节,突然停了电,脱粒机不转了。乡亲们急得团团转,却束手无策。我说找个人去公社问一问。大家七嘴八舌,说去了也不管用。我问为什么,他们便对我说事情的前因后果。这个村子位于还乡河上游,邱庄水库的边儿上,过去没有桥,进村出村要靠摆渡,摆渡一次一人二分钱。这一天公社的电工到村子里检查线路,坐摆渡不给钱。本来嘛,人家是公务,又是给他们村办事,免费也应该。可是这个村子的人不干,上去几个人把人家暴揍了一顿。从此公社电工就和这个村子作下仇,每逢大忙时节就要停电。听他们说完,我说,你们把人家惹了,有什么办法?村电工说:“要说办法也有,不过请他们吃一顿饭,把这个事儿平了就得了。”我说就这末简单啊,那什么,你去告诉谁谁家,让他们准备饭,多弄些鱼,再告诉书记、村长,中午都来陪客,带两瓶酒,然后你再去把公社电工请来。村电工听了,欢欢喜喜跑了。然后我对聚在打麦场上的乡亲们说:“你们可别说我大吃大喝,我这可是为你们好。”大家都急着说:“老王你就使劲喝吧,把电通了,比啥都强。”中午大家喝得很畅快,电也就通了。乡亲们对我的评价也很高,说这个工作队很办事儿。当然,我绝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好干部,不过是一个又馋又懒的年轻滑头而已,但那个时代干群关系确实很好,那个时代的农民也确实很好。
由于金池先生写得很真实,故而引起我自己的回忆,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为主要的是,我们从他的叙述中,很真实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对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无比重视。他老人家所设计的国家政权,绝不是过去那种官僚衙门,而是一种新型的,真正与劳动人民心贴心的,真正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新型政权。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也许可以与时俱进,但其精神实质却应该是万古不移的,只要共产党主政,它就应该是我们永远遵循的准则。
真实地回忆真实感受
由这里看,真实,是我们回首往事时的基本前提,虚假的,造作的所谓回忆,是对于历史的歪曲。是一种对于历史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当然,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据说胡适先生也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很对。历史是由人叙述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具有不同的阶级地位,社会身份,具有不同的思想、意识、阅历、观点,因而面对历史,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认识,因此历史的叙述就难免打上不同的烙印,就难免有不尽真实之处。因为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哪个人也无法完全还原历史的现场,对于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看法,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完全否认历史的真实性,完全否认我们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这里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真实地遵循自己的内心记忆,不为当下时风所干扰。所谓真实的记忆,不仅是具体事件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当时当地的真实感受。这是比事件记忆更为重要的记忆。比如对于“文革”时期的叙述,就眼下所见,大多印象是孽火遍地,浊浪掀天,群魔乱舞,惨剧连连。“文革”中的中国就是人间地狱,故而人们称其为“一场浩劫”。而回忆的主人公也大抵是当时就对于“文革”有着绝大不满。可是据我所知,当时的人们对于“文革”不满的并不很多,绝大多数人是无比拥护,积极参与。可是在张金池先生的叙述中,却能够遵循他自己的记忆,不为时下流行之风所动,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好的,有坏的,好的不溢美,坏的不回避,故而形成一种很端正的文风。比如他在书中写了文革中的种种怪现象,写了文革中干部作风的败坏。比如一位公社书记晚上喝多了,跑到一个大队的民兵枪库里,扛出一挺轻机枪,对着村里的鱼塘疯狂扫射。突起的枪声惊动了七里八村,人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跟着他的公社武装部长急中生智,马上命令紧急通知全公社的基干民兵紧急集合。全公社的基干民兵快速集结到公社所在地,武装部长讲话,说这是一场临时组织的紧急演习,目的是加强战备意识,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然后布置了每个村民兵的行军路线,一场演习就结束了。成功地掩饰了公社书记的酒后失态。
但是他也写了像“高老大爷”这样为人民群众深深热爱的好干部。这位“高老大爷”本名高友富,曾任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书中写到:“那个年代里从领导到社员只要一提及‘高老大爷’,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知道他真实姓名人并不多。可是称谓‘高老大爷’绝对是对他本人的敬畏而无任何贬义。就连县委书记和主管农业的县革委会副主任,以及县直单位各局局长一见面都习惯地称呼他‘高老大爷’,就连县里开基层干部大会,有请他介绍经验时,会议主持人也不直呼其名,而是介绍说:‘下面有请高老大爷介绍经验’,久而久之,在丰润县人民心中知道有一个高老大爷,而且知道他是远近闻名的土专家……”他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如此尊敬,就在于他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社员群众有什么困难要求,都爱和他说一说,他也是能够解决的全部解决。更重要的是,他深研农业技术,是农业技术的“土专家”,会非常及时地根据农时提醒各生产队应该注意什么,会为农民种地提供最新的技术指导。他在人民心目中达到了这种印象,就是农民根本离不了“高老大爷”,以至于当上级领导要提拔他时,当地农民联名向上级组织情愿,无论如何也不能调走高老大爷。结果农民的意愿得到满足,他却失去了升迁的机会。他就在田间地头走了一辈子,和农民兄弟打了一辈子交道。像这样的干部,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人民的热爱,尤其是在今天,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他还写了一位生产队的“红管家”刘义普。他是一个生产队的管库员,在别人看来,这是生产队中最有“油水”的岗位,因为可以偷拿一些队里的粮食。可是他却把生产队的库房当成自己的家,不仅保管的粮食器具无一损失,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自己动手缝补队里的口袋、麻袋,多少年来,他自己都不知道缝补了多少条麻袋,仅这一项每年就为生产队节省数百元。数百元,今天看来微乎其微,可是在那个年代,在不太富裕的生产队,这就是一笔大钱。后来他被唐山五金交电公司录用,仍然干管库员的工作,仍然是那样以库为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最终当选全国劳模。
这样写,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使后人读起来对于那个时代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可是这样写却是全面考较作者基本素质的事情,是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金池先生做到了,也便突显了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基调。
真实地回忆真实细节
我们古代文、史、哲不分家,许多哲学著作同时也是文学著作,比如著名的《老子》,原本就是有韵的长诗,只是后来语音变化太大,今人读不出它那原本的韵脚了。同样,史书当中也不乏出色的文学作品,比如著名的《史记》,它有许多极其精彩的细节描写,使人读起来栩栩如生,过目难忘,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鸿门宴》了。运用细节刻画人物,是古代史家的绝技,绝大部分史书都是采取这种方法来描写历史人物,因而那里面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立体的,让人记得住。再看如今的史书,不过是一堆数字与结论,枯燥干瘪,除了专业人士,大约少有人去读如今的史书。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也要十分注意吸取古代史书的技巧,注意细节的描写刻画,这样才有看点,才能让人爱看,耐看。如果也如当今史书的写法,只有数字和结论,没有生动活泼的细节,那么遭遇只怕也和现代史书一样,鲜有人问津。张金池先生这部著作让人感觉细节的刻画非常生动,以至使人有过目难忘的感觉。比如他写五十年代末乡村孩子上学的情景:“那时,只要一走进教室首先会闻到一股股浓重的煤油味,当时一些老者称煤油为毛子油。之所以有吸入煤油的感觉,是因为在教师的窗台上摆满了一个个煤油灯,这些煤油灯制作绝大部分是出自于学生家长之手,也有学生自己动手制作而成。小小的煤油灯是由废弃的蓝墨水瓶,将原来的塑料盖弃掉,然后用一小铁片从中间打一个小孔,再用一根线绳穿孔而过,瓶中放上煤油,通过线绳吸取瓶中油,点燃突出在盖上的油捻,点燃后灯会发出微弱的光亮。学生们就是利用这一盏盏土法制造的煤油灯坚持上早、晚自习。也是利用这一盏盏土的掉渣的煤油灯度过春夏秋冬;更是通过这一盏盏煤油灯学到了文化,掌握了知识,走向社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就这一个细节,就把那个时代农村孩子们求学之艰苦全部写出,根本用不着长篇大论地去述说那个时代有多么艰苦。
再如写当年农村的老辈人吃饭讲究礼节,书中这样写:“作为客人用完餐之后,要把一双筷子横在用的饭碗上,然后道一句:‘各位慢用,我先偏着了。’意在我已经吃完,各位慢用。但不能独自离席。”我们中国素来号称“礼仪之邦”,但长期以来的印象,那些礼仪主要是在上层人士中使用,草根阶层,山野乡民,则不大讲究。由这里看,我们那些普通的农民也是很讲究礼仪的,这种礼仪贯穿至穿衣吃饭行住坐卧等种种生活细节。我亦有这种体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骑自行车到农村串门,主人第一件事就是接过你的车子,推进门口,临走,主人也必将车子推出门口,再交给你。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礼节,源于过去骑毛驴时代,过去普通农家串亲戚,大抵是骑了毛驴去,到了人家,主人自然会接过毛驴拴在自家槽上,还会给弄一点水和草料。临走,也必会把毛驴牵出门外,再交给客人。后来时代变了,毛驴变成了自行车,可是礼仪没变。当然,这种礼仪在当今就行不通了,当今大多是开了汽车去,从没见主人接过车来开去停车场的。礼仪也要与时俱进。但是这一个细节却可以使我们很感性地认识到那时的农民也不愧是礼仪之邦的农民,他们自有自己的礼仪,马虎不得。而这种礼仪恰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济,不可缺失。
总之,读了张金池先生这部新著,给人的感觉就是真实,具体地讲,就是事件的真实,认识的真实,细节的真实。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这种真实,那么其事已经过半,其功未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