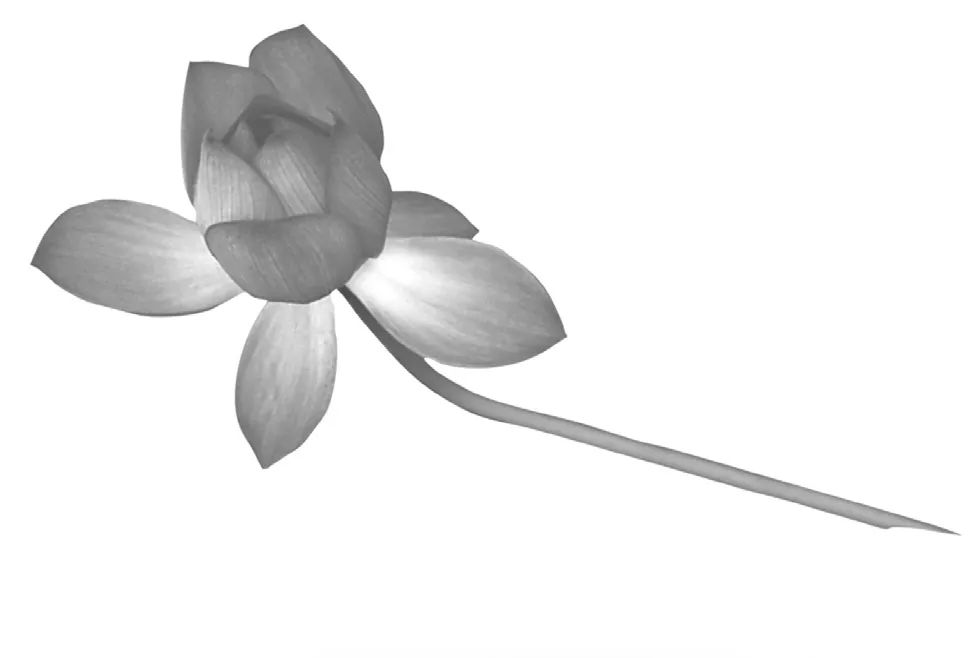火种
陈克新
一
谷雨麦怀胎,立夏麦呲牙,芒种三天见麦茬。这是我从小听父母念叨过的农谚。长大后我细心察看,发现农民总结的这些经验还真准。可五六十年后的今天,我发现芒种三天见麦茬的说法有些不准了。芒种三天见不了麦茬了,起码要在芒种五六天或者十多天之后才收割小麦。究其原因,一是现在的夏天不如小时候那样热了,二是现在都是水浇地,小麦成熟的晚了。古人云: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看来现在有些农谚也该改一改了。
作为记者,越是农忙时节越忙乎。这不,芒种已经过了八天,夏收才全面铺开。此时正是我们报道农业大丰收的时候,我开着面包车下乡采访,一路所见,到处是金黄色的麦浪,不少地块里来来往往的收割机正在收割小麦,那些空着的或装满麦粒儿的三马车也往来于村地之间,地头围满了等待收割的人群……我扛起摄像机,来到一块洼口较大的麦田,一会拍几个收割机割麦的镜头,一会儿拍几组麦穗的大特写,一会拍下收割机卸仓时麦粒儿哗哗下流的镜头,一会又拍下农民们抓着麦粒评论年成的景象。这时,一位脑袋剃得锃光瓦亮的中年人指着摄像机对我说:“你录录这麦茬,你看留得多矬呀。”
我低头一看,果不其然,这麦茬最多不过10多公分,而我突然记起不少地方差不多都是一尺多高。此时,职业的敏感已提醒我这其中好像有些文章,因为我知道,第一,麦茬低,种棒子的时候好种。为什么年年人们燎麦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麦茬高,耩棒子不好耩。现在都是带茬播种,麦茬一高耩的时候走几步就拥个大坟头子,机子就得抬起来清理清理,没法耩。所以这麦秸年年都有人燎,而燎麦茬又严重污染环境。第二,麦茬低,机子跑得慢,麦秸里边的麦粒裹得少,一亩地少说多收好几十斤。因此,老百姓愿意麦茬低,可机手们不愿意,因为麦茬低机子跑的慢,一天少割十多亩,少挣钱!还有,凡不燎麦秸的就不爱长草。而且,出苗匀实,浇的时候也好浇……正因为麦茬低有这么多好处,所以上级三令五申机手们留麦茬不能超过15公分。可要求归要求,好多机手还是不听那一套,谁乐意少挣钱呢。这么一想,我忙问:“看来这个机手还真有点思想觉悟呢。”“那是呀”,那个光头农民笑着对我说,“你知道这割麦子的是谁吗?他就是我们大皇村的党支部书记刘茂泉。刘茂泉你知道吧,就是前几年被评上全国见义勇为先进青年的那个!”
“哦——他呀,知道知道。他当书记了?”
“当书记了。”那光头农民点着了一支烟,把火柴一扔,显得有些自豪地说,“村里乱得没法闹了,上边这才动员他回来当了这个书记。”
“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那光头农民扭头问开三马的小伙子:“这才多长时间,去年过了秋吧?”
“过了秋,”小伙子肯定地说:“我老爷死的时候,他还没上来呢,我老爷死的时候我觉着麦子都出来挺高的了。”
我到县电视台上班不到一年,当然没有报道过刘茂泉的先进事迹。不过他的事迹当时好多媒体都报道过,我也知道的清清楚楚。他30来岁,复原军人,在一个塑料厂当工人。前几年有个做贼的到他邻居家偷东西,半夜三更听到有人喊“抓贼呀”,他就抓起把铁锨、穿着裤衩追出去了。谁想那贼人有手榴弹,只见火光一闪,轰一声响,他被手榴弹炸伤了大腿,但他仍然拖着一条伤腿紧追不舍。这时那人又冲他咣咣打了两枪,一枪打在胳膊上,一枪打在大腿上,这下跑不动了……后来这个案子破了,做贼的离大皇村不远,也是一个复原军人。他在周边几个县一共盗窃70多次,三马、汽车、钱,逮住什么偷什么,最后判了个无期徒刑。
此时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我意识到我今天很可能是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此时刘茂泉的收割机快开到我的面前了,我一扬胳膊,他便慢慢地停了下来,弯着腰问我:“怎么着?”
“我想耽误你一会儿,咱俩聊聊。”
刘茂泉麻利地跳下了驾驶台,用手梳理了一下满是尘土的头发,抱歉地说:“我都成了土猴了。”说着他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聊什么呀?咱们麻利着点,我也是想少耽误功夫多挣个钱。”
“行,”我把镜头对准了他,问道:“我看老百姓对你麦茬留这么低挺满意,听说这样一天少挣不少钱哪。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哎呀——你问这事。”他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说,“我说了恐怕你怀疑我唱高调。说实话,就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员,还是个党支部书记。都知道麦茬低对大伙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咱就要带头干,少挣钱也要干。我不但自己这么干,我们村一共有3台收割机,都是共产党员,我要求他们也必须这么干。”他用手一指远处正在来回跑的红色收割机,“他们俩今天都上大河岗割去了。一会儿你扛着摄像机去看看,看我说的是真还是假。”说完他双手抱拳道歉说,“实在对不起了啊,时间就是金钱,趁天儿好我得抢着干活儿了,有时间咱们家里聊。”他“噌”一下跳上了驾驶台,发动了机子,收割机又轰轰的开了起来。
我立即将摄像机对准他身后又低又齐整的麦茬录了起来,并且录了旁边人群赞许的目光和称赞的话语。猛地,我突然觉得这些又低又齐整的麦茬就是一句响亮的宣言,又好象是一面鲜红的旗帜。
二
为了验证一下刘茂泉说的是不是真事儿,我又开车直奔他指给我看的那两台红色收割机。
我一进麦地,果然见远处一台红色收割机身后的麦茬又低又整齐,跟刘茂泉割得一模一样。我向旁边等着割麦子的一群人问:“这台机子是哪个村的?”
“大皇村的。”一个长相俊俏的中年妇女抢先答道。
“这活干的不赖,麦茬不高呀。”我想来个抛砖引玉。
“他敢高吗?”还是那位妇女说,“他们村的书记说了,超过15公分就让他写退党申请书。”
“真的?”刚才刘茂泉可没跟我说这事儿。
“这还假的了?”旁边与她一位岁数差不多的妇女抢着说,“割麦子的是他表弟,他亲口对我们说的。”
“人家这书记就是拿得硬。”一位60多岁的连鬓胡子非常佩服地说,“这样的书记不好找哇,真按共产党那一套办。”
此时红色收割机也快要来到我的面前,我也冲他一扬胳膊。那司机见我扛着摄像机,赶忙停下机子问我:“怎么着,采访我啊?”
“对,采访采访你。”我把摄像机扬了起来,“听说你们村党支部书记让你割麦子麦茬不准超过15公分,出了村也不能超,有这事吗?”
“这不假,你量量超了15公分了吗?”
“你不知道这么做要吃亏吗?”
“谁不知道吃亏呀,可我有法儿吗?头割麦子村支书就把我们有收割机的党员召集到一块儿,左强调右强调,麦茬不许超过15公分,谁超了谁写检查,不写检查就写退党申请书。”
“他为什么这么要求你们呀?”
“他这个人办事特别认真。他说了,是党员就要干对老百姓有利的事,不能前脚走后脚让人家骂。”
“那你要是不听他的行不行?”
“嘿嘿嘿——”司机笑了笑说,“不敢不听。”他直了直身子,表情严肃地说:“一来他本人就这么干,二来他老拿党的原则来吓唬我们,拿得你脑瓜皮疼。再说了,平时关系又不错,不好意思不听他的。”“关键还是你本人有自觉性。”我给他戴了个高帽,不料他却笑了笑:“在他手下,自觉也得自觉,不自觉也得自觉。他有法儿治你。”为了进一步验证,我对他说:“不耽误你了,我去找你们村那台机子看看去。”
“看不看都一样,”司机听说我要看看那块地,连忙说道,“你就是借给他俩胆,他都不敢留高了。”
“为什么?”
“去年为地边地沿人家说他欺了地,他不但不承认,还依仗着他舅刘茂泉是书记,跟人家诨横不说理,气得他舅一个嘴巴打得他满嘴流血,当下找会计一量,他欺了人家一尺多……后来开党员会书记点名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还指着他的鼻子骂他,要你这样的党员干什么,给共产党挣骂呀!……往后再这样我非开除了你的党籍不行。”
“那他外甥说什么呀?”
“他敢说什么呀。”说着,他发动起了机子,又冲我嚷道:“为了保险,你还是自己看看去吧。”
三
平时局长总说我们不会深入生活,不会发现典型,可直觉告诉我,我这次却深入了生活,而且还发现了典型。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刘茂泉这个人,几天以后,我又抽空来到了大皇村。我的策略是,先接触一些老百姓,听听群众对他的评价,然后再去找刘茂泉本人谈。
大皇村的公路上都晒满了麦子,有的人正用耙子划拉小麦,有的正用扫帚幔麦子里的麦余和麦糠,也有的正在大树下下棋。我把面包车停在路旁不碍手的地方,扛着摄像机下了车。
“电视台的来了。”一位正在划拉麦子的年轻媳妇发现了我。
正在下棋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小胡子冲我看了看,似乎认识我似的,问道:“县电视台的吧?”
“对,县电视台的。”
“采访谁呀?”
“没有什么目标,随便转,碰上什么采什么。”
“那你应该采访采访我们大皇村的风气。”这是旁边一位正用扫帚幔麦余的老头儿说话了。
“大皇村有什么风气?”
“你刚过来的时候看见那几个灌麦子的吗?”老头儿用手指着北边说,“他们家有个党员,按规定他家的麦子已经晒了一天多了,不干也得收起来先让没晒过的人出出风。不能你家的晒干了,人家的发霉了。这就是风气,你说好不好?”
“那当然好啊,”我适时引导,“刚才你说得按规定,谁规定的?”
“书记呗,别人规定管用吗?”老头儿往树荫下站了站说:“过去谁管这些事呀。人家刘茂泉说了,老说党员先进,哪儿先进?说白了,就是有便宜沾光的事往后退,有困难危险的事往前蹿。就说这晒麦子吧,党员就要象个党员的样儿。原先有的人占上地方非晒干了不拉倒,别人一捂好几天,发了也没人管。今年支部广播了,只要你还承认你是个党员,就不要跟老百姓争公路,你晒个半干子先灌起来,反正放个半月二十天的也坏不了,等别人都晒完了你再弄出来接着晒。”
“有不听的吗?”我问。
“还没听说有不听的呢。”老头儿弯腰将一块玻璃碴子捡出来扔到一边,“人家说话在理,谁好意思不听。再说了,你不听他找你。”
这时旁边大树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走了过来对我说:“你们说茂泉呢吧,这可真是个大好人。原先我们村好事坏事都没有人管,就说我吧,四个小子,有三个不养着我。他们养的那个大狼狗,一天都花百八十块,可给我老婆子一分钱都心疼的打滚。我找干部,干部让我找法院。我又舍不得告他们。后来茂泉上来了,不用我找,他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都制服了。现在都出钱养着我。”
我大感兴趣:“他有什么高招?”
那老头儿抢过话茬说:“她这三个不养着她的儿子有两个是党员。茂泉连着召集了两次党员会和老人会,让大伙发表意见。大伙谁赞成不养老人呀!茂泉说话更不留情,他说,咱们入党的时候都宣过誓,都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可你们连爹妈都不养,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吗?你们养条狗都成天心肝肺的敬着,狗有了病上县里输液,不行又拉着上市里,可爹妈有了病说什么岁数大了还短得了闹个灾呀病的,养养就好了!这叫人吗?……你猜怎么着,开了两回会,他们现在每人每月给老人100块钱。”
“看来他们也是怕群起而攻之呀。”
“那是呗,不过关键还是得有人管。现在有好多事坏就坏在没人管。真要管,不是管不了。”
“也不是都不管,”老太太指着身旁大坑边上一圈杨树说:“这都是原先的干部栽的,他们自己栽了自己要,自己得利的事积极着哪。”
“也就是这一回了。”老头儿瞄了一眼那一圈杨树,“我听茂泉说了,等他们过了秋把树卖了,村里再统一栽,现在要让他们归公,他们肯定不同意。”
这时从北边过来一辆三马车,他从我身旁过的时候,问道:“采访什么呢?”
“采访一下大皇村的风气。”我回答说。
“这可多了。”开三马车的一指前边十字口墙上贴的几张大红纸,“你看见那几张红纸了吗?那是今天早晨才贴出来的吃低保的名单。原先是既不公开又不合理,现在不一样了,按我看就挺合理,别看我妈没吃上,我也没有怨言。”
“这不假。”老头儿也说,“我也没吃上,说实话我也不该吃,可是我也服气。”老头儿又指了指十字街口树下的一群人,“你再采访采访他们,看他们说什么。”
“那好,”为了了解更多的群众,我又扛着摄像机向十字街口走去。
还没走到人们跟前,树下便有人嚷道:“电视台的来了。”我忙说:“对,我是县电视台的,听说你们村今年评低保比较公平,我想跟你们聊聊。”
“这你可来着了。”一位五十多岁、瘦瘦的妇女指着旁边一位看起来两眼昏花、头有点哆嗦、身旁放着根拐棍的老太太说:“你叫她说说吧,全村属她困难,可原先就是不让她吃,她跟书记不对眼,要不是刘茂泉上来,她还吃不上。”
“这是真的。”那位老太太拉着我的手哆哆嗦嗦地说:“我大小子死了,二小子瘫了,一点进项没有,大热的天我连根冰棍都舍不得吃,人家就是不评我。今年刘茂泉说了,大皇村的低保户要是没有我,全村的党员都不够格,党支部也昧了良心,我这个书记就应该辞职。”
这时一个怀里搂着个小男孩的老大爷说话了:“今年评低保跟往年不一样,干部们先筛一下,他们看着沾边才叫代表们讨论,他们看着不沾边,连讨论都不讨论。往年谁吃咱都不知道,有的成天抽十几块钱一盒烟的也吃低保,找小姐一下找仨的也吃低保,要不大伙骂街!”
这时那老太太又说话了:“人家茂泉说了,这低保是上边拨下来的,应该是谁困难给谁吃。困难的吃不上,不困难的倒年年吃,这不是给共产党挣骂吗?”
“看来你们村这个书记挺不错呀。”我又适时引导。
“就是不错,反正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他这样的村干部。”老大爷一边摸着孩子的小鸡鸡,一边有些自豪地说,“就按老百姓办事来说吧。过去谁家要是有事不请请干部,什么事你也办不痛快,变着法儿给你使绊子。现在,茂泉公开在大喇叭里边喊,谁请客送礼就不给谁办,该办的也不办。前些日子有个死人的,为埋人占了人家地,两边打起来了,刘茂泉正在县里,听说以后租了个三马车跑回来把事给解决了。要在过去,你不请他们早就恨得你牙根疼呢,一看你出了事,早乐着打滚呢,正好看你的哈哈笑。茂泉这样的书记难找。”
“他为什么这么好呢?”我刨根问底。
“为什么?”老大爷指了指旁边墙上,说:“你看见这几个大字了吗?为人民服务,这可是毛主席说的。别看就这么五个字,可共产党的道理全在这里边……茂泉说了,共产党员不能像狗一样,给口饽饽就打滚,见着香肠就作揖。”
“这话太好了。”我发自肺腑地称赞道。此时我的手机响了,原来是主任找我,他问明了我的方位,让我立即去附近的一个村,说是那个村村东在大坑里正有一帮人抢救一个落水儿童。我立即辞别了这群人,开车向那个村赶去。
四
当晚,我用手机联系上刘茂泉,打算对他继续进行采访。他说他正在地里给人家耩玉米,非要采访就晚上9点在家等他。于是,我便在一家小饭馆草草地吃了点饭,看看快到点了,便开车直奔大皇村。
我刚进刘茂泉的院子,他开着一台播种机也回来了。他一边让妻子去冰箱里拿几根冰棍出来,一边舀水洗脸,并且脱掉了背心,连身子一块擦。完后他要带我去饭店吃饭。我执意说我吃过了,他才歉疚地说:“不好意思了。我也是想多干会儿多挣个。这年头没钱是寸步难行啊……看看你还需要我说点什么。”
我把下午在大皇村采访的事一五一十地向他念叨了一遍,总结性地问道:“看起来你是抓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问题,这确实抓在了点子上。可有一事我得问问,万一人家不听怎么办?”
刘茂泉两只大眼睛眨了眨,笑着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么想的,首先我必须带好这个头,我要事事不按原则办事,有什么脸要求别人?再说了,共产党员的招牌毕竟是一块先进的招牌。你别看有些人敢公开不按党的要求办事,可他不敢公开宣扬说,‘我就是一个不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共产党员,你们怎么着了我吧,开除还是枪毙?’我还没见过这样的人。我们就是拿道理逼他,逼得他不愿意也不敢反对。谁不讲脸面哪。当然,要想让党员都服服贴贴地听你这一套,就得有方法,有路数,得做好多细致的工作,不容易啊。我总在想,我这个书记是干什么的?一方面,我是带头的;另一方面,我又是管人的。”
“千真万确。”我完全同意刘茂泉的观点,但又不无遗憾地说:“可惜,现在好多人做不到。”
“关键还是个思想意识问题。”刘茂泉递给我一瓶矿泉水。“一些人光看别人如何如何,不看自己如何如何。就拿腐败来说吧,平时他恨腐败恨得牙根疼,恨不得拿刀子宰了那些腐败分子才解气,可轮到他掌了权,他比别人腐败的还厉害。有些人光嚷社会风气不好,你为什么不看看那些坚持高风亮节的人们呢?”
“像你这么看问题的人恐怕不多。”我佩服这个刘茂泉,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党支部书记。
“现在社会上就是缺少一股正气。只要让我当书记,我就要约束、控制你的私心膨胀,发现苗头就削,见芽就掰。我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共产党员就是火种,大皇村37个党员,700多口人,这30多个火种要带动700多口人,很快就会烧成一片。”
“VeryGood!”我禁不住用英语说了句“非常好。”是啊,我当了一年的记者,农村党支部书记也接触了不少,可从来没有听到有哪一位有过这么精致的表述,如果农村党支部书记都是这样的水平,那将是一种多么喜人的景象啊!
我正在换录音笔的当口,忽然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她一见刘茂泉就嚷道:“茂泉,你快去看看吧,我们那个该死的不知又从哪儿弄了一头病猪来,我说上回人家茂泉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还办这缺德事呀!他说,别成天老是茂泉茂泉的,没看见电视上演吗,坑人害人的多了,我不坑不是白不坑吗?快去吧,这回你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只见刘茂泉气得骂道:“真他妈不依好!”说着掏出手机,翻找了一组号码,等接通了之后说道:“喂,是畜牧局的王科长吗?我是大皇村的刘茂泉,上次我跟你说的我们村灌肠子的那个人,现在又弄了一头病猪正要宰呢……对,你马上过来,咱们来个人赃俱获。好,我现在过去先稳住他。”打完电话,他又冲我说:“只要我当大皇村的书记,就绝不允许有人干坏事。”我看他这么忙,也见好就收,说了声“你去忙,我也该走了”,立即收拾了家什,装上车辞别了刘茂泉向县城驶去。
我顺公路一直往南开,车过大堤,进了分洪道,两边的田地有几处大火熊熊,不知是哪几位农民又在燎麦秸了。此时公路上烟雾缭绕,来来往往的车灯一照,更让人看不清道路。我一边变换着车灯,一边连连摁着喇叭,好不容易过了分洪道,我才敢开快一些。
我一边开车,一边梳理着这几天对刘茂泉和大皇村采访的情况,全部采访虽然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切切实实是来自农村真正老百姓的声音,来自农村普普通通共产党员、普普通通党支部书记的心声。
刘茂泉的一言一行都让人敬佩,他和他的那些党员们,就像火一样闪光。对,那是火种啊!火种是什么?火种不就是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