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納德特如何解讀《奧德賽》
黃薇薇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跨文化研究院)
Benardete’s Interpretation ofOdysseyReviewing Benardete’sTheBowandtheLyre
Author:Huang Weiwei is lecturer at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24,China).E-mail:oupavia@163.com
Seth Benardete,《弓與琴》(TheBowandtheLyre:APlatonicReadingoftheOdyssey),MD:Rowman & Littleeld Publishers,1997,195頁
伯納德特一生都孜孜不倦致力於解讀經典作品,古希臘詩歌與哲學貫穿了他整個學術生涯。在撰寫完《伊利亞特》的博士論文四十年之後,他再次轉向荷馬,以柏拉圖爲路徑進入《奧德賽》,試圖以柏拉圖對話中展開的觀點審視荷馬史詩的情節發展,以此探查詩與哲的關係。
一、關於書名
伯納德特給自己的書命名爲“弓與琴”,這個題目與奧德修斯的名字一樣,令人費解。伯納德特只在一處提到過“弓與琴”的關係。當時,他正在分析奧德修斯殺死求婚人與女僕的正當性。荷馬對奧德修斯的描述似乎傳達出兩層含義:一方面竭力把奧德修斯塑造成一個冷血殺手,另一方面卻又爲奧德修斯的殘酷報復尋找正當理由。伯納德特稱這種矛盾的寫法就是“荷馬區分弓與琴的表現”(參《弓與琴》,頁184)。甚麼意思?伯納德特給了一個注釋,讓我們回到《奧德賽》的原文。其實,荷馬也只有一次同時提到“弓與琴”。當時,求婚人正在比賽“安弓射箭”,牧豬奴把弓交給了偽裝成乞丐的奧德修斯。奧德修斯不顧求婚人的嘲諷,
立即舉起大弓,把各個部分查看,
有如一位擅長弦琴和歌唱的行家,
輕易地給一個新制的琴柱安上琴弦,
從兩頭把精心搓揉的羊腸弦拉拉緊,
奧德修斯也這樣輕鬆地給大弓安弦。
他這時伸開右手,試了試彎弓弦繩,
弓弦發出美好的聲音,有如燕鳴。*参王焕生译,《奥德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页402。本文引文皆出自王焕生译本,以下仅注行号。
(《奧德賽》卷二十一,行405-411)
在這段話中,荷馬把弓比作琴。奧德修斯嫺熟地安弓弦,有如樂師嫺熟地安琴弦,在這裏,奧德修斯就是樂師,弓就是琴。弓與琴合爲一體,意味著奧德修斯與樂師合爲一體。而樂師,更廣泛地說,就是荷馬。換言之,奧德修斯在這裏與荷馬合爲一體。因此,在伯納德特看來,既然奧德修斯可以和荷馬合爲一體,也就可以分離,一如弓與琴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的器具,如此便意味著,荷馬是荷馬,奧德修斯是奧德修斯。也就是說,伯納德特認爲,《奧德賽》的敘述者不只是荷馬一人,還有奧德修斯。荷馬並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那樣,我們以爲,荷馬是《奧德賽》全知全能的作者,因而把荷馬等同於奧德修斯(甚至詩中的每一個人物),以爲奧德修斯只是荷馬的傳聲筒,他說的話等於荷馬說的。其實,荷馬理解的奧德修斯與奧德修斯自己對自己的理解並不相同,而奧德修斯的全貌就出現在這兩種理解當中。
如果說荷馬編造了奧德修斯的故事,奧德修斯又何嘗沒有編造自己的故事?如果說,荷馬的編造是虛構的假話,那麼奧德修斯的編造又何嘗不是如此?但是,正是在這兩種假話當中,奧德修斯的真相才得以顯現。我們對奧德修斯的理解既需要考慮荷馬的敘述,又需要考慮奧德修斯的敘述,把兩種敘述結合起來,才能對奧德修斯作出完整的理解。這就是伯納德特所謂的“詩人的辯證法”,也就是荷馬把對奧德修斯的塑造一分爲二,我們要對奧德修斯得出正確的結論,就必須把這種二分的東西合一。同理,荷馬對奧德修斯的矛盾創作就是希望能用這種二分的方式呈現真實的奧德修斯,這就是所謂的“荷馬區分弓與琴的表現”。因此,弓與琴就是這種二分關係的具體意象。弓,由弓臂和弓弦組成,二者合一才能射箭;琴,由琴柱和琴弦組成,二者合一才能奏樂。因此,弓和琴儘管是兩種不同的器具,但都是“一中隱藏著二,二能寓於一”的東西,而其功能則須合二爲一才能實現。一言以蔽之,弓與琴指的就是詩人的辯證法。伯納德特認爲,這種方法可能先於哲人,使得詩歌與哲學有了共同的基石。因此,從這個意義上,弓與琴也可以理解爲詩與哲的關係。這就是伯納德特爲自己的書命名爲“弓與琴”的緣故。
二、關於《奧德賽》的主題
伯納德特認爲,《奧德賽》中有多個主題,諸如苦難、憤怒、回歸和復仇等等,但能夠把這些主題統攝起來的是“神義論”和“政治”。*以下内容按照文章的顺序可以分别参看《弓与琴》第一章“开端”、第八章、第三章以及第九章“拉埃尔特斯”。與《伊利亞特》的“憤怒”相比,《奧德賽》似乎更強調“苦難”,不僅包括奧德修斯的海上歷險,也包括奧德修斯同伴以及求婚人和奴僕的慘死,“苦難”是整部《奧德賽》揮之不去的陰霾。但就開場而言,“苦難”似乎沒有“憤怒”在《伊利亞特》開場的位置那麼明顯,儘管荷馬請求繆斯爲他講述奧德修斯的苦難,但他明顯要求的不是苦難本身,而是造成苦難的原因——太陽神的懲罰(參《奧德賽》卷一,行1-10)。於是,我們可能會猜測,《奧德賽》講述的不只是人的苦難,而是神對人之不義的懲罰。
繆斯並未聽從荷馬的建議,沒有從奧德修斯的手下如何得罪太陽神講起,而是對奧德修斯的久滯不歸給出了另一種解釋——神明的安排。繆斯的話似乎是對荷馬的一種修正和補充:神不只介入人的遭遇,而且介入人的一切行動。奧德修斯受阻,是卡呂普索的強留和波塞冬的憤怒所致,不過神明現在已經決定讓他回家(參《奧德賽》卷一,行11-21)。奧德修斯的滯留和回歸都是神的意志。儘管繆斯強調,奧德修斯不能回家不是因爲太陽神,而是因爲波塞冬,但她與荷馬一樣,把神的意志和人的境遇對立起來,並把矛頭指向神,由此突顯了神義論問題。神義論就是奧德修斯苦難背後的主題嗎?
《奧德賽》中第三個出場的是宙斯,他對荷馬和繆斯的說法給予了如下反駁:凡人的災禍和不幸都是咎由自取,神明不是苦難之源,人的苦難源於自身的意志(參(《奧德賽》卷一,行32-34)。言下之意,凡人的一切遭遇都應該由自己來承擔,而不應該歸咎給神明。把宙斯的說法拿去重新解釋荷馬的說法,我們會發現,宙斯的話非但不是一種反駁,反而是一種有力的支撐:得罪太陽神是奧德修斯的手下不可遏制的貪欲所致。但若用宙斯的話來解釋波塞冬事件就不那麼容易了。奧德修斯惹怒波塞冬是因爲他刺瞎了波塞冬的私生子波呂斐摩斯,而奧德修斯這麼做是因爲波呂斐摩斯先吃掉了他的手下。在這個事件上,奧德修斯顯然不是處於不義的一方。所以,宙斯後來也承認,波塞冬確實是奧德修斯不能回歸的原因,因而鞏固了繆斯的說法。看來,神義論問題的確是《奧德賽》的一大主題,但這個主題並不足以解釋奧德修斯的所有遭遇和行動,尤其是在判斷奧德修斯的正義與不義的時候。
宙斯在爲神明辯護時提到一個著名的例子,但這個例子的出現同樣讓人大傷腦筋。宙斯說,埃吉斯托斯被害是喪失理智所致,不是神明的責任。神明不僅不應該爲他的暴死負責,反而應該受到感激,因爲神明對他寵愛有加,曾派赫爾墨斯警告過他(參《奧德賽》卷一,35-43)。宙斯以此爲例,證明神的無辜和恩惠。可是,宙斯爲甚麼要以埃吉斯托斯爲例?如果是爲了突出埃吉斯托斯自身的不義,爲甚麼還要如此寵愛他,對他發出警告而不是對阿伽門農給予警告?神明對埃吉斯托斯的偏心與奧德修斯有甚麼關係?就《奧德賽》中橫遭慘死的男人而言,埃吉斯托斯顯然與奧德修斯的同伴不太吻合,即便後者也有不義的一面,卻從未犯下奸娶君王妻子、殺害君王並篡奪王位的滔天大罪,更沒有爲此遭到君王兒子的報復。與埃吉斯托斯的身份和命運相當的是求婚人,然而,與其說求婚人的動機與埃吉斯托斯有相通之處,倒不如說埃吉斯托斯的例子就是求婚人事態發展的極端狀態。因此,宙斯的例子不僅可以給神義論辯護,更是意想不到地揭示了奧德修斯回家的真正理由,由此帶出《奧德賽》的另一主題——政治。
不過,求婚人畢竟不是埃吉斯托斯,他們圍著佩涅洛佩轉了三年,除了與部分女僕苟且之外,並未褻瀆佩涅洛佩半點尊嚴,更談不上與之合謀殺害親夫。此外,他們除了用言語侮辱特勒馬科斯之外,並沒有密謀殺害他。否則,他們也用不著等待三年,直到特勒馬科斯出訪回國之際,他們才布下陷阱準備殺死他,但並未得逞。既然求婚人並未成功娶到佩涅洛佩,也就談不上奪妻弑君,更談不上特勒馬科斯爲父報仇,因此求婚人的罪行與埃吉斯托斯相比相去甚遠,僅僅只是消耗奧德修斯的財產而已,或者說,僅僅只是覬覦他的女人和王位而已,遠遠不足以承受慘遭屠戮的死刑判決。由此,宙斯的例子就在暗示,奧德修斯殺戮求婚人缺乏正當性。然而,這個正當性與神明決議在奧德修斯漂泊二十年之後才讓他隻身歸返伊塔卡有關。
特洛伊戰爭持續了十年,奧德修斯在戰爭結束之後就立即回家,卻經歷了三年的漂泊到達神女卡呂普索那裏。如果神女不阻留奧德修斯,那麼奧德修斯或許在離家之後的第十三年就可以回到伊塔卡,爲甚麼神明要讓他與神女生活七年?或者說,如果他只與神女生活四年,即在求婚人開始向佩涅洛佩求婚之前就趕回伊塔卡,是不是就可以阻止求婚人的罪行,進而阻止悲劇的發生?爲甚麼一定要有七年的懸置,神明在等待甚麼?在特洛伊的十年,奧德修斯喪失了無數的同伴,而在接下來的三年漂泊中,奧德修斯又喪失了從特洛伊分得的所有戰利品,以及最後剩下的十二條船和船上的所有同伴。換言之,奧德修斯在十三年裏,犧牲了從伊塔卡帶走的所有精英。如果他空手而回,如何平息民憤?其次,在三年的漂泊中,他曾到過冥府,聽過特瑞西阿斯的預言,得知自己返回伊塔卡後還將再度離去。他離去之後,如何能讓兒子合法地繼承王位,並把自己的統治平穩地延續下去?所以,奧德修斯必須等待,等待一個可以向眾人交代的正當理由,同時等待特勒馬科斯長大成人,可以順利移交政權。換句話說,奧德修斯需要重新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需要重新建立政權,並把政權傳給自己的兒子。因此,神明的安排和宙斯的例子指向伊塔卡的政治,政治確實是《奧德賽》的另一個大主題。
求婚人在奧德修斯離家後的第十八年才去向佩涅洛佩求婚,這個時間點很有意思。此時,奧德修斯正滯留在卡呂普索的島上,儘管他整日以淚洗面,思鄉情切,但就奧德修斯的機智而言,與其說他正在等待神明的遣返,不如說他正在等待政局的演變。在奧德修斯出發去特洛伊之前,他就聽過哈利特爾塞斯的預言,說他必定會返回家園,但那將是在二十年之後,且要犧牲所有的同伴(參《奧德賽》卷二,行171-176)。此後,他在返家途中,又下過地府,聽過特瑞西阿斯的預言,說他一定會在多年後孤身返家,還告訴他求婚人將去求婚,消耗他的家產,而他也一定會用計謀或鋒利的銅器把他們全部殺死(參《奧德賽》卷十一,行112-120)。把這兩個預言連起來,奧德修斯很容易計算出自己應該回家的時間。儘管特瑞西阿斯沒有告訴他求婚人上門的確切時間,但哈利特爾塞斯清楚地說過他要二十年才會回家,如此,求婚人必是在他回家的前幾年來伊塔卡,而且要讓他們待一段時間,這段時間要恰到好處,不可以過長以致發生實質性地政變,也不可以過短而不至於挑戰眾人忍受的極限。這段時間也是對伊塔卡所有人的考驗。求婚人到達之前的十七年,伊塔卡在奧德修斯離家這麼久居然波瀾不驚,足見奧德修斯之前的統治如何穩固,但求婚人的出現說明這種穩固局面出現了動搖。與此同時,奧德修斯的父親拉埃爾特斯也值得考慮。拉埃爾特斯目前健在,說明他當初要麼讓位於奧德修斯,要麼是奧德修斯篡權。如果是前者,那麼在奧德修斯去特洛伊之前,他可以請先王出山,代爲統治。但這個假設顯然不能成立。何況,在求婚人製造混亂的這段時間,拉埃爾特斯並未露面,甚至佩涅洛佩想請他出來保護他自己的家產和孫子的想法也受到了奶媽歐律克勒婭的阻止,說明拉埃爾特斯與奧德修斯有隙,或者說拉埃爾特斯心裏至少對奧德修斯有些埋怨,如此才能解釋拉埃爾特斯的袖手旁觀。求婚人只是伊塔卡部分精英的代表,他們不僅代表著對奧德修斯統治的挑戰,也代表著他們身後一大批人對奧德修斯的怨恨。奧德修斯把他們的親人帶走了近二十年,可以說帶走的是伊塔卡的一代人,不僅如此,奧德修斯還讓他們生死未卜。如果奧德修斯真的空手而歸,這意味著伊塔卡絕大部分的人會人財兩空,那麼他們對奧德修斯的怨恨就會演變爲制裁,要麼流放,要麼處死,然後另立新王。這些還是有正當理由對付奧德修斯的人,此外還有一些蠢蠢欲動者,他們依附於這些人,對奧德修斯的統治表示質疑和不敬。這些人就是以牧羊奴墨蘭提奧斯和十二個與求婚人廝混的女僕爲代表的僕從。奧德修斯需要時間讓這一切局面浮出水面,更重要的是他要讓自己有足夠的時間應付這一局面,並爲自己的解決辦法(重建政權)將付出的代價(殺死所有的求婚人和不忠者)提供正當的理由。這不僅是他避世在外七年之久的原因,也是他回到伊塔卡慢慢籌畫復仇步驟的原因,更是荷馬謀篇佈局的原因。這樣一來,神的安排就與奧德修斯的計謀融合在一起,使得神義論與政治突顯爲《奧德賽》的兩大主題。
三、關於奧德修斯
伯納德特按照詩人辯證法的原則,根據荷馬對奧德修斯的命名與奧德修斯對自己的命名兩個方面來解析奧德修斯的身份。*以下内容按照文章的顺序可以分别参看《弓与琴》第三章、第七章“名字与伤疤”、第五章“记忆与心智”以及第七章“女仆”。奧德修斯有兩個名字,一個是他外祖父取的,一個是他自己取的。荷馬說,“奧德修斯”這個名字是外祖父奧托呂科斯取的。“奧托呂科斯”這個詞的希臘原文指“狼”,而且奧托呂科斯本人善於偷盜和說咒語,這兩個本領都是赫爾墨斯賜予他的。赫爾墨斯之所以賜給他這樣的本領,是因爲奧托呂科斯善於博得神明的歡心,神明樂意伴隨他。奧德修斯出生的時候,奧托呂科斯去看他,他說,
因爲我前來這片人煙稠密的國土時,
(參《奧德賽》卷十九,行406-409)。
奧托呂科斯說自己“怒不可遏”的時候,用的是一個有雙重含義的詞,即可以把這個詞理解成中動態或被動態。如果理解成中動態,那說明是他自己發怒,但如果是被動態,那說明他是在承受憤怒。因而,奧德修斯的名字也就具有了雙重含義:他既是“憤怒”的化身,又是引起“憤怒”的對象。無論如何,這個名字的雙重含義與奧德修斯的命運和遭遇緊密地聯繫起來。如果說他久滯不歸是在承受波塞冬憤怒的懲罰,那麼他回家之後對求婚人的殺戮就是在發洩憤怒,奧德修斯的一生就在承受憤怒與發洩憤怒中度過。奧德修斯就是“憤怒”。
然而,荷馬在介紹奧德修斯名字的來歷時,卻把這個故事插入在“傷疤”的故事當中。當時奶媽歐律克勒婭正在給奧德修斯洗腳,併發現這個標誌著奧德修斯身份的疤痕,以此認出眼前這個乞丐就是真正的奧德修斯。傷疤是奧德修斯的特徵,一如憤怒是奧德修斯的特徵一樣,傷疤和憤怒都是奧德修斯身上的痕跡。荷馬把奧德修斯取名的過程與奧德修斯傷疤的由來放到一起講,實際上就是把奧德修斯的本質與奧德修斯的過去聯繫起來。傷疤是外在於奧德修斯的標記,憤怒是內在於奧德修斯的實質,我們也可以說,荷馬讓傷疤與名字在這裏相遇,相當於讓奧德修斯的外表與實質融爲一體,使得奧德修斯的“身”與“名”合二爲一,奧德修斯的全貌因而得以完整的呈現。
那麼,我們回過頭去重新理解,荷馬在開篇並沒有提到奧德修斯,而是用“那位英雄”來代稱(參《奧德賽》卷一,行1)。奧德修斯的名字是由繆斯說出口的,而且與波塞冬對他的“怨怒”同時出現(參《奧德賽》卷一,行20-21),說明荷馬一開始就讓奧德修斯的“身”和“名”相分離,讓“憤怒”一直尾隨其身,直到卷十九才讓名和身合二爲一。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說,荷馬講述的奧德修斯,其實是在展現一個人的身和名從分裂到合一的過程,奧德修斯的回歸就是發現整全的自己的過程。然而,這只是荷馬的說法,我們還需要仔細分析奧德修斯本人的說法才能知道我們的結論是否合理。
儘管奧德修斯在離開神女卡呂普索之前,早就知道了自己未來的命運——他註定要返回家園,也清楚他回去的使命,但他對自己是誰以及自己的遭遇仍然缺乏清晰的認識。直到伊諾的出現,他才知道自己與波塞冬的恩怨。奧德修斯離開卡呂普索的第十八天,波塞冬發現了他,便發動了一場罕見的風暴來懲罰他,以發洩對他的憤怒。此時,奧德修斯對自己說了一段話:
我真不幸,我最終將遭遇甚麼災害?
我擔心神女說所的一切全都真實,
她曾說我在返抵故土家園之前,
會在海上受折磨,這一切現在正應驗。
宙斯讓這許多雲霧籠罩廣闊的天空,
把大海攪動,掀起各種方向的勁風的
暴烈氣流,現在我必遭悲慘的毀滅。
那些達那奧斯人要三倍四倍地幸運,
他們爲阿特柔斯之子戰死在遼闊的特洛亞。
我也該在那一天喪生,接受死亡的命運,
當時無數特洛亞人舉著銳利的銅槍,
圍著佩琉斯之子的遺體向我攻擊;
阿開奧斯人會把我禮葬,傳我的英名,
可現在我卻註定要遭受悲慘的毀滅。
(參《奧德賽》卷五,行298-312)
在這段自白中,奧德修斯對自己的未來表現出極度的不自信。他以爲自己會死去,而且是死於一場風暴。這樣一來,還不如當初死在保護阿基琉斯屍體的戰鬥中,那樣他至少可以英名傳世,而不像現在這樣死得寂寂無名。奧德修斯並不知道自己是在承受波塞冬的憤怒,也不知道自己的本質就是要承受憤怒,他一直以爲風暴的始作俑者是宙斯。但在這裏,他表現出的後悔是因爲死在海上不會得到埋葬,而葬禮是對凡人的認可和禮贊。奧德修斯在比較兩種死法,也就是在比較自己的選擇。他依稀開始明白,自己爲何如此堅定地拒絕卡呂普索,不只是神意的安排,也是自己意志的決定——拒絕成爲不朽的神明,選擇有死的凡人,是要延續自己的過去。奧德修斯看似選擇了未卜的前途,卻是指向自己的過去。奧德修斯的選擇把未來的自己與過去的自己聯繫在一起,這才清楚自己是誰,一如荷馬對他的描述。
奧德修斯對自己的理解有進一步的認識,是在伊諾出現以後。出於同情,伊諾現身,準備救他一命,從伊諾的話中,奧德修斯才得知,自己的苦難是波塞冬所爲,而且自己的命運就是承受苦難。伊諾說,
不幸的人啊,震地神波塞冬爲何對你
(參《奧德賽》卷五,行339-340)

然而,僅僅是自己的名字和經歷還不足以構成奧德修斯對自己的全部理解,除了“奧德修斯”這個名字之外,他還給自己取了一個名字“無人”。按照奧德修斯漂流的順序,波呂斐摩斯這段插曲是第三次歷險,而波塞冬的復仇則發生在最後一次返家途中,那時奧德修斯早就經歷完所有的險阻,且被神女囚禁了七年並最終獲得釋放。也就是說,奧德修斯自己取名的故事發生在得知自己名字的實質之前。但波呂斐摩斯這段故事是奧德修斯對費埃克斯人講述的,換句話說,奧德修斯是在知道了自己名字和命運之後,重新反思了給自己取名的故事。



(參《奧德賽》卷九,行405-4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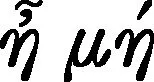

(參《奧德賽》卷九,行408)

奧德修斯除了承受神明的憤怒,自己也有發怒的時候。其中最爲明顯的就有兩次:一次是他自述的對波呂斐摩斯發怒,一次是荷馬敘述的對女僕們發怒。前一次發怒是看到兩個同伴被波呂斐摩斯吃掉的時候,後一次發怒是看到一些女僕去與求婚人鬼混的時候。這兩次他的心都要狂跳出來,都想著要立即殺死對方,但心裏的“轉念一想”(第二種想法)又讓他冷靜下來。如果他在怒不可遏的情況下殺死波呂斐摩斯,那他的確能夠報仇雪恨,但會因爲搬不動洞口的巨石而把自己和其餘同伴困死在洞裏;同樣,如果他一怒之下殺死那些女僕暴露了身份,就無法對付求婚人。兩次的“轉念一想”都沒有神的參與,都是奧德修斯理性思考的結果,奧德修斯用自己的“智慧”戰勝了“憤怒”。如果我們把“憤怒”對應爲柏拉圖的“血氣”,而把“智慧”對應爲“理性”,那麼奧德修斯就是“理性”統治“血氣”的典型示例,或者說奧德修斯就是“哲人王”的化身。如果說,奧德修斯最終如此意識到了自己身上的所有品質,並由此理解了自己的命運,卻看不到自己的品質和命運產生的結果,那麼這個問題則由荷馬通過後面整整十二卷的篇幅來展示:奧德修斯的憤怒和智慧產生的結果是屠戮和恐怖。或許可以說,荷馬在柏拉圖之前就對“哲人王”做了一番審查。
最後說一點《弓與弦》的結構。伯納德特基本上按照《奧德賽》的敘述結構來謀篇佈局。《奧德賽》總共二十四卷,前面十二卷主要講述奧德修斯的歷險,後面十二卷主要講述奧德修斯的屠戮。按照這樣的線索,伯納德特把《弓與弦》分成九章。第一章針對卷一和卷二,分析《奧德賽》的主題;第二章針對卷三和卷四,分析《奧德賽》中的範式;第三章針對卷五,分析奧德修斯的抉擇;第四章針對卷六至卷八,分析奧德修斯到達費埃克斯人那裏的情況;第五章針對卷九至卷十二,分析奧德修斯口述的九次歷險;第六章針對卷十三和卷十四,分析奧德修斯回到伊塔卡的情況;第七章針對卷十五至卷十九,分析奧德修斯殺死僕人的正當性;第八章針對卷二十至二十二,分析奧德修斯殺死求婚人的正當性;第九章針對卷二十三和卷二十四,分析奧德修斯與親人的關係。
以上只是概述了《弓與琴》的部分內容,方寸之間難以言盡閱讀此書的驚奇和喜悅,而要準確地捕捉伯納德特解讀過程中所傳達的智慧,也難免力有不逮,僅拾取一些散落在地的智慧的遺珠罷了。《弓與弦》可謂我們理解《奧德賽》的嚮導,通過它,我們既可以傾聽荷馬的意見,又可以觀照奧德修斯的內心,並在荷馬和奧德修斯的雙重闡釋下理解“憤怒”與“苦難”,“無人”與“智慧”的分分合合,從而聆聽一曲完整的《奧德賽》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