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
論《克力同》的結構和意圖
羅曉穎
(重慶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
柏拉圖的政治哲學生動體現於蘇格拉底的言行之間,《克力同》則爲蘇格拉底行言的一致提供了最深切的例证。《克力同》中的蘇格拉底使用哲學的與非哲學的兩種辯證法,哲學的辯證法呈現哲人正義,非哲學的辯證法關切法律及城邦(政治)生活秩序。兩者的對比昭示了蘇格拉底的選擇及其所體現的政治哲學內涵。本文意在從對話的整體結構出發探究蘇格拉底兩段講辭的內在差異和對話的意圖。克力同基於大眾意見勸逃,認爲自救並盡到爲父之責才不違正義,蘇格拉底則認爲行動的正義以理性的深思熟慮爲前提,不可盲從大眾,而要聽從行家。他提出不可有意爲惡,因此切斷了行爲關聯性的鏈條,保持了準則的一貫性。最終說服克力同的法律講辭,其論證一方面暴露法律的缺陷,一方面承認了蘇格拉底的冤屈。蘇格拉底的含冤服法,表明沒有完美的法律,而有缺陷的法律亦可維持城邦秩序。可以說,蘇格拉底的選擇使他成爲言行一致的哲人和遵紀守法的好邦民,藉此,蘇格拉底既是爲城邦法律辯護,也是爲未來哲人在城邦中的生存辯護。
Author:Luo Xiaoying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E-mail:xiaoyingwell2005@126.com他寧願守法而死,也不願違法偷生。
——色諾芬
色諾芬在回憶蘇格拉底時,說蘇格拉底常愛引用荷馬的一節詩,詩中描述了奧德修斯如何對傑出人物與普通士兵說話時使用不同的言辭。蘇格拉底爲何喜愛這節詩,或者說,引用的用意何在?施特勞斯對此的解釋是:“蘇格拉底使用兩種類型的辯證法:一種導向真理;另一種總是在普遍接受的意見範圍內而導向(政治上的)一致”。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否認自己“說話很聰明”,然而,修辭家意義上的不聰明與柏拉圖式哲人的審慎並不衝突,甚至修辭家眼中說不來“聰明話兒”的人恰恰體現了某種德性。“兩種類型的辯證法”在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身上自然也不乏其例。《克力同》這篇短小的對話就明確展示了蘇格拉底對兩種談話方式(邏各斯)的運用,換言之,《克力同》中的兩段講辭正是蘇格拉底兩種辯證法的具體運用。這兩段講辭,一是蘇格拉底本人首次答復克力同的越獄請求和一系列質疑;一是蘇格拉底假託法律之口對克力同的二次答復。通過對比兩段講辭,通過蘇格拉底的選擇,柏拉圖向我們揭示的正是哲人爲政治辯護的可能性。那麼,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爲何及如何爲政治辯護?對此,我們有必要從《克力同》這部對話本身的結構入手進行探究。
儘管人物動作描寫闕如,《克力同》本身仍是一部完整的戲劇,亦是“戲劇中的戲劇”——具體而言,若將與蘇格拉底之死有關的四部對話視爲一部大戲劇,《克力同》可視爲這部“大戲劇”中的緩衝或起伏階段。從蘇格拉底接受控告、被判死罪,到他飲鴆赴死之間,因城邦的敬神行動行刑被延遲了。可以想見,在這一個月的額外生命時光中,蘇格拉底與他的追隨者之間一定又有過許多熱烈的交談。然而,當聖船即歸,刑期逼近時,克力同渴望勸說蘇格拉底逃跑以改變其死亡的命運。這一個小小的“波折”促成了蘇格拉底與克力同的這場談話,這是一場對(未來)哲人與非哲人表現出幾乎同樣悲憫情懷的談話。面對克力同的勸說,蘇格拉底以“哲人正義”與“城邦法律”兩種不同說辭兩番答復克力同。最終,當戲劇落幕時,克力同默然接受了蘇格拉底的勸導。
一、困境
生死抉擇的“困境”,蘇格拉底已在《申辯》中直面過了。是活著遠遁他鄉,放棄在雅典從事哲學?還是含冤受刑而死?“重要的不是活著,而是活得好”,這句話足可預示蘇格拉底可能作出的選擇。在雅典民眾面前,蘇格拉底申明他這樣從事哲學乃是神所安排的使命。在城邦容不下哲人,或者說在哲學與政治衝突的背景下,蘇格拉底爲哲學在城邦中的生存辯護,最後,不事哲學毋寧死!《申辯》結束時蘇格拉底接受了不義的死刑判決。“死”而非苟活於世是蘇格拉底擺脫“困境”的方式。平靜地於獄中等待死刑的蘇格拉底,在《克力同》中似乎又被帶入新的困境。得知“聖船”就要回來的克力同天不亮就匆匆趕到監獄,因爲船今天回,明天蘇格拉底就得死。這個“嚴酷的消息”讓克力同心急如焚,然而,看到酣眠的蘇格拉底時他大爲驚訝。針對克力同的驚訝,蘇格拉底說,年紀老邁的人不應爲死而惱怒。但克力同說,別的老人“卻在這樣的不幸中被擊垮”,年紀不能令其釋然,死對他們來說就是極大的不幸。蘇格拉底表示贊同。我們知道,克力同與蘇格拉底年歲相仿,他極力勸逃的背後不正由於對死亡的畏懼麼?那麼,克力同也在說他自己?他也屬於無法釋然的那類人?
聽到消息的蘇格拉底卻略帶戲謔地說起他剛做的夢,夢中有白衣女子說他第三天“會到達土地肥沃的佛提亞”。蘇格拉底認爲這預示他會在第三天死去,這在克力同看來不過是個怪夢。他急於告訴蘇格拉底逃跑的理由和計畫。失去朋友以及因大眾誤解而失去名聲,對克力同來說不啻一場災難。因此,“救還是不救”是克力同的困境,而“逃還是不逃”則成了克力同強加給蘇格拉底的困境。爲了擺脫困境,克力同要說服蘇格拉底逃跑,而蘇格拉底則要說服克力同爲甚麼不可逃跑。
二、勸說
克力同的勸說依據三大要點:大眾的意見以及朋友和名譽;蘇格拉底無需顧慮錢財;蘇格拉底應當自救並承擔爲父之責。克力同首先“基於大眾意見”提出他的論據:其一,蘇格拉底死了,他會失去“不可再得的朋友”。其二,若他不救蘇格拉底,就會失去好名聲,因爲大眾會認爲他愛錢財勝過朋友。其三,必須重視大眾還因爲他們破壞性很大。後兩個論據明顯源於克力同對大眾意見的態度,可爲甚麼“失去不可再得的朋友”也是因於大眾意見呢?聯想《斐多》中克力同缺席“靈魂不死的論證”便可知道,克力同替蘇格拉底送老婆孩子回家,最後又詢問蘇格拉底死後如何安葬等。顯見克力同關心的是肉體的蘇格拉底,至於靈魂的蘇格拉底,雖然克力同與蘇格拉底無比親近,並視之爲“獨一無二”的朋友,但他未必真正懂得蘇格拉底。克力同關注的正是大眾關注的,關心肉體豈非大眾的普遍趨向?再有,對話開始時他們曾討論老年與死亡這一話題,克力同不正是基於大眾對生死的理解才急匆匆趕來勸說蘇格拉底行動的麼?
至於名聲,正如克力同所說,大眾不肯相信蘇格拉底有機會逃走時竟然不願逃走,“螻蟻尚且偷生”,保全性命不是最普遍的人之常情麼?克力同擔心因大眾的誤解而失去好名聲並不奇怪。克力同難以承受重財不重情誼的惡名。況且他並非沒有領教過大眾的鑠金之口,色諾芬在《回憶蘇格拉底》中記述過,大眾要搞臭克力同,正是蘇格拉底幫他逃過了一劫。當然,大眾也在乎他們的名聲。從《申辯》中我們不難推斷,判蘇格拉底死刑的雅典人(大眾)內心其實覺得蘇格拉底應當被自己的朋友從獄中擄走。換個角度說,這或許是一個很深的陰謀,深到已成爲常情的一部分:雅典大眾希望蘇格拉底緘口,他最好去流放,既不給雅典帶來濫殺無辜的惡名,他們也無需再聽他在市場“聒噪”。法庭上的蘇格拉底沒有上當。《克力同》中身不由己的克力同,在不自知的情況下無異於再次替城邦勸誘蘇格拉底流放,蘇格拉底豈會上當?無疑,蘇格拉底也在乎他的“一世英名”,而且那或許還是更嚴峻的問題:一生都在談論美德,臨到頭兒卻爲貪生怕死而越獄,那就不但使他這原本無罪的人成了罪人,還使得他一生的言行都成了大笑話。對蘇格拉底而言,他一生所教誨的東西即便付出性命也必須維護,而他的死還恰恰同時維護了那個不義地判他死刑的城邦法律的尊嚴。最終,這受到不義判決的哲人竟然成爲城邦中好邦民的表率,成爲後世的榜樣。
蘇格拉底當然也是克力同的榜樣。克力同對朋友與對城邦的態度截然不同。在克力同看來,蘇格拉底死帶給他的名譽損失,要比他自己違背對雅典人的誓言而勸誘蘇格拉底逃跑造成的名譽損失大得多。在這位雅典紳士眼中,更高的責任是挽救朋友的性命,而不是忠於自己的國家。我們還記得,在《斐多》(115d以下)中,蘇格拉底說克力同曾答應裁判官們保證蘇格拉底在關押期間不離開監獄。可見,克力同漠視自己的誓言,也並不把遵守城邦法律看成必須(如一般大眾不會像哲人那樣嚴格約束自己的內心和行爲)。這似乎正好反襯了城邦判決的荒謬:一個寧死都不願意違法的哲人被判死刑;一個隨時可以無視城邦法律的克力同,卻是他那個時代的標準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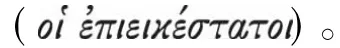

克力同勸說的另外兩個依據是:蘇格拉底無需顧慮錢財;蘇格拉底應當自救並盡爲父之責。克力同用錢買通關節,制定了逃跑計畫。雖然明知行爲本身違法,但他想到的只是蘇格拉底會顧慮錢財問題;而蘇格拉底顧慮的卻是比這更深的麻煩,即逃跑後必然發生的連帶反應,如克力同或其他朋友會遭逮捕、流放或判刑。當然,進一步說,怕給朋友惹麻煩也不是蘇格拉底拒逃的根本原因。不逃跑的根本原因在他自身,在於他對“甚麼是美好生活”的理解。克力同的安排可謂周密,包括逃亡後的去處——無異於爲蘇格拉底選好了流放地。但如前文所述,蘇格拉底在《申辯》中(37c以下)拒絕提議流放,在他看來,離開雅典就對他構成了懲罰,而他認爲自己的品行不該遭惡報,他不會提出、更不會主動選擇這種替代性懲罰來對自己行不義。
在錢財之外,克力同更談及正義——甚麼樣的行爲是正義:眼下冒險救友就是正義。後面我們會看到,蘇格拉底同意逃跑,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朋友的名譽,以及使兒子免遭孤兒之苦,在克力同眼裏也都是正義。但是,克力同沒有注意到,這樣冒險違犯城邦法律是不是正義?把朋友或個人放在比城邦更高的位置是否正義?好邦民克力同偏偏忽略了邦民對城邦的義務。克力同還會談到“羞愧”。克力同基於雅典傳統的道德觀念所談及的正義,與蘇格拉底的正義,其差異究竟何在?
克力同從大眾視角來審視蘇格拉底,認爲他放棄自救就是處事不當。這就是說,在能夠保全自己時不保全自己,等於幫助敵人更快速地毀滅自己,而這恰是敵人最想促成的事情。“損己(友)助敵”在大眾看來簡直是不可原諒的愚行,因爲傳統的道德觀念認可“助友損敵”。至於放棄爲父之責更是大眾眼中的怯懦之舉。克力同責怪蘇格拉底錯過幾次逃生機會,尤其責備他沒有認真地依照陪審團樂見的方式申辯,而這卻恰恰是蘇格拉底嗤之以鼻的帶上兒女對法官“哭訴求情”式的申辯(《申辯》34b-35e)。在蘇格拉底看來,哀求法官不合正義,而以情緒影響法官的判決也有違神意。
對於以上克力同的建議、克力同提出的問題及其暗藏的危險,蘇格拉底必須答復。他給出了兩種答復,一種基於哲學的理據,一種出自法律的視角。兩種答復論據不同,卻殊途同歸,均指出“蘇格拉底不應逃跑”。但最終說服克力同的是第二種答復。爲甚麼?兩種答復的根本區別何在?以蘇格拉底對克力同的瞭解,當然知道甚麼樣的言辭可以說動他,既如此,爲何又有兩次答復,這其中可能暗含何種意圖?
三、哲人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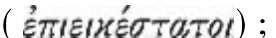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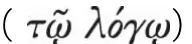
這裏展示的不只是蘇格拉底的理智,更是他作爲哲人的品格。蘇格拉底語重心長地勸導克力同不能因眼下的不幸放棄原先的準則,表明這裏的蘇格拉底與申辯的蘇格拉底完全一致。當然,要說服克力同,蘇格拉底必須設法解決使克力同感到逼迫的兩樣東西:大眾意見、大眾力量。
蘇格拉底首先條分縷析地區分好意見和壞意見,實際上無形中排除了大眾的意見,留下了好意見——回到老問題:蘇格拉底區分知識與意見,但同樣重視意見而非輕視意見。我們的知識可能只是“無知之知”,最高的知識只有靈魂在諸神的引導下在天界才能見到。那麼,退而求其次,我們必然得尋求最接近知識的意見——好意見。有所知者才有好意見,行家即有所知者。
關於意見的分解如下:
不必看重人們的所有意見(意見中區分出好壞)
而是有些看重,有些不看重;
接著,蘇格拉底有意地把意見引向人的意見,即從僅僅考慮意見的好壞引向考慮人的好壞,也即從對意見的分類引向對人的分類。這意味著:其一,意見終歸是人的意見,蘇格拉底點明了問題的根本;其二,爲甚麼引向人?是爲區分少數人和多數人。這可以在第一種答復結束時看清楚,“我知道,只有少數人相信或將會相信這話”(《克力同》49d)。
也不必看重所有人的意見(人中區分出明白人與糊塗人)
而是有些人的看重,有些人的不看重;
進而推出:
看重好意見,不看重壞意見
好意見是明白人的,壞意見是糊塗人的
這顯然已經完全將大眾及其意見排除出去了。那麼好意見是甚麼人的?明白人的,即在某一個領域擁有專業知識(或意見)的人,即行家。

若不聽從行家意見會怎樣?蘇格拉底說我們要遭殃。不聽從醫生或體育教師,身體會遭殃。而關於義與不義、美與醜、好與壞,若不聽從行家意見,我們“摧毀和損害的將是那個因行義而變得更好,因行不義而遭到毀滅的東西”,這個東西不就是靈魂嗎?爲了不損害靈魂,我們需要找到關於正義(和美德)的行家。蘇格拉底是這方面的行家嗎?顯然,蘇格拉底沒有把自己當成這樣的行家,他只是說自己寧願服從行家的意見。那麼,若找不到這樣的行家該怎麼辦?從整個對話來看,蘇格拉底直面了這個難題,因爲他的言辭表明,若我們找不到這樣一個人,聽從保守的法律是次好的選擇。蘇格拉底也以自己的行動表明自己遵從了法律,並教導克力同這位大眾的一員也要如此。然而這時的克力同聽從大眾意見,正在忙於違背法律。

回到克力同的勸說,我們需注意三個問題:其一,蘇格拉底拒絕逃跑,逃跑挽救身體,卻可能敗壞靈魂;其二,克力同勸告蘇格拉底時談到的顧慮也均與身體相關;其三,哲人對身體與靈魂的看法顯然與大眾極爲不同,他甚至輕視身體。如此,若要靈魂不被毀掉,就必須時時自問“如此行事是否正當”。蘇格拉底遭受了“不義的”判決,但他選擇“正義地”服從。這是人們不常遭遇卻並非不具有典型性的兩難境地。蘇格拉底因雅典人的誤解和敵意陷入了這一兩難境地。色諾芬在《申辯》中(第26、28段)對此也有記述,蘇格拉底說“無論如何別人不義地處死我,我沒有理由慚愧。不光彩的不是我,而是定我罪的人”。阿帕拉多斯在蘇格拉底被判罪後說,“我最難受的是,你這樣被不公正地處死”,蘇格拉底則微笑著回答(極少見他笑):“難道你希望我被公正地處死?”這一問一答的鮮明對比,讓我們立刻明白了蘇格拉底對自身處境的深切感受和平靜處置。
顯然,蘇格拉底的行動前提並不是自己被如何對待,而是其行爲本身的正義。可以說,這是一種純粹哲學的、反思的方式,而非出於習慣或傳統或大眾意見。在這些被排除的傳統的或大眾意見的考慮中,也包含了克力同所顧慮的東西:錢財、名聲、兒子。無疑,這個行動本身的正義通過遵循最好準則而得以確保。這個準則對克力同所圖謀的行動判定如下:賄賂和逃跑都不正當,都是錯誤行爲(甚至是違法行爲),那麼,寧可等死或遭受別的不義,也不可讓自己在當下行不義。可見,蘇格拉底切斷了行爲關聯性的鏈條(自然的或傳統的鏈條),卻保持了準則的一貫性。可以對比傳統的、自然正當的“血親復仇觀念”,其背後當然蘊含“助友損敵”觀念,這正是自荷馬以來希臘思想中流行的觀念,一直延續到羅馬,到任何時代……而這不恰恰是常人生活世界中的支配性行動準則?
最後蘇格拉底將其答復的論證上升到“不可有意爲惡”的問題,哲人的原則與習俗或大眾原則的衝突也最明顯地凸現出來。不但不能有意爲惡,甚至以惡報惡也不行,如此便否定了“血親復仇原則”。末了,蘇格拉底不忘感歎,信從這一點的只有少數人,而信與不信者彼此輕蔑,實“道不同,不相爲謀”。這裏面是否暗含蘇格拉底的反諷?他已經意識到與克力同商議一致行動的困難,因而只得轉變論證方式,引出法律——這個與克力同對等的形象,這樣他們之間才能商議出一致意見?
四、城邦之法
蘇格拉底基於哲學理據的論證聽得克力同暈暈乎乎。蘇格拉底接著問:“未說服城邦就擅離此地,我們是否惡待了某些人……我們遵守那些曾一致同意的且爲正義的事情,還是不遵守?”克力同則說“我沒法兒回答你的提問,因爲我不理解”。不得已,蘇格拉底換了一副面孔,他引入擬人化的法律來勸說克力同,因爲蘇格拉底與法律最終(或許僅僅表面上)在這一點上高度一致:“不能逃跑”。那麼,擬人化的法律所說的正是蘇格拉底內心要說的嗎?這是一個讓許多學者爭論不休的問題,此暫不贅述。此處我們除了關心法律說了甚麼之外,也還關心在甚麼情況下法律站出來說話,以及法律講辭中的理據如何不同於蘇格拉底講辭的論辯,卻又讓克力同心服口服。蘇格拉底借法律之口作出的第二個答復,實爲法律對蘇格拉底的質問,這一問共分六節,分別展示了基於法律或城邦的、不同於哲學的理據。前三節(十一至十三節)先後提出“不可逃跑”的三個理由:逃跑有違城邦與法律;受惠於城邦和法律者毋求平等;邦民與城邦的同意契約。這三條可以說是“普遍性”意義上“不可逃跑”的理由,對任何邦民都具有同樣的約束力。尤其前兩條強調的正是個人與城邦之間的“血脈關聯”(即邦民與城邦的關係如同子女與父母),事實上也反映了法律“強制”的一面。十一節提到個人行爲違法可能摧毀整個法律,究其原因應該是:挑戰了法律的權威、有辱法律的尊嚴、破壞了使所有法律有效的法(更嚴重的是這種圖謀還會成爲一個哲人違法的惡劣先例,蘇格拉底絕不可能爲之)。在這一節中,演說家正是城邦及法律的維護者。第十二、十三節可以看作是進一步深究血脈關聯所導致的法律的強制性根源:受惠於城邦、同意契約。這意味著邦民應當對城邦感恩,而不是力圖毀滅城邦和法律。此處暗示的問題是:邦民應以何種姿態對待城邦?若此,與其說法律是在教導蘇格拉底,倒不如說是教導克力同,前文正是講克力同全然漠視城邦法律的存在而勸說蘇格拉底逃跑。那麼,甚麼樣的行爲會毀滅城邦和法律?顯然,克力同圖謀之事即越獄行爲本身就違法,會毀滅法律甚至整個城邦。因爲,逃跑意味著不認可且不服從城邦法律的裁決,這種行爲無異於個人私自廢棄法律判決並使之失去效力,最終必然連整個城邦的權威都受到顛覆?
但施特勞斯提醒說,父親可能瘋癲,城邦也可能會通過瘋癲的法律。他提醒我們注意法律在這兩節中的自相矛盾之處,那就是,法律提出的“無條件地服從法律”的理由自相矛盾:一方面說法律如父母對子女一般地生養和培育了邦民,因而邦民如同法律的奴隸,需要無條件地服從法律(或城邦)——專制且毫無商量餘地;另一方面又說邦民與法律(城邦)有默認的同意契約,曾就許多事情達成過一致,表明自己並非簡單的粗暴專制,而是允許邦民像自由人一樣地對待法律——自由且民主。這種專制與自由的對立意味著擬人化的法律論證中存在明顯缺陷,內部不能自洽的法律的辯證法是否動搖了法律的威權?至少,這種缺陷暗示城邦的法律並非沒有可能成爲惡法,譬如蘇格拉底曾提到過,雅典的法律在一天之內判人死刑。那麼,蘇格拉底如此展示法律的論證意圖何在?內在包含矛盾的法律講辭爲何比哲學講辭能更有效地說服克力同?蘇格拉底爲何服從有明顯缺陷的法律,這是不是縱容了不義的法律?
其後三節(十四到十六節),法律提出“不可逃跑”的另外三個理由:最中意城邦者尤不可抗法;逃亡後的生活前景黯淡;毋違正義,才能坦對冥間法律。這三條可以說是針對蘇格拉底的“個體性”理由。第十四節具體到蘇格拉底這個個人,他算得上最中意雅典城邦的人:除了打仗幾乎從不離開雅典,在法庭上拒絕提議流放,而且儘管屢贊他邦政法修明,卻對雅典七十年不離不棄。那麼這意味著甚麼?蘇格拉底的使命就是待在雅典,以警醒雅典人關心自己的靈魂?或許這也是哲人返回洞穴的行動,蘇格拉底是主動返回洞穴的哲人?他寧死也不願流放,離開雅典就是離棄哲學生活。無疑,法律看重的正是蘇格拉底待在雅典七十年的事實。既然七十年不離開這裹,那自然表明他對城邦的一切都很滿意,這當然包括對法律。若此,違背這裹的法律是難以想像的事。這個論據既包含城邦生養蘇格拉底的恩德,也暗示他與城邦之間久已存在而未明言的同意契約。
第十五節實際上談論的是逃亡後黯淡的生活前景:他將不斷在逃亡中,於己於友均無好處。於己,居無定所、顏面盡失;於友,違誓抗法,身家不保。到了政法修明之邦會遭到敵視;而到了亂無法紀之邦則會受到嘲笑。如此蘇格拉底照樣不能從事哲學,這點與蘇格拉底自己在申辯時的考慮完全吻合。
最後,法律警告說“毋違正義,才能坦對冥間法律”。正義比兒女、性命及其他一切都重要。況且逃跑既於己於友無益,在此世與冥間也都無好處。此節很要緊的一點是,法律承認蘇格拉底是含冤而死,但不是死於法律,而是死於判他死刑的雅典人。固然,若爲對抗冤屈而逃跑,反而真的成了罪犯,害的不只是自己和朋友,還有城邦和法律。就連冥間的法律也不歡迎抗法而死的人。法律此處的說法雖含有威脅恐嚇的成分,卻也不失其正當之處。然而,末了,法律要求蘇格拉底“不要聽信克力同,按他說的去做,不如聽我們的”。
聽從法律意味著甚麼?法律對蘇格拉底說,他是死於雅典人而不是法律,這表明法律已經把自己與城邦分開,而在我們先前的敘述中,它們是合一的。施特勞斯的分析發人深省:法律只能通過人才能行動,也即人制定法律且人執行法律。最要緊的是人制定法律,此時的法律乃是雅典民主政體下的法律;再有,不義的行動對人施加惡行,而法律不是人。如此我們難免推導出令人費解的結論:違背法律逃跑也算不上不義了?或許這些矛盾正是法律本身內含的矛盾,是克力同這樣的人難以覺察的矛盾。蘇格拉底如此呈現法律講辭,雖然揭示了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同時卻也表明,即便有缺陷的法律對於維持城邦秩序,對於說服克力同這類非哲學的邦民遵紀守法也行之有效。完美的法律是沒有的,法律的局限映襯的是人性的不完美。而哲人行動的抉擇並不依賴法律,因而法律的完美與不完美並非哲人遵守或違抗法律的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講,蘇格拉底的確是非政治的、“城邦外的”哲人。但蘇格拉底拒絕逃跑,默然承受有缺陷的法律施加於他的不義判決,最終成爲守法的邦民,就此而言,他又的的確確是政治的和“城邦內”的哲人。
五、神示
在對話結尾,蘇格拉底提及科魯班特療法,其用意何在?是法律的講辭充滿了蘇格拉底的耳朵,不可能再聽克力同的勸告?還是法律的話如同科魯班特人轟鳴的笛聲,而內心焦慮的克力同正好可以在喧囂中被治愈?而最終蘇格拉底仍舊聽從神的指引。此時的克力同終於被說服,樂於跟蘇格拉底一起“按照神的指引行動”。想要說服蘇格拉底逃跑的克力同反被蘇格拉底說服。我們的疑問是蘇格拉底爲甚麼給出兩次答復,兩次答復的內在理據又如此不同。蘇格拉底不可能不知道克力同是甚麼樣的心性,爲甚麼不直接用法律講辭來說服他?卻還要多費周折,重述他在申辯時已經公開講過的那些準則和道理?的確,兩次答復,兩種辯證法:哲學的辯證法說服自己和潛在的未來的哲人;而法律的說辭——蘇格拉底的另一種辯證法用來說服克力同,以及與克力同一樣的城邦民,使他們在“普遍接受的意見範圍內而導向(政治上的)一致”。
相對《申辯》之爲哲學辯護,《克力同》最根本的意圖似乎是爲政治辯護,這或許是施特勞斯把兩部對話放在一篇文章中解讀的原因。蘇格拉底借法律講辭說服克力同,卻還要先給出哲學的論證,乃是要用哲學論證映照法律論證的缺陷。然而,儘管法律論證有缺陷,它仍是我們必須遵行的準則,因爲在沒有或找不到關於正義問題的行家時,服從法律就是最穩靠地服從了正義。施特勞斯在《城邦與人》中提醒我們注意《王制》卷一(338以下)關於三種正義的討論:卷一講了三種依次上升的正義,一是克法諾斯的正義即欠債還錢;二是其子玻勒馬庫斯的正義即助友損敵;三是忒拉敘馬霍斯的正義即服從法律。在《克力同》中,克力同最終服從法律而放棄了讓蘇格拉底逃跑的念頭:這是否也是一種上升?的確,克力同至少從第二種正義上升到了第三種正義——有意思的是,這種上升還是哲人蘇格拉底引導的。
此文系2014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科研專項人文社科類重點項目“哲人正義與城邦法律——柏拉圖《克力同》譯注與研究”(項目編號:CQDXWL-2014-Z024)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References]
Adam,J.Crit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88.
Bentley,Russell.“Responding to Crito:Socrat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XVII.1(Spring,1996):1-20.
布倫戴爾,《扶友損敵:索福克勒斯與古希臘倫理》,包利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9。[Blondell,R.Helping Friends and Harming Enemies:A Study in Sophocles and Greek Ethics.Trans.Bao Liming et al.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9.]
Burnet,J.Plato's Euthyphro,Apology of Socrates,and Crito.Oxford:Oxford Universtiy Press,1924/1979.
陳建洪,《克力同與蘇格拉底:論〈斐多〉的文學特徵及其哲學後遺症》,收於《柏拉圖的哲學戲劇》,劉小楓、陳少明主編,上海:三聯書店,2003。[Chen,Jianhong.“Crito and Socrates:on the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and Philosophical Sequela of Plato's Phaedo.”The Philosophical Drama of Plato.Eds.Liu Xiaofeng and Chen Shaoming.Shanghai: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3.]
Coby,Patrick.“The Philosopher outside the City:The Apolitical Socrates of the Crito.”Law and Philosophy,the Practice of Theory:Essays in Honor of Geoge Anastaplo.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92.
Dyson,M.“The Structure of the Laws'Speech in Plato's Crito.”The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vol.28,no.2(1978):427-436.
荷馬,《伊利亞特》,羅念生、王煥生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Homer.Iliad.Trans.Luo Niansheng and Wang Huansheng.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10.]
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吳飛譯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Plato.Apology of Socrates.Trans.Wu Fei.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07.]
柏拉圖,《斐多》,楊絳譯,北京:三聯書店,2011。[---.Phaedo.Trans.Yang Jiang.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1.]
柏拉圖,《柏拉圖〈對話〉七篇》,戴子欽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Seven Dialogues.Trans.Dai Ziqin.Shenyang:Liaoning Education Press,1998.]
施特勞斯,《論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的申辯〉和〈克力同〉》,應星譯,收於《西方現代性的曲折與展開》,賀照田主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Strauss,L.“On Plato's Apology of Socrates and Crito.”Trans.Ying Xing.The Tortuousness and Unfolding of Western Modernity.Ed.He Zhaotian.Changchun: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2.]
施特勞斯,《論僭政:色諾芬〈希耶羅〉義疏》,何地譯,觀溟校,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On Tyranny.Trans.He Di.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06.]
韋斯,《不滿的蘇格拉底》,羅曉穎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Weiss,R.Socrates Dissatisfied:An Analysis of Plato's Crito.Trans.Luo Xiaoying.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1.]
色諾芬,《回憶蘇格拉底》,吳永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Xenophon.Memorabilia.Trans.Wu Yongqua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10.]
On the Structure and Intention of Plato's Crito
Plato's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vividly deomonstrated in Socrates'words and actions,and the Crito is a good example in point.Just like Xenophon's Socrates,Socrates in Plato avails himself of two kinds of dialectics,namely the philosophical dialectic and the non-philosophical dialectic,with the former one to show the justifications of philosophers and their lives and the latter the order of the(political)life of the city.The twospeeches in the Crito exhibit philosopher's justice and the law of the city respectively,and clarify Socrates'choice and the political-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embodied in it by contrast.This article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inner difference of the two speeches delivered by Socrateswith a grasp of thewhole structure of the dialogue and to reveal its intention.That Crito persuades Socrates to flee by resorting to the power of the people,friends,reputation,wealth,self-saving,and paternal responsibilities is in view of the opinions of the people,to which,however,Socrates replies that he will but only submit himself to“the best principles after deliveration,”which is an antithesis to the opinions of the people,as Socrates'sayingmeans that the justice of taking action lies in reasonable consideration.Furthermore,Socrates excludes“bad opinions”and“opinions of the fools”from the“sound opinions of the sensible,”i.e.,the opinions of the experts.The principle of Socrates'action is no other than the justice of the action per se.He proposes that“do not do evil on purpose”(repay one evil for evil),cutting down the chain of the relationships of actions buton the other handmaintaining the continuity of principles.Yet Crito cannot understand this speech of justice made by the philosopher,forwhich Socrates introduces the personified Laws which have given six reasons for notescaping,the first three general reasons exposing the defects of legal argument and the limits of laws,while the rest three admitting that Socrates is suffering from injustice in the light of his individual reasons.Socrates'insistance on obeying the law shows that law,though not perfect,can still in some extent keep the city in order.Socrates'choice,as itwere,makes him a philosopher whomatches his deeds to his words,and a good citizen observing law and discipline,whereby he defends not only the law of the city,but also the existence of philosophers in the city after him.
Socrates;dialectic;Crito;philosopher's justice;law of city
關鍵詞:蘇格拉底辯證法《克力同》哲人之義城邦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