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柏拉圖《泰阿泰德》“序幕”中的基要問題
賈冬陽
(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柏拉圖《泰阿泰德》的顯白議題是:“甚麽是知識?”這似乎意味著,蘇格拉底和泰阿泰德試圖探究“知識的本性”——所謂的“知識論”或“認識論”問題。但柏拉圖的“筆法”表明,蘇格拉底並沒讓“哲學”和“泰阿泰德”僅僅停留在試圖發現“知識”是“甚麽”,而是引導泰阿泰德在探問“知識”的途中领悟一种政治性的探問:爲何求知?換言之,單單追問所謂“知識論”問題,很可能丟失了柏拉圖更爲緊迫的教誨。在《泰阿泰德》的“序幕”中,柏拉圖以精微筆法深切暗示了这一点。就像一粒“種子”含蘊著一棵大樹的所有“潛能”一樣,柏拉圖精心設計的這個“開端”,也內在地爲《泰阿泰德》規定了“方向”,或者說提供了綱領性的線索:只有將一顯一隱兩個議題結合起來,柏拉圖的讀者才有可能領會,《泰阿泰德》或者說蘇格拉底—柏拉圖式的“靈魂學”所探問的,究竟具有怎樣的整全面相。
Author:Jia Dongyangis lecturer at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8,China).Email:12252436@qq.com在談到城邦護衛者的“教育次第”時,蘇格拉底對阿德曼圖斯(Adeimantus)說,“凡事開端最重要”。這句話適用於柏拉圖的任何一部作品。據說,柏拉圖爲其對話的“開篇”煞費苦心,以便引領讀者,使他們“在力圖理解這篇對話的整體時理清自己的方向”。
那麼,《泰阿泰德》的“開端”會將我們引向何處?
柏拉圖以一個不同尋常的“序幕”開啟了《泰阿泰德》。或者說,《泰阿泰德》的獨特之處,首先表現在它擁有一個如此不同尋常的“開端”。據說,這個“序幕”並不是此篇對話原有的部分,而是後加上去的,先前有一個更枯燥的。這個後加上去的“開端”意味著甚麽呢?表面看來,“序幕”與“正文”相分離,只是爲了交代一場三十年前的交談是如何開始的。但事實上,這個“開篇”或者說“序幕”非常豐富,充滿意味深長的暗示。就像一粒種子含蘊著一棵大樹的所有“潛能”一樣,柏拉圖精心設計的這個“開端”,也內在地爲《泰阿泰德》規定了方向,或者說提供了綱領性的線索。我們必須嚴肅地對待它。
一、泰阿泰德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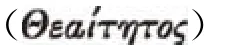
不算“書簡集”,在柏拉圖傳世的35部對話中,明確以人物爲主角的有27篇,其中更有25篇直接以某個人物的名字命名。除了神話人物“米諾斯”外,其他幾乎都是實實在在的歷史人物。據此,我們似乎可以確定,在“戲劇筆法”之外,柏拉圖的寫作還有另一個重要特徵——“史家筆法”,或者說柏拉圖的寫作帶有一種鮮明的記事烙印。這一筆法,進一步加強了他爲蘇格拉底辯護的特徵!既然如此,還有必要問泰阿泰德是誰?
泰阿泰德不就是那個在古希臘數學史上鼎鼎大名的數學家麼?作爲一個畢達哥拉斯主義者,泰阿泰德以無理數理論和正多面體理論爲自己贏得了不朽的榮譽。在逍遙學派的歐德穆斯(Eudemus)看來,泰阿泰德堪稱公元前五世紀最偉大的幾何學家之一。傳諸後世的《幾何原本》蒐集、融匯了許多前人的成就,其中就包括泰阿泰德的無理數定理。史記昭昭,爲甚麽要問“泰阿泰德是誰”?
倘若如此,那麼柏拉圖記述的也許不過是這個歷史人物的少年往事,在某種程度上,《泰阿泰德》可以滿足數學史家的歷史好奇心。可是別忘了,柏拉圖的寫作除了“史家”筆法,同時還有“詩”(哲學戲劇)的特徵。施特勞斯提醒我們,柏拉圖“從未保證過,他筆下的蘇格拉底談話是真實的”。換言之,我們如何確信《泰阿泰德》不是柏拉圖爲了“淨化”某種靈魂類型而講的一個“虛假的故事”?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可以說,柏拉圖的“史家筆法”與“戲劇筆法”混合交織在一起,“詩的真實”包含並高於“歷史的真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面對的只是“柏拉圖底泰阿泰德”!無論如何,“泰阿泰德”這個名字,讓我們的閱讀從一開始,就與一個活生生的“形像/樣子”聯繫在一起。

忒赫珀希翁:斯人竟遭此難!

忒赫珀希翁:毫不奇怪,若不如此,那才稀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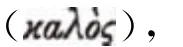
換句話說,三十年前,還是個毛頭小子的泰阿泰德,憑其“天資”和數學上的非凡成就而贏獲美名,這種美名不同於“軍功”,不是一種政治性之美,而是“數理之美”。這一區分激發我們思索這樣的問題,從一個數學天才到城邦的護衛者,泰阿泰德是如何實現其靈魂之潛能的?如果說,“人應該如何生活”是蘇格拉底關切的核心,那麼,再也沒有比《泰阿泰德》的序幕更適合提出這一問題了。
事實上,柏拉圖的讀者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柏拉圖讓歐幾里德來讚揚泰阿泰德的軍功,是在故意搞笑或反諷。爲甚麽這麼說?因爲雅典曾與麥加拉交惡,並給麥加拉人帶去了深重的苦難,讀讀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便知。讚頌與母邦有宿怨的敵國公民的軍功,表明歐幾里德要麼沒有政治頭腦,要麼根本不關心政治,總之,是一種“非—政治”的生存身姿或者說靈魂狀況。還有一個例證。據說,即便在麥加拉與雅典高度敵對時期,歐幾里德也常常“穿著女人的衣服潛往雅典”,爲了能見到蘇格拉底,聽他談話。這則“逸聞”加深了我們前面的判斷——作爲一個數理哲人,歐幾里德是非—政治性的人,或者說他對政治事物沒有生命熱情……
柏拉圖如此筆法有何深意?
我們已經看到,柏拉圖用泰阿泰德和蘇格拉底兩個人的政治性“死亡”框住了整部對話——這讓《泰阿泰德》的“序幕”籠罩在肅劇的氣氛之中——但,讓我們驚訝的是,泰阿泰德和蘇格拉底兩人一生之行止,都被稱頌爲“既美又好”,但他們的政治性之死卻截然對立。泰阿泰德爲之獻出生命的城邦,同樣也是處死蘇格拉底的城邦。通過思索這種並置,我們或可得以領會,爲甚麽柏拉圖如此鮮明地突出“序幕”中的“政治處境”。更重要的是,通過該處境,我們將被引向對話的主題——知識的本性——這似乎遠離任何政治關懷。
二、歐幾里德與麥加拉學派
麥加拉人歐幾里德是《泰阿泰德》的記錄者,而柏拉圖自己則充當了歐幾里德與其弟子的戲劇性開場的記錄者。通過並置“兩個記錄者”,柏拉圖的“意圖”與歐幾里德的“記憶”對立起來,二者之間有明顯的分離,這種“分離”意味著甚麽呢?問題是,柏拉圖爲何要安排一個麥加拉人來記述這場關於知識本性的對話?要想回答上面的問題,首先要問:歐幾里德是誰?
他不是寫作《幾何原本》的那位同名數學家,而是來自伊斯特摩斯地峽的麥加拉人。此人——包括忒赫珀希翁——與蘇格拉底關係匪淺。蘇格拉底飲鴆前曾與一群哲學青年在獄中談論自己的“第二次起航”以及“靈魂不死”,當時,歐幾里德和忒赫珀希翁都在場(《斐多》59c),但二人自始至終都未發一言,始終保持沉默——值得注意的是,當歐幾里德的童僕開始誦讀蘇格拉底與泰阿泰德的交談記錄時,二人同樣保持了沉默,這意味深長的沉默貫穿始終。更早之前,當蘇格拉底在獄中靜候前往德羅斯島祭祀阿波羅的船返航時(《斐多》58ac),歐幾里德就經常來探訪他(《泰阿泰德》142d-143a)。由此可見,歐幾里德對蘇格拉底始終充滿欽佩之情,即便在蘇格拉底死後三十年,因爲偶遇聲名卓著又奄奄一息的泰阿泰德,這種情感仍在歐幾里德心中油然而生。
根據第歐根尼·拉爾修的記述,我們還知道——
歐幾里德,他致力於研究帕默尼德的作品,人們把他的追隨者稱作麥加拉學派,然後又稱作論辯派,再晚些時候還稱作辨證論者。……他認爲,善實際上只有一個,雖然它有很多名稱來顯示;因爲,有時叫它智慧,有時叫做神,另外的時候也叫做理性,等等。他否認一切與善相矛盾的東西,宣稱它們是不存在的。
這段記述中有幾個要點值得注意:第一,歐幾里德創建了麥加拉學派;第二、該學派致力於研究“帕默尼德的作品”;第三,它結合了埃利亞派與蘇格拉底的教誨並因此主張:“善”雖名目眾多,實則爲“一”,唯“善”存在,與善“相異者”皆不存在;第四,爲了證明這一點,他運用了智術師式的“詭辯”並因此著稱。難怪,提蒙在提到他的時候說,愛爭吵的歐幾里德“帶著對辯論的瘋狂創立了麥加拉學派”(同前,2.107)。
在《形而上學》(1047a15-20)中,亞里士多德對麥加拉學派吉光片羽般的描述,有助於我們理解柏拉圖選他作爲對話記錄者的深刻用意——
[麥加拉學派的]這些觀念消除了運動與生成。照此觀念,站著的將常站著而坐著的則常坐著;亦即坐著的無法站立,因爲不能站立者就無法站起來(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1047a15-17)。
麥加拉學派取消了“運動與生成”,即取消了“潛在的可能性”而只堅持“絕對的實在性”。在他們看來,沒有甚麽能夠成其所未是,或者說無論何物,總如其所是(《形而上學》,1046b29以下)。然而,否定“運動與生成”,就意味著人的發展或成熟、目的與方向,甚至生和死,都變得不可理解了。倘若如此,柏拉圖讓歐幾里德對蘇格拉底關於泰阿泰德靈魂潛能的“預言”表現出的“驚訝”,就充滿了反諷!我們要注意在此反諷中顯現出的“分離”——“靈魂”與“身體”相分離,“觀念”與“行動”相分離,“高”與“低”相分離——麥加拉學派信奉的“理論”否定“運動與生成”,致使“靈魂”陷於停滯。但在“序幕”中,柏拉圖的精妙筆法卻讓我們看到,歐幾里德與忒赫珀希翁的“身體”卻實實在在處於運動與變化之中——

忒赫珀希翁:到了好一會兒了。我在市場上找了你半天,還擔心找不到你。
歐幾里德:難怪,那會兒我不在城裏。
忒赫珀希翁:去哪兒了?[a5]
歐幾里德:下到港口去了,碰巧遇見泰阿泰德,正被人從科林斯的軍營抬回雅典。
在“序幕”中,柏拉圖以多種方式展現了歐幾里德與忒赫珀希翁“身體”方面的“運動”。這種“知—行”分離,爲《泰阿泰德》的“開端”鋪就了濃濃的諧劇色彩。倘若沒有忘記因“蘇格拉底之死”和“泰阿泰德之死”而產生的肅劇氣氛,我們就會發現,柏拉圖成功地展示了蘇格拉底在《會飲》結尾處所宣稱的高妙的混合筆法——“同一個人可以兼長諧劇和肅劇”(《會飲》223d)。如果說,“肅劇”顯示了人性中“高”的部分,“諧劇”展現了人性中“低”的部分,那麼,《泰阿泰德》開篇中的這種混合性特徵,就顯得是在提醒我們注意,在一場對“知識本性”的探問之旅中,蘇格拉底將如何超逾各種對人性的片面理解而貫通高與低、知與行、同一與差異……
麥加拉學派的絕對一元論,與堅持相對主義“流變”學說的普羅塔戈拉剛好“各引一端”,針鋒相對。但令人驚訝的是,在對待泰阿泰德“靈魂潛能”的問題上,二者卻結成了同盟——麥加拉學派從根本上否定“潛能”;普羅塔戈拉雖鼓吹“流變”,卻得出與歐幾里德殊途同歸的結論:泰阿泰德的“靈魂”不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實現其“潛能”,因爲這種“實現”必須以一個“具有延續性的自我(enduring self)”爲前提,而這個前提是普羅塔戈拉的相對主義無法接受的。在這個意義上,歐幾里德和普羅塔戈拉雖分處“兩端”,實則“一體兩面”,誰都不具有“悖論式差異”的整全視野。因此,他們無法理解蘇格拉底的眼光,換言之,無論在哪一端看來,蘇格拉底對泰阿泰德靈魂之潛能的考察都將毫無意義。斯特恩(Paul Stern)的說法可以拿來作爲一個注腳——
這兩種觀點都否認一種具體人類生活的關鍵特徵,即它被人們看作一種生活(as a life)的能力,看作一個包含著所有無法避免的變化的整體,並且因此,看作同時帶有穩定性和流動性的某種方式。
總之,無論歐幾里德還是普羅塔戈拉,都不可能正確對待泰阿泰德的靈魂。而蘇格拉底則試圖證明,泰阿泰德的靈魂同時擁有“持存性”與“潛在性”。事實上,《泰阿泰德》正是始於蘇格拉底對某種特殊靈魂類型的關切與憂心。至此,“泰阿泰德是誰?”這個問題的真正意義才顯露出來(同上,頁30)。通過一個人靈魂潛能的延展與實現,它連接了“知”與“行”、“同一”與“差異”。這對我們理解“知識的本性”意味著甚麽呢?
上述兩種學說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兩種更古老的思想的不肖子嗣。隨著對話的延展,兩種更古老的思想將漸次出場——“萬有歸一”與“萬物流變”——共同構成蘇格拉底與泰阿泰德交談時的“思想處境”!我們關心的問題是,蘇格拉底的身位或者說立足點在哪里?柏拉圖讓我們看到,蘇格拉底既非“歸一”派,亦非“流變”派,因此,“知-無知”的蘇格拉底必將受到來自兩端的攻擊——“歸一”派必將攻擊其爲歷史主義、相對主義,歸根結底乃虛無主義;“流變”派則必將指摘其爲獨斷本體的本質主義、普遍主義。在“絕對”與“虛無”之間,臨界哲人如何執兩端而扣中庸?
三、“時間缺口”:在絕對與虛無之間
“序幕”或確切地說柏拉圖的“筆法”告訴我們,這部對話經由了“雙重轉述”——蘇格拉底與泰阿泰德的交談發生在一個無名運動場內(144c),當時歐幾里德並不在場。後來,蘇格拉底在獄中將對話內容轉述給歐幾里徳。但歐幾里德的“記性”實在不夠好,不像斐多那樣僅憑“回憶”就能復述對話的全部內容,而是回家後要馬上起草備忘錄,然後再憑記憶寫下來(143a以下)。但即便如此,還是記不全,後來歐幾里德又去監獄反復問了幾次蘇格拉底,記下的東西才“極爲接近完整的談話”(143a以下)。我們現在讀到的文本,就是歐幾里德在家中讓童僕念給忒赫珀希翁聽的筆記中的內容——一份經過“雙重轉述”,亦即“模仿的模仿”的文本。我們不禁要問:以蘇格拉底的“知人之智”,他肯定清楚甚麽是平庸的歐幾里德能夠勝任的,甚麽是他不能夠勝任的。那麼,在死亡即將到來之際,雖身在獄中,蘇格拉底仍積極協助歐幾里德“製作”並“出版”這樣一部包含著自己“自畫像”的“作品”,究竟想要借歐幾里德傳達出怎樣的自我認識(selfknowledge)?他想讓甚麽人或何種靈魂類型的潛在讀者在他死後也能聽見這些傳遞“自我認識”的言辭?
爲了避免談話中間的“旁白”使記錄變得囉嗦,歐幾里德刪去了蘇格拉底的“我說”、“我答道”、“他同意”或“他不同意”等詞語(《泰阿泰德》143c以下),從而將蘇格拉底的“敍述體”改成了“演劇體”——在這一過程中,壞記性的歐幾里德又丟失了甚麽?——這種改動讓我們覺得,三十年前的對話猶如發生在“當下”。斯特恩敏銳地發現,通過這樣的“修改”——
歐幾里德排除了敍述體中所包含的時間語境。他敉平了解釋與事件之間的時間缺口(gap),該缺口的存在能提醒我們:變幻莫測之流(the vagaries of flux)支配著我們的知識。
這一“時間缺口”墓碑般尖銳地提醒或反諷著探求“知識”的人們,在實事、懷疑與反思之間,有著不可彌合的時間缺口,任何試圖敉平這一時間缺口而構造同一性/確定性知識的努力,都不過是爲本體論戰場增添了新的頭蓋骨而已;但,這是否意味著,人們只能陷入“虛無主義的河流”或“極端的唯我論’——人是萬物的尺度?“記憶”與“回憶”對這個“時間缺口”又意味著甚麽呢?它們能將我們從無岸無底的虛無之河中救起嗎?

憑藉上述思索,我們或可得以穿過“序幕”……
*本文受海南大學科研基金項目資助,項目名稱:“重读西方哲学史”,項目編號ZXBJHXK027。
參考文獻[References]
Clay,Diskin.“Plato s First Words.”Yale Classical Studies 29(1992):113-129.
Dorter,Kenneth.Form and Good in Plato s Eleatic Dialogues:The“Parmenide,”“Theaetetus,”“Sophist”and“Statesman.”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Levels of Knowledge in the Theaetetus.”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44,No.2(Dec.,1990):343-350.
Halperin,David M.Plato and the Erotics of Narrativity.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Suppl.vol.Ed.Julia Anna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
Harrison,Joan C.“Plato s Prologue:Theaetetus 142a-143c.”Tulane Studies in Philosophy 27(1978):103-123.
Heath,Thomos.A History of Greek Mathema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1.
郝嵐,《政治哲學的悖論:蘇格拉底的哲學審判》,戚仁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Howland,Jacob.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Philosophy:Socrates Philosophic Trial.Lanham:Rowman &Littlefield,1998.]
克萊因,《柏拉圖的三部曲:〈泰阿泰德〉、〈智者〉與〈政治家〉》,成官泯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Klein,Jacob.Plato s Trilogy:Theaetetus,the Sophist,and the Statesman.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7.]
Lutz,Mark.Socrates Education to Virtue:Learning the Love of Noble.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
Rosen,Stanley.“Dynamis,Energeia,and the Megarians.”Philosophical Inquiry 1.2(1979):105-119.
Stern,Paul.Knowledge and Politics in Plato s Theaetet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Strauss,Leo.The City and Ma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Witt,Charlotte.Powers and Possibilities:Aristotle vs.the Megarians.Proceedings of the Boston Area Colloquium in Ancient Philosophy.Vol.XI.Eds.John J.Cleary and William Wians.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5.
Some Basic Issues in the“Prologue”of Plato s Theaetetus
The exoteric teaching of Plato s Theaetetus is about“what is knowledge,”rendering us an impression that Socrates and Theaetetus are trying to investigate“the nature of knowledge,”namely the issue concerning“the theory of knowledge,”or“epistemology.”However,Plato s art of writing shows that Socrates is not satisfied to let“philosophy”and“Theaetetus”just rest on the finding of“what”“knowledge”is,instead he encourages Theaetetus tocarry out a political kind of inquirywhy knowledge?in the process of the exploration of“knowledge.”In other words,it is bound to lose hold of Plato s more earnest teaching if the inquiry is merely focused on the issue of“the theory of knowledge,”which is skillfully hinted in the“prologue”of the Theaetetus.Just like a tree s“latent energy”is hidden in the“seed,”this welldesigned“beginning”sets the“direction”for the dialogue,or provides some programmatic clue:only if when the readers combine the exoteric and the esoteric,i.e.the philosophical issues and that of politics together,can they get to know that the inquiry of“knowledge”in the Theaetetus,or in the SocraticPlatonic“psychology”is in the final analysis a knowledge about the souls of human beings,meaning that Socrates investigation of“knowledge”and his seeing it as“the highest,”is not out of a passion for“natural science,”but a result of his dedication to“guiding peopl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ls of human beings.”Through an inquiry into“the nature of the soul,”Socrates makes it known what the beauty and the ugliness,the goodness and the vice,as well as the fortune and the misfortune of the soul are,thereby guides the particular souls to deliberate on“what kinds of person they are going to be,and what ways to take to have a good life.”To put it another way,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ratic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the highest knowledge”is divine,and human reason can but know how to approach while by no means obtain the real knowledge.Being a love for wisdom,what philosophy finally acquires is simply“a knowledge of ignorance.”And it is this special kind of moderate knowledge that teaches and guides Theaetetus and readers of later generations to the beauty of“the harmonious order of the soul”and that of“the life which is worthy”when the“soul”is led to a human“moderation”for its selfrecognition of its own“ignorance.”
Socrates;Plato;Theaetetus;Eucleides;knowledge
關鍵詞:蘇格拉底 柏拉图 泰阿泰德 歐幾里德 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