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长江丛刊》编辑部
时间:2018年5月27日至30日
地点:江城武汉
主持人:夜鱼
嘉宾:刘洁岷、黄斌、盛艳
夜鱼:《长江丛刊》决定持续组织开展“长江诗歌沙龙”讨论,并自本期评论版开始,陆续发表讨论内容。本期邀请刘洁岷、黄斌和盛艳三位实力诗人批评家做客长江诗歌沙龙。讨论题目:“主题与技艺:当代河流诗写的变迁”。“河流诗写”主要是指创作主题,也是自然文学的一部分。江河流域的生活背景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讨论将以具体的诗歌作品为对象,围绕诗歌创作与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讨论技艺在主题表现上所起的作用,以及河流诗写在不同语境下的变迁等。下面有请各位自由发言。
刘洁岷:新诗草创时期,1919年周作人在《新青年》(六卷二期)发表了小长诗《小河》,成了突破旧体诗桎梏,开新诗诗体解放的先“河”,其口语化、象征内涵、结构组织、情境展开乃至叙述性和戏剧性都达到了不可小觑的成就,值此新诗百年,周诗也近百年之际讨论汉语的河流诗写,不单是一个题材、主题问题,深入探讨,也许会有更多更大的启示性意义。
黄斌:河流诗写?我的直觉是又一个诗歌概念的泡沫,和我们以前谈乡土诗、城市诗相当。在我的印象中,诗经第一首第二句,在河之洲,是不是也可以叫河流诗呢?土地与河流,一直是我们生活的背景,诗歌也大多是在地的,诗人更不用说是在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人生存于大地山川中的自然反应,过去如此,以后也如此。
如果从当代新诗的角度,写河流的诗句也是随手可撷的,因为这本就是一个背景式的存在,是诗意生发的恒定基础。从正面看这个提法,我在想,是什么因素让我们突然注目于新诗的河流诗写,是不是河流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我们的在地性出了问题,从而需要特别去关注吗?
盛艳:今天讨论的河流主题是一个镜像的概念,它不是被直接书写的。旧体诗和抒情诗中会看到对于河流的直接抒情。在现代诗中的河流主题通常是动态的,在河流的变迁中,它具备水的流动与蔓延甚至是枯萎干涸,随之会有人的经历变迁,由此引发的身份疑问,还有以河流为代表的环境与人的关系阐发,也有从人的角度对于记忆与当下,乃至未来的经验投射。
刘洁岷:水为五行之首,对于肇始于农耕文明的国度,河流乃图腾般的原型,河流诗写是再司空见惯不过了,既是古典诗歌的基本意象,也是新诗里的一个随手拈来的元素。我们“煞有介事”地专题讨论河流的主题和技巧似乎多余,黄斌之问,是一个从事创作的诗人的本能反应,因为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望文生义的关于某某诗歌题材和主题的评论,那种不深入具体语境和固化内涵的“研究”实属鸡肋之文。而且,诗歌的优劣不在于选择的主体,因为文学的母题是循环的变的是书写它的方式。但我们在这里研讨的“河流”不是静止抽象地谈论河流诗歌,而是结合河流诗歌探究其中的经验重构、身份想象以及生命欲望乃至民族魂魄想象的投射,其在不同的时期文本呈现太值得比较咂摸了,而且同一时期的诗人在同一个主题上的交叉叠合与分歧对立,也便于我们认知其精神构造与诗艺得失吧。
夜鱼:那就深入具体语境来看看周作人的《小河》吧,在白话诗刚启蒙的时候,就有了诗歌理念如此超前的作品,即便和我们当下的诗歌比,也不逊色。同时代比较受推崇的新诗代表人物,语言上都或多或少地有着新旧纠缠的磨痕,读者必须设身处地在当时的语境下去理解,而《小河》没有障碍,好好儿地说着话叙着事。虽然运用的修辞现在看来有点幼稚,但他对大多文艺腔调的同时代诗歌的冒犯,还是具有相当价值和意义的。

夜鱼,本名张红,祖籍江苏东台。现居湖北武汉。十一届武汉市签约作家,《长江丛刊》作品版副主编。出版诗集两部。
黄斌:周作人的《小河》,虽有新诗开拓之功,终究乏善可陈,才在河流诗写的层面考察这首诗。在经典性和传播力上考察,《小河》肯定无法和《关雎》《汉广》相比。多多有首诗《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感觉不错,有一种铿锵的语调和冷峻的诗境,在写作上也显得紧凑,比较成熟。而《小河》明显是不成熟的。似乎并没有构成这样的体量。
河流诗,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提出来,如果没有文学史现象的诉求,而只是作为一般的诗歌写作内部的价值和技巧的讨论,我认为也不是不可以。也就是说,把范围缩小至新诗写作内部,对文本进行分析和批评,作出如其所是的考察和研判,从而以某种进化论式的眼光,给出某种可能的写作路径。只是我有点担心,在当下多元和融合的写作氛围中,任何结论都有可能陷入独断的嫌疑,可能我之所喜正是彼之所恶。我们的本意和良好的初衷,原是为了呈现新诗写作的更广阔的可能性,但一旦研判下来,也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武断和对可能性的遮蔽。
比如刘洁岷说,去意象化,在“朦胧诗”之后,获得了比较一致的支持,但我的疑问正好在这个研判中发生。我认为,对一首还没有写出的新诗而言,不管是河流诗还是山水诗,任何技巧都是可以运用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允诺新诗及其写作的自由。我们是面对未来写作,那尚未现身的未来,没有任何禁区,只有当它出现,我们才能看清其面相——它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刘洁岷, 湖北松滋人,2003年命名并创办《新汉诗》,2004年创设《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名栏,2016年创办“新诗道”订阅号,出版有《刘洁岷诗选》《词根与舌根》等,编选出版有《群像之魅》等多种诗学论集。现居武汉,为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主任,编审。
盛艳:同意。问题的指向在于一个优秀的现代诗人会用何种技巧切入,他一定是有预设的,会避免一些创作陷阱,或者是虚晃一下,让人以为他已掉入窠臼,其实并非如此。诗人在创作中的几条重要原则,我觉得要避免泛滥的抒情,避免不断重复之前文本。
刘洁岷:黄斌说了对《小河》的现代诗史上的评价,很认可,又从“当代”的视角进行了判断,不怎么认可,我直觉与他颇不一样。考虑到百年前的语言资源和整体诗歌语境,这首《小河》品质还是很突出的。
中国诗坛的面貌不是抽象的,它是由一个个阶段、一个个小时代组成。各阶段或时期的诗人群体形象也是由一个个有代表性的诗人主体形象构成的。诗人之间的差异,在风格、风骨、风尚之外、之中,如果我们欲探讨整体、历时性,还得从局部、个体入手,从具体的文本的自我比较、相互比较中,探寻发现他们在同一主题上的差异、分歧与共生、共鸣,(“技艺”也必然融汇于其中)如此,可以“测绘”出其诗歌的深度与广度、心灵的动态构造。
“河流意象”早先是自然的说法,但朦胧诗以后,诗歌创作风潮在反“意象化”上是比较一致的,即便是走意象性写作的,与前期意象诗歌也有了很大的区别。即便现在看来还有一些“意象主义”成分的海子、骆一禾也针对“意象”有所警惕。海子提倡“意象与咏唱合一”,骆一禾诟病了“意象叠加”式的创作。将河流称为“心象”还为人们所认可一些。我们把“河流”在此确定为“主题”是强调其在汉语诗歌的塑形中的巨大可能性——是对河流诗歌的动态表现能够承载的“水源意象”(西渡)和“水缘诗学”(米家路)的强调,这也会在我们的研讨中逐步有所揭示。
多多《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是多多出国后写下的第一首诗,该诗值得专文细读,其心灵体验性的非凡喻象甚至断行断句都可圈可点。
盛艳:河流塑形的巨大潜能,也不是说不能直接写,如果直接写,那么对河流的直接书写又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构建,诗中的河流之景并非是我们目力所及的景物,它融合了心理层面,文化层面,类似于集体无意识,这个在现代诗中其实更难。
夜鱼:我把刘洁岷提到的诗人匆匆读了些,印象最深的是昌耀的《斯人》:“静极——谁的叹嘘?//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援而走。/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至于其他作品我还没来得及细品,先听各位老师高见!
黄斌:夜鱼提到的《斯人》,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当时未经对诗歌语言进行本体性反思的写作环境中,这首诗显得极简,极富张力。这么说吧,就像现在的微信界面的首页,一个人站在蓝色星球的下面,类似这种诗境。
夜鱼:从创作者角度,这类极短又极富张力的诗的产生,我的经验那是灵光一现,不会去考虑别的。当然本体性反思,是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不可说没有影响。还有昌耀、海子的河流长诗、组诗,那种铺张的恣睢的高调诗写方式,似乎也潜移默化了许多人,虽然不乏结构上的隐喻构建,但带着那个时代文学风尚的印痕,如何从诗学角度进行研判呢?我们先具体谈谈昌耀吧。
盛艳:昌耀的《河床》不写河流而写河床,使诗更为雄壮。视角的转换,使诗的傲气源自内部,而不是诗人对河流的外在阐发,整首诗歌的可信度更高。“我是父亲”这一句放在诗歌的中部,夹在长句中间,简洁有力,使得前文的一切拟人有了落脚,而又和后文的“消失的黄河象”联系,形成了从地域的广阔的横向跨度,到时间的纵向跨度的微妙的转换。而最后的一句,有生命不息的感受“我答应过你们,我说潮汛即刻到来,/而潮汛已经到来……”这也和黄河象相呼应。整首诗的词语粗犷而富丽,色调上也是极其丰美,感觉整个色泽是蓝和白,浅色,而其后的夜晚,也是有团圆月的明亮之夜。居然消解了前文中的黄河象中本应该产生的悲凉。而就连悲凉也不需存在,因为“我在每一个瞬间都同时看到你们。”
刘洁岷:昌耀的《斯人》算是名作,但如果我们熟读《登幽州台歌》(陈子昂)、《断章》(卞之琳)、《公园里》(普列维尔)之后,娴熟了诗艺中时空对比的手法,再判断的话也就是一则还不错的小品。荒诞派诗人祁国写过《自白》“我一生的理想/是砌一座三百层的大楼//大楼里空空荡荡/只放着一粒芝麻”。玩的是纯语言游戏,也算是展示了一种空间反差的语言技巧。那种“空灵”之作只是一类,对当代诗歌的覆盖度也是有限的吧。
盛艳:我也觉得《斯人》类似俳句在诗歌形式上就占据了仿古先机。
夜鱼:从技巧上看,大家说得都有理,但我保留自己的看法,“空楼放芝麻,”显然不能和“那边攀援这壁无语独坐”的意境相媲美。道法合一,内容和技巧是不可分割的。另外,骆一禾的《大河》,我也相当欣赏,直觉出创作者的真诚和技术的精湛。
盛艳:我看这首《大河》就想起我的爷爷,我爷爷是船工,我爸爸十八岁的时候就在船上的事故中去世了。我爸爸有时候讲他小时候在船上生活的故事,就和这首诗给我的感觉一样。
黄斌:骆一禾这首《大河》,显示了较强的叙事性,细节描写准确精当,也不乏势大力沉的诗句,整体看,我认为是首上乘之作。不过,结尾的处理,似略约平淡了些,虽然是客观的描写,但让人读来,觉得还客观得不够。此诗中,“我们的衣领陈旧而干净”“蓝色的门廊”“老锈的锋利的船头”,这些经验的痕迹并呈,似加入了一次合唱,各现其声,叙述很丰满充实。拥挤不堪的甲板,如黑白电影中的一座大床,睡满了素不相识但又共享着同一种命运的人类。这有如展出一张旧照,把消逝的人生经验独截一面。这种呈现无疑是诗意生成的技艺,并呈,各有其独特的内蕴。“我们没有经验”“我们还远远没有懂得它”,这一气呵成的两句,当为此诗的诗眼和高音。经验因没有经验,从而开始了经验之旅。不懂之作为懂的前提,也使得“懂”在生成并逐渐生成和充实的途中。我的阅读在此获得了共鸣,并觉得这首诗有了近似河水的流动和船的行进这种相交互的动感,阅读感觉像船头的水沫,泛起,而后落下;落下,又接着泛起。
夜鱼:很高兴二位和我有同感,对比昌耀的呢?
刘洁岷:昌耀的《河床——<青藏高原的形体>之一》气势之雄浑激荡让我想到聂鲁达的长诗《马楚·比楚高峰》,也想到张承志的小说《北方的河》。起笔“……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的造境非常得力,一种鸿蒙初开的神话般的味道就出来了。水是女性意象,所以反过来以此诗书写“河床”以展示“刺肤文身……向霜风展示我体魄之多毛”的父亲形象。在笔法上,昌耀采取了极具创造性的描绘与烘托。此诗写于1984年,昌耀个人劫后余生,那是一个社会剧烈转型,一种初具狂飙突进气象的年代,作者以从黄河源头奔向大海的澎湃,用神话—诗性的结构,呼唤着一种民族的崇高精神和创造的伟力。河床—河流共构了民族振兴、文化复兴冲动的精神景象。此诗与其同时代的海子、骆一禾的河流书写在史诗情结、史诗意识上好有一比,与同时代的牛波、于坚、聂沛的河流诗判然有别。另插一句,相较此诗的雄性壮美,苛刻点说,李白那首《将进酒》也只能算是臣子贴上胸毛的豪迈。
黄斌:不过,我觉得昌耀的《河床——<青藏高原的形体>之一》《划呀,划呀,父亲们:献给新时期的船夫》这两首诗经典性不够。原因有二:一为整体上的不足,二为诗句中的多余。前一首好一点,还有些异域风情;后一首像在写生命起源,与其说是史诗意识,不如说写的是史前诗,但两首诗整体上都有欠缺,前一首诗感觉黄河还没流出青海,更别说流到华夏文明的腹地了,后一首几乎看不到人文的闪耀,只体现了生命意志。至于诗句的多余,就不列举了,很多。在衡量文本的经典性上,还是要有一把奥卡姆剃刀,看一看有没有可剪掉的冗枝赘叶。
刘洁岷:《河床》在那一路水准相当高!《划呀,划呀,父亲们》现在看来是明显弱了。我们在这里不是单按自己写诗的喜好来看待,而要从“史”的角度,从诗歌创作的动态发展来评价。
黄斌:我们现在的观点和看法,就是因为已经站在了他们肩上,他们的历史贡献,自当无法否认。我们这种”严苛”,也是向他们致敬的方式。
夜鱼:接下来的一个诗人我要向他致敬:于坚。《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写得多好啊,“它无法再往下它缺乏石头的重量”,什么时候,我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整首诗水到渠成,没有任何不适,似乎所有的象征和隐喻就该是这样。
盛艳:于坚这首诗,水在这里被分开了,上面的水,下面的水,上面的水在阳光中,下面的水在黑暗中。河流的身躯,河流其实也和水分开了。这个和海子是一样的。水本身就是很大的隐喻。水的生殖,繁衍,介乎实体与非实体,水的明亮,幽暗。河流的哲学意味很浓,石头没击碎河流,它一沉到底,而河流在不停的变化,不断的改变着。
黄斌:于坚这首诗还是有点象征主义的味道,“深处的黑脚丫”,像匿名在社会底层生活中的苦力,结尾那个龙的意象,也很通透。看来,隐喻和意象,他用得挺娴熟。

黄斌,1968年4月出生于湖北赤壁,199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居武汉。出版诗集《黄斌诗选》(2010),随笔《老拍的言说》(2016)。
夜鱼:好,再回到海子的河流组诗。刘洁岷说的海子、骆一禾河流书写有史诗情结、史诗意识,那么他们与同时代牛波、于坚的河流诗的区别是什么呢?
盛艳:海子《河流》中的河流存在着阴性和阳性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是由孕育和分娩完成。海子以几乎童话白描的手法开篇,写了河流由微到宏的诞生与变化,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力量的把控,细腻有,力量也有。
牛波的《古老的波涛》塑造了幸存者的形象。雷电与阳光的转换,再到雷电与云母片的转换。虚幻的河流上的幸存的水手是谁?远看是独木舟,靠近了却觉得是渡船,为什么?矛盾在于现实的渡船没法水天相接,如果水天相接那么就不是渡船,就算是渡船,也是渡过大海,这样才会“是孤帆远影碧空尽”,才有可能有滑过天空的姿势。而古老界限,似乎就是河流这边和那边,这里又有点像忘川之水,船于夕阳中划走驶向幽暗的黄昏。棕熊的意象来得有点突兀,这个也和写作惯性有关,水手的焦黑的船与水手的健硕叠加,就会得到棕熊的意象。关键在于水手把船划去了哪儿?地图上未出现的大河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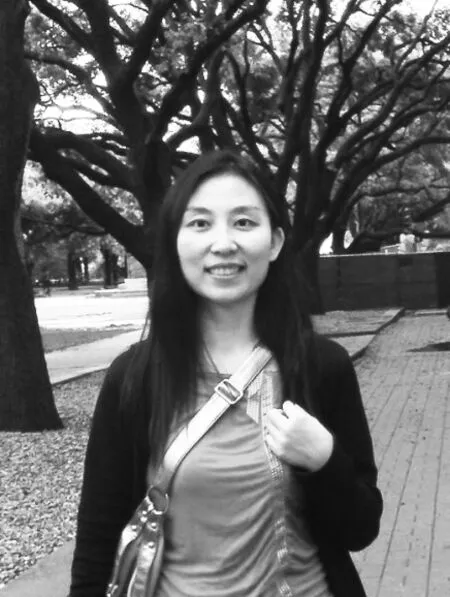
盛艳,诗人,译者,诗歌评论人,现执教于中南财大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汉语现当代诗歌。
夜鱼:佩服盛艳对《古老的波涛》的探究,我读此诗如同猜谜,觉得晦涩,汉语原本就有着无限的言外意,何必刻意制造阅读障碍呢?
刘洁岷:构造抒情史诗的抱负使得海子和骆一禾分别展开了长诗的书写。海子写下了长诗《河流》《传说》(1984)等,骆一禾写有《河的旷观》《河的传说》(1983—1984)、《滔滔北中国》(1984)、《大河》(1987)等。美国诗学学者米家路认为,通过河流的持续性与流动性,对民族身份的想象在他们对河道的神话、传说、历史和民俗的诗性重构中强烈地表达出来。骆一禾、海子、昌耀等不约而同地以河流为主题,以水为魂魄书写神话化的史诗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象所促成的。同期江河写出了杰出的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他在海里闭上眼睛/得到太阳绿色的光环/太阳小得仅仅是一颗麦粒/含满了汁液/中间的缝里有一条河流着/他还记得/那是黄河。”从朦胧诗的背景里夺路而出,完成了一次现代神话史诗(轻型史诗)的先锋试验,也完成了自身的“心灵图像”建构。台湾诗学学者陈大为认为,其对第三代诗人的反崇高、反英雄、平民化的先锋美学实验,有很大的示范作用。我深以为然,甚至认为应该作为一个常识写入当代诗歌史。如果看到江河那时的短诗《接触》《室内》《话语》《母亲和我》《交谈》等的诗型以及语感和语调,再看到后来的那些为自己打上“口语诗”标签的,便会怀疑其自我命名的诚实性?
前述黄斌解读骆一禾的《大河》时说结尾处理不够客观,我有不太一致的看法:结尾“……浓烈的薄荷一闪而过/划开肉体/积雪在大路上一下子就黑了/我们仰首喝水/饮着大河的光泽”在我读来感觉非常成功,颜色在快速地挥洒,到了“仰首”的动作感,突然宏大地虚化。前面几句可以说是娴熟的技术操作,最后两句才凸显诗人的深厚功力,有如神助!“仰首”(而不是低头)喝水的画面感、仪式感和超现实场景,那是为了体现崇高精神气质所决定!海子在《河流》原序中说道:“诗不是诗人的陈述,更多的时候诗是实体在倾诉……诗的超现实平面上的暗示力和穿透力能够传递和表达这种状态。”1990年代以来的所谓“接地气”“说人话”“及物”指的是诗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回到日常生活、个体经验中来,同时语言更平实,更像日常家居用品,自有其还原、返真的道理。但诗歌作为一种非日常会话的语言艺术,也有崇高、恢宏、超越的精神形塑的诉求。虽然彼时代的精神气象或已不再,但当年那些投身诗歌事业,寻求传统史诗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转生契机的努力,还是应该理解和敬佩的吧,他们在诗艺上除了不足,还有启示性的造诣。否则我们的书写就渐渐只会面对一个动作:低头喝水玩手机,从冷风景环绕的电梯上下来。
夜鱼:嗯,很受启发,我晕头胀脑地探究牛波诗歌的意思,其实没有必要,他也是一种语言探索,涵盖着自己的美学诉求,事实上我感受到了他诗歌里零碎的富有刺激性的画面,这就够了,实在没必要纠结懂与不懂。
盛艳:同意刘洁岷“心灵图腾”的说法。昌耀《河床》的诗是图腾式的,对于词语的选择雄浑,有力,诗歌的推进充满了力量,揉合了历史感和时空感,这通常是用第一人称的顿呼式创作表现出来的,和河流的磅礴相得益彰。海子的诗是雌雄同体的,隐形地讲述了河流的诞生,成长,生殖,挣扎,到最后成了澎湃的有回响的巨大的水域。海子在河流诗歌的把握上从细微处入手,而又能恰当的雕刻出河流的力道。他没有像昌耀那样横空出世的雄浑,他有着刚柔并济的力量。
牛波擅长塑造动态画面,通过文字调节画面的光亮感,他的意象有时是视觉整合下产物。海子诗中的透明是文字带来的,牛波却仿佛是把印象中的画面刻描出来,他们的写作模式是不同的。河流的语义丰富在牛波的诗歌中有多重能指性。骆一禾的《大河》有力,没有过多炫技,结尾的通感使诗歌明亮、干脆。在于坚的河流中更多的看到了哲学意蕴,这也许是中西交融的美好结果。
黄斌:讨论诗歌,我总是乐于参与,并有学习和沟通的意愿,这是因为时时会享受到不能预期的快乐。这次讨论诗歌的二级概念——河流诗,有时波澜不惊,有时喧哗奔腾,也有一种动静偕行的感受。虽说我仍然认为河流诗写直至当下显得不够亮眼,但很有认真审视的必要。诗歌技艺不是工艺美术,技道共生,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感谢三位诗人的启发和砥砺,期待有更多机会参与讨论。
刘洁岷:海子除了大型构地创作诸多河流长诗外,还写了诸如《妻子和鱼》《船尾之梦》《河伯》《水抱屈原》《鱼篓》这些短诗佳作。我留意到海子在《船尾之梦》中对船的形容“……而婴儿睡在母亲怀里/睡在一只大鞋里/我的鞋子更大/我睡在船尾/月亮升了”。此诗开头是“上游祖先吹灯后死去”,这种结构使得诗歌灌注了历史意识,有寻根与寻求精神皈依的意味。无独有偶,牛波在其组诗《河》中有一首《不觉如履》:“船是一只鞋。远处/看不见的地方,还有一只/你会看见它的——//这是巨人的脚步行于水上/横跨山峦或者平原……”牛波写的是冥冥中不可抗拒的巨大的力量——“一个伟大的梦游者/一个不见行迹的人”。出色地写出了人类的渺小懵懂无知和巨人先知般的伟力。两首诗比较阅读,其共生和差异更显得各有其妙。
在昌耀、海子、骆一禾宏大的史诗叙述,在强调精神体的象征内涵以外,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两位特异的朦胧诗代表诗人转型、降下调门的创作,一个是梁小斌,以长诗《断裂》(1985—1986)为标志告别了宏阔叙述,也告别了“优雅”,揭示了生活之恶;再就是江河,在新型史诗探索和口语、平易化书写上均有建树。于今看来,诗歌作为一种书写生命的语言艺术,单篇作品及物不及物,模拟的口语化程度多大比例,都可自由,无需画地为牢,一切以题材、主题需求向度来创作。
朦胧诗、实验诗退隐后,第三代诗人渐渐形成了不断分化的潮流。作为他们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于坚除了以模拟日常生活的中性、客观的语言关注个体命运的书写外——《罗家生》《作品51号》《尚义街6号》——于坚还有着另一套笔墨,即以他故乡云南的人文地理为背景的高原诗写作,其中河流书写有《河流》《横渡怒江》等,这些作品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河流山川,表达了对大自然的赞美与敬畏,用不凡的语感和语调构筑了一种充沛的语型,同时,获取了一种俯瞰世界自然之子的视角。他的《那人站在河岸》(1985)比较另类:“……他还不敢对着他的姑娘说/你向一堆泡沫/臭烘烘的泡沫/臭烘烘的河流/像从前一样流向远方/臭烘烘的河岸/要像往昔一样长满爱情。”将爱情与河流污染诅咒般地进行了书写,殊不知,未来数十年间,关于河流的书写大都难以脱离污染的主题。
另外,当代河流书写中,像陈先发的《鱼篓令》,叶球《……的鱼》,黄斌的《鳇鱼或中华鲟咏》,杨键的《跃进桥》,雷平阳《昭鲁大河记》、余笑忠的《为蕲河作》等,都适合比照阅读欣赏的篇什。当题材、主题、技艺浑融为一体的时刻,诗歌风格亦如水赋形般地在激活着我们生命内在的灵动,而那些古老的流经我们诗心的绵绵波涛将再也不会枯竭。
夜鱼: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发言,在你们的支持下,此次讨论愉快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