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轻逸
轻是可以驾驭重的。如同灵魂可以驾驭肉身,思维可以驾驭行为。当面对现实主义题材和历史题材之时,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和处理它们,是我们在动笔之前就应该明确的工作。我们知道,所有的历史都是曾经沉重的现实,所有曾经的现实都终将成为凝重的历史,抑或时光深处的一块斑影。如何驾驭这些外部世界(内容),卡尔维诺提倡尤其需要以轻逸的形式来减轻它的重量,以免陷入某种情绪的泛滥。窃以为,此即沉重的事物轻逸地表现这一“轻逸”特质的内涵之一。人生而孤独,也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如同每一位创作者,在面对空白文档时那种对未知的无助,对即将深陷无物之阵旋涡中那种既满怀期待,又心存恐惧的“临敌”状态。在第一讲《轻逸》这个文学特质中,卡尔维诺写到: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是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示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昆德拉认为,形形色色的限制就是生活中的重负;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中的种种限制,像一张网眼细小的大网越来越紧地束缚着人类生活。他的这部小说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
小说被故事限制,爱情被婚姻限制,婚姻被家庭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成为王小波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外部的重负往往具象而容易感知,最难把握和驾驭的却是来自我们自身的,集体无意识的压抑和威迫。它无处不在,却又无从捉摸。于小说而言,我主张一种创作者以临终之眸回望的情态和视角进行叙事,以临终之言对生命中任何惊涛骇浪的往事予以轻描淡写。也许,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只有在临终之时,才能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以置身事外的理性和抽象,来概括或叙说生命中感性的高涨或低徊、哀伤或欣悦,才能不受天地万物的约束,插上轻逸的翅膀,御风而行。
当想象插上翅膀,就能够和沉重的现实拉开距离。如同卡尔维诺在这一讲的结尾,借用卡夫卡极短篇故事《小桶骑士》所喻示的那样,在寒冷的冬天,主人公提着小桶出来找煤生炉子,却被煤店的老板娘驱逐而不得,最后骑着小桶飞走了。卡尔维诺写到:这个空桶是贫苦、愿望与追求的象征,它使你离开了互助与自私的地面,把你提升到你那谦卑的请求再也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程度。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与之形成悖论的是,如果愿望得到满足,小桶里装满煤块,我们的骑士还能飞翔起来吗?如同卡尔维诺在1985年将他认为21世纪文学应该保存的价值锁定在轻逸、速度、精确、形象鲜明以及繁复这五大特质,隔着时空飞到我们的案头。
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沉重的题材,比如拆迁、矿难、城乡变迁、农民工进城、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等。这些内容在小说中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才不会流俗于同质化是每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窃以为,卡尔维诺抛给我们的“轻逸”是一个不错的手段,给我们的小说技巧打开了一扇阳光可以投射进来的窗口。我的意思是,在达意的基础上,赋予题材以审美意义。就算作家置身于生活重负的旋涡,在表现时,也不必歇斯底里地呈现。文本可以具象,可以有画面感,但是驾驭具象的,恰恰是抽象。
前面我说过集体无意识对人类生活形成的重负丝毫不亚于外部世界的威迫,这是源于我个人的一个文学观点,即文学表现的不是个性,而是共性。只有那些深刻地表现了“人人身上有,个个笔下无”的共通性的作品,才能够创造文学的未来。
对集体无意识的把握和超越将作家自我他者化,使他闪光的思想碎片像颗粒一样轻盈地悬浮在文本中。只有那些“既是文本希望得到的合作方,又是文本在试图创造的理想状态的读者(艾柯《悠游小说林》)”才能给精准地发现颗粒散布的位置,并予以指认、提炼和内化为自身的知识库存。丰盈其知识储备量。
除了沉重的事物轻逸地表现这一内涵以外,我以为卡尔维诺这一讲的另外指向就是语言的轻逸。
“减轻词语的重量。从而使意义附着在没有重量的词语上时,变得像词语那样轻微。”
“世世代代的文学中可以说都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要把语言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像云彩一样飘浮于各种东西之上,或者说像细微的尘埃,像磁场中向外辐射的磁力线;另一种倾向则要赋予语言以重量和厚度,使之与各种事物、物体或感觉一样具体。”
毋庸讳言,轻逸的语言比有重量的语言更富有诗意和美感,也更容易轻舞飞扬。我对小说虚构的理解是“从虚无中构建世界”,因此,我并不赞同原型说、自传体等等,虚本身就有轻逸的形象在我们的意念里闪动。而从小说中刻意寻找作者及其生活影子的蛛丝马迹,早已经成为大多数读者的集体无意识。有鉴于此,我在短篇小说中经常使用第二人称来叙事,或在以第一人称写作时,那个“我”经常是女性,更有甚者,在《西湖》2017年第4期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句子对作者和读者的抵抗》中,“我”干脆就是一个句子,而小说主人公“你”则是这篇小说可能存在的一个读者。这也是另外一种“寻求轻松,是对读者阅读惯性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的表现形式。
我们知道,语言不是工具,语言就是实质。轻逸的语言像鸟儿一样能够自由飞翔,却也五脏俱全。语言的意义虽然轻微、抽象,但它是“磁场中向外辐射的磁力线”,是文本能指的磁极。
二、速度
还说磁力线。抛却小说直接以物品名称来命名,以确立其象征意义或思想价值不谈,一般而言,物品一旦在叙事中出现,它对小说就形成了某种牵引作用。它不需要作者花费笔墨特意介绍或渲染,只需要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从容而不露痕迹地带入即可。这件物品“变成了磁场的一个极或某个看不见的关系网中的一个眼”。物品对小说的走向或人物命运具有改变或推动作用,那么两者之间或隐或现的磁力线针对文本来说就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行文中无意间带入了一把生锈的剪刀,它必定在某个情节推进的时刻,成为伤害人物的凶器,才使得这件物品在文本中产生了特殊的力量。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物品出现在小说中,作用不是那么明显,而是通过或隐或现的象征来凸显其意义。“它把一切都留给人们去想象,而故事情节的迅速转换使人觉得故事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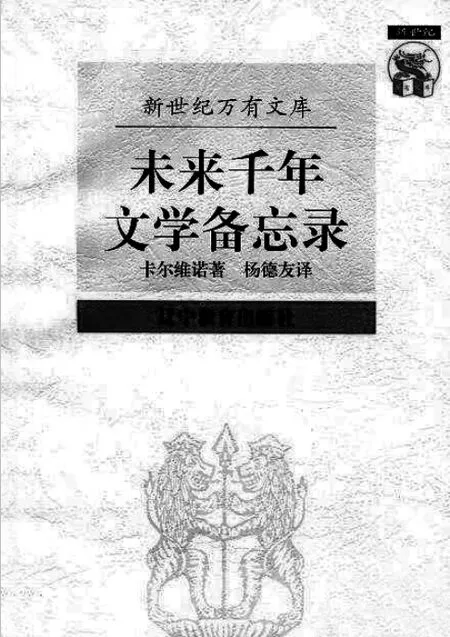
《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我们知道,故事时间不能与现实时间等量齐观,它得符合文本表达的需要(包括语言)。我再重复一遍,作品首要的原则是达意,其次才是审美。数十年的光阴一句话可以概括,而一个重复的动作耗费万余字进行事无巨细地刻画也未尝不可。“民间口头传说的技巧是符合实用原则的:对不需要的情节避而不谈,对有用的东西则百般重复。”我想,严肃文学同样如此,而高明的重复一定是递进式或渐变性的重复,它在强化读者意念或视角形象之时,必定在故事的走向上让自身的量变转化成故事或意义的质变,而只有细读文本的理想读者才能够领略其中的美妙。“民间文学总是忽视时间的延续,倾向于迅速实现人物的愿望或使人物重新获得失去的幸福”,而严肃文学则在作品内部尽力迁延。因此,速度本身在小说文本内部就身不由己,它无时无刻不受到文本意义或作品思想倾向的制约。
有节奏感或韵律感的重复可以延缓结尾或高潮的到来,离题同样可以。“离题或插叙,是推迟写结尾的一种策略,是在作品内部拖延时间,不停地进行躲避……”这些插叙并非多余,而是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或者促进文本的丰满度,或者拓宽文本能指的向度,丰富文本的意义。
卡尔维诺想要的,是对时空的“高度的浓缩”,他对博尔赫斯由衷赞叹道:“他能够非常流畅地实现向无限的时空过渡,能够清晰、严谨、流畅地划分阶段,能够做到叙述简明扼要且用词准确具体。”面对各类文学体裁,有一种共性需要创作者直接面对,那就是如何处理文本中的时空问题,甚而言之,如何处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维度问题。
除了文本内部的速度以外,卡尔维诺在本讲最后,还借助庄子以十年时间的“厚积”,而以瞬间的“薄发”画好一只“完美无缺、前所未见的螃蟹”的多重指涉和隐喻来结束本次讲座。
毫无疑问,卡尔维诺对作者在创作时应考虑各种时间的要求,正是他对自我的要求,也是对所有坚持探索性的文学创作者的经验式告诫。以庄子画螃蟹的典故则双关了“创作者的时间与速度”和“文本成熟度的时间与速度”,同时更加隐喻了本讲的主旨——文本(小说)内部中故事或情节推进与价值、达意呈现之间的时间与速度。
三、精确
这一讲的概念卡尔维诺阐释得非常“精确”。一是作品的构思非常明确;二是视觉形象清晰,令人难忘;三是在造词和表现思想与想象力的微妙时,尽可能使用确切的语言。让我们先说作品的构思。卢克莱修认为世界由性质、特征和形式构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之套用到作品(小说)头上,窃以为是可以的。我先说说特征和形式,或者换言之说说小说的结构和表现手法。
一部小说的结构就是一栋建筑的主体框架和外立面,也是一个具有“精确的晶面和折射光线能力的晶体”。卡尔维诺在阅读科学著作时,看到了生物形成过程的模式:“一边是晶体(象征表面结构稳定而规则,是一种‘自我编制系统’),一边是火焰(虽然它的内部在不停地激荡,但是外部形式不变,是‘从噪音到有序’的渐变)。”卡尔维诺将晶体的象征意义同小说结构结合起来,是非常“精确”而有说服力的。
我想表达的是,就一部小说而言,作者在落笔的那一刻,至少在结构方面应该是“构思非常明确”的。尤其是篇幅较长的中篇小说。我的做法是,将第一个自然段和最后一个自然段的内容先敲定在文档里。然后让行文从第二个自然段摆渡下去。只有这样,不管内部的“火焰如何不停地激荡”,依然能够切实做到结构层面的“稳定而规则”。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莫言的《檀香刑》,直接以凤头部(表现手法上是四个章节分别以四个不同人物的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猪肚部(表现手法上是九个章节以第三人称叙述)、豹尾部(表现手法上是五个章节分别以五个不同人物的第一人称进行叙述)来建构全书。还有高行健的《灵山》以“我、你、她和他”四个人称代词进行交替叙述,将独特结构和新颖表现手法合二为一,使之具备了双重属性,以炉火纯青的笔力构建了一部内蕴丰盈、指涉多维的长篇小说。既然说到了这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就让我们顺便过渡到小说的“性质”。
我们来看第3章结尾部分的内容:
码头上方,堤岸上,还真有个飞檐跳角的凉亭。凉亭外摆着一副副差不多是空的箩筐,亭里坐着歇凉的大都是对岸赶集卖完东西的农民。他们大声聒噪,粗粗听去,颇像宋人话本中的语言。这凉亭新油漆过。糖下重彩绘的龙凤图案,正面两根柱子上一副对联:
歇坐须知勿论他人短处
起步登程尽赏龙溪秀水
你再转到背面,看那两根柱子,竟然写道:
别行莫忘耳闻萍水良言
回眸远瞩胜览凤里灵山
你立刻有了兴致。渡船大概是过来了,歇凉的纷纷挑起担子,只有一位老人还坐在凉亭里。
接下来“你”就问老人“灵山怎么走”,老人家指着河对面的两条路说:“走这一条路,不是走那一条路”。针对全书81章来说,从这一刻开始,“你”才真正进入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即“寻找灵山”这一番精神漫游之旅的70余章内容,其中包含3章对本书从结构、手法、隐喻等方面的解构)。直到小说第76章“他(你的背影,见第72章)孑然一身,游荡了许久,终于迎面遇到一位拉着拐杖穿着长袍的长者”,于是和“你”一样上前请教老者“灵山在哪里”,然后就是一阵抢白式的关于“在河这边还是河那边”的,既富有哲理和浓烈的思辨色彩,同时也具备就事论事现实意义的问答。最后“老者抬起拐杖,不再理会,沿着河岸一步一步远去了。独自留在河这边,乌伊镇的河那边,如今的问题是乌伊镇究竟在河哪边?他实在拿不定主意,只记起了一首数千年来的古谣谚:‘有也回,无也回,莫在江边冷风吹。’”
窃以为,就本书的“性质”而言,就指涉的多维性而言,前半部分的“灵山怎么走”和尾声部分的“灵山在哪里”是一种意义上的递进式照应。这一条路还是那一条路?这边还是那边?彼岸还是此岸?灵山是有还是无?是抽象的个人精神的“灵山”还是具象的乌伊镇附近的灵山?重要吗?不重要!“他(或者说你)”已经从那边来到了这边,或者说从此岸来到了彼岸。你能回去吗?不能!过去了的就是历史,历史无法回去。但是一个人,无论何时,都可以听从自我内心的召唤,回归自我,起心动念,皆可抵达。我们知道,《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师傅菩提老祖所居之地为“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而此处的“灵山”即指人的思想和内心世界。我不知道高行健在取书名时是否受此激荡而得到启示,但是小说中东方道教的虚无、佛教的空性和西方信仰上帝的学说无不杂糅共生。催生出夺目晶体般的光彩,造就出斑斓多姿的、隐喻的、多向思维的指涉性。
现在,让我们从多维的指向上抽离出来,探视卡尔维诺对“精确”定义的第三个要点。我们来看三段文字:
一、时间是日光下移动的阴影,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是细沙长流。
后来人们才听到时间的声音。
——李敬泽《青鸟故事集》之《利玛窦之钟》
二、阳光浩浩荡荡地泼洒在紫禁城金色的屋顶、血色的宫墙和空旷的广场,冬日的阳光坚脆,能听见阳光落下时发出瓷器开片般的细响。
——李敬泽《青鸟故事集》之《利玛窦之钟》
三、千古旱天那一年,岁月被烤成灰烬,用手一捻,日子便火炭一样粘在手上烧心。一串串的太阳,不见尽止地悬在头顶。
——阎连科中篇小说《年月日》
上述三段文字有三个共同的特性:一是皆出现在作品的开头部分;二是都用了通感手法;三是都写到了日常事物阳光。窃以为这三段诗意盎然的句子强有力地成为“精确”内涵的第三个要点的精准注脚。我们知道,优秀作家的功力主要体现在对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事物或生活,拥有独具只眼的发现和精妙的呈现,并赋予其意义上。他们是如何“在表现思想与想象力的微妙时,尽可能地使用了确切的语言”的呢?
李敬泽关于时间的想象和阳光的细描是通感,更是比兴。在轻逸表现与精确呈现共振的基础上,是李敬泽通过捕捉想象力的细微,将和表现思想有关的,“看到”的时间(如隐喻的沙漏)与后文“听到”的时间(自鸣钟)杂糅共生。而阎连科此处的语言既能够给读者造成视觉成像的逼真感,又能够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外衣下,给读者以切实的触感(日子便火炭一样粘在手上烧心),这种想象力的精妙幽深,是同《年月日》的作品思想紧密连接的。堪称大师手笔。
然而,在表现思想与想象力的微妙的更加高超的、无以伦比的文本,还是出自卡尔维诺之手的长篇小说《看不见的城市》。大师无法谦虚,也不必谦虚或故作谦虚。我们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城市这个形象比晶体与火焰的形象更为复杂,我可以用它来表现几何图形的合理性与人类生活的混乱状态之间的矛盾。我认为我的作品中含义最丰富的仍然是《看不见的城市》,因为我在这本书中把我的各种考虑、各种经历与各种假设都集中到同一个形象上。这个形象像晶体那样有许多面,每段文章都能占有一个面,各个面互相连接又不发生因果关系或主从关系。它又像一张网,在网上你可以规划许多路线,得出许多结果完全不同的答案。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每个概念和每个标准都有两重性,精确也有两重性。这本小说中有一段写忽必烈大汗,表现了智力向有理化、几何化与代数化转变。忽必烈把他那个帝国看成一盘棋,把马可·波罗给他详细描述的那些城市看成是黑白相间的棋盘上的车、马、相、士、将、兵。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占领的所有地方都变成了这个棋盘上那些棋子下面的小方格,而这些小方格又是虚无的象征……
卡尔维诺的语言在这一段中经过了高度抽象后达到了高度精确,证明了外部世界的实质是虚无。
四、形象鲜明
在上一讲的札记中,我引用了阎连科“一串串的太阳,不见尽止地悬在头顶”这样一个视觉成像的句子。与此造成互文性的,是在本讲的开端,卡尔维诺首先以但丁《神曲·炼狱篇》中“然后落入我的崇高想象中……”这句话作为引子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想象是可以落进东西的地点。阎连科此处的“崇高想象”就是卡尔维诺认为的“亦即想象力中最高超的部分,不同于幻想。”那么,形象是从哪里“落入”幻想中的呢?我非常激赏卡尔维诺在这一讲中的观点——近代某些作家声明自己与地上的信息源连在一起,即与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连在一起,认为那些形象是已消逝的时间在感觉中的再现,生命在某个时间与地点的浓缩或显现。这个观点是非常高度抽象又高度精确的。在第一讲“轻逸”的札记中,我借用拙作《一个句子对作者和读者的抵抗》说明“轻松对重负的反作用力”,现在我同样借用小说开头和结尾的逗号来阐释“形象落入幻想”这一现象:由于小说的主人公早已在我构思中假定为是这篇小说可能的读者“你”,那么,“你”在阅读这篇小说之前或阅读完之后,都在干什么呢?十有八九是在看这期杂志这篇小说前面或后面的小说,或者这期杂志其他的文章,那么这个逗号在我的幻想中,既是表现“人物行为的连续性”,但同时又隐含着“没有开始的开始,没有结束的结束”这样一种既是小说开始或没有开始的开始或结束或没有结束的结束,也是小说内部人物行为、心理的开始或没有开始的开始或结束或没有结束的结束的一种“状态”。
对于一个小说作者来说,如何才能做到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事物“视觉形象清晰,令人难忘”呢?卡尔维诺要求作者,在观察人物时“把自己当成一个穷人,一个卑微的奴隶,毕恭毕敬地去观看他们,观察他们,并为他们的千种需求服务,就好像自己是亲临其境”。在观察人物这个单项上,此处的观点和我不谋而合,我想要的作者视角是“眼睛低到尘埃里,贴地而行”地观察你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察觉常人所不经意忽略的东西。
五、繁复
不管语言、内容还是结构,简洁不见得比繁复好。繁复当然不是冗长,也不是臃肿、庞杂或琐碎。只是在我们眼下这个消费社会,在每时每刻海量信息迅速拥塞进我们的眼里、脑海里的时代转型期,阅读就像海面上漂浮的泡沫,稍纵即逝。浮躁不安的我们对一部作品多数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式的阅读,这就导致了我们本能地抗拒或回避那些挑战我们阅读习惯和思维惯性的作品。而繁复,就是这些作品中一个鲜明的特征。先说语言。我在2010年阅读中国台湾作家骆以军繁体版的《西夏旅馆》时,首先受到思维冲击的就是他那繁复又精确的语言。我的文友李华在评论拙作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即《边缘人》)时这样写到:
骆以军是另一个极端,最大限度地调动记忆库存,他那丰腴的、充满想象的、细枝末节的、分叉繁殖的语言,以最丰富的内涵来表现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他所告诉我们的,不只是那个结局,更是语言“走神”或曰“离题”时的那份想象所带给我们的震撼感。这种根深叶茂的语言我谓之折叠式语言。何也?读起来有褶皱感,有纵深感。每一处褶皱都能迁出层出不穷的意象,让人猝不及防。
上述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赞赏繁复并不排斥简洁,就像赞美丰满并不排斥瘦削。繁复或简洁,都是针对句子传递出来的意义而言,而不是针对句子的长短而言,很多时候,句子本身的意义不取决于这一句或那一句,它和段落有隐秘的关联,和章节有隐秘的关联,甚至和整部作品的走向、内容、思想倾向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长句子或者繁复句子的形状、价值、意义何在呢?我来引用一位名叫不有的作家《彩练当空舞——对长句的幻想》中的一个段落:
我不能完全解释清一直以来我对长句的那种迷恋,它可能使得我想要表达的获得了一种与我正在表达的相距渐远、迂回的效果,使得我的意图不致过早暴露,而由句子不断衍生出的呈发散状的各种手势展现了一种富于耐心的美感,像一盆值得付出心血经营的藤蔓植物,尽可能保持对根的远离,但又不完全脱离与地面的指向性联系,通过在各个方向上可能的尝试和努力,句子没有停止加长,反而获取了新的动力,最终复杂的扭结和盘曲将展示一种强劲粗壮和精致无尽的美。只有美,可以消解那些看似急功近利的意义。
再说内容。卡尔维诺在本讲的开篇即引用了意大利作家卡洛·埃米利奥·加达的小说《梅鲁拉纳街上一场可怕的混乱》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加达的观点“事物是过去的与将来的、现实的与可能的、无穷无尽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的网。”是的,网在这一讲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但又不局限于网状叙述。加达作品的特征是说明任何一个人认知过程都是由恰当的精确性与肆意的曲解两部分组成的。
卡尔维诺总结说,内容多样(繁复)的小说,即以众多的主体、众多的声音、众多的目光代替惟一能思索的“我”(如莫言《檀香刑》的凤头部和豹尾部)。窃以为,此处的“我”既涵盖了小说中的“我”与叙述者,也涵盖了叙述视角以及作者。
最后说结构。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各种事物连接成的网是由事物本身依次在时空中占据的点构成的。窃以为,这就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所呈现出来的网状结构。在卡尔维诺眼里,能够完美体现幻想与语言的精确性这一美学理想,并写出了符合结晶体的几何结构与演绎推理的抽象性这类作品的人,他报出了广为我们熟知的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这篇小说中提出的设想是:一、准确时间的想法,即主观的绝对的现在(任何事情对当事人来说都发生在现在);二、由意愿确定时间的想法,按照这种想法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消除不了的;三、多样化的、分出许多枝杈的时间的观点。按照这一想法,任何现在都分成两个未来,从而形成“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互相分离、互相交叉又互相平行的不断扩大的时间网。”这种繁复,将时间无限扩展。
卡尔维诺的长篇小说结构是累积式的、模数式的、组合式的,且篇幅大都不长,这也是他为自己设定的“长文短写”规则的体现。这些小故事的结构使卡尔维诺能够把思维与表达上的浓缩与客观存在的无限可能性联系起来。
在这一讲的结尾,卡尔维诺希望“有部作品能在作者以外产生,让作者能够超出自我的局限,不是为了进入其他人的自我,而是为了让不会讲话的东西讲话,例如栖在屋檐下的鸟儿,春天的树木或秋天的树木,石头,水泥,塑料……”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我在前面提到的拙作《一个句子对作者和读者的抵抗》中的“我”就是一个句子,而小说主人公“你”则是这篇小说可能存在的一个读者,至于小说中的“徐清松”就有三重属性,既可以当做小说人物,又可以当做作者本人,更可以当做小说中的那个“我”——即句子。我之所以敢以“先锋小说”来命名这部九千字的小说,主要是我认为有两点我起码做到了前无古人:一是小说以逗号开始以逗号结束;二是小说中的“我”虽然是一个句子,但它又是每一个句子,因此它本身隐含了第三人称的叙述功能,即实现了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合二为一的现象。“我”具备了无限延长的魔力,也就是说小说本身可以九万字、九十万字地无限写下去,而又能够自圆其说。这种累积式的、组合式的叙事既是内容的繁复,也是结构的繁复,“能够把思维与表达上的浓缩与客观存在的无限可能性联系起来”。在此,请允许我衷心感佩《西湖》编辑同仁的巨大包容性,居然让这个篇幅短小的小说在我有生之年变成铅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