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人的尊严
——读周芳的《重症监护室》
吴 艳
一、疾病与文学象征
文学与疾病的关系由来已久,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是人,连同人的生病过程都难得漏掉,只是到了20世纪,文学的“疾病”书写才被赋予一些隐喻意味。探讨疾病所遮蔽的意义,其代表性成果有法国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和美国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福科《疯癫与文明》借着对精神病人“癫狂”症状的考古,揭示癫狂与文明的关系。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癫狂仍然作为一种审美和世俗事实的存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说明癫狂具有表现和启示真实的功能。十七世纪,癫狂才开始被社会排斥,成为一种可笑、虚妄的病态。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用精神病院处置癫狂者,精神病院就像监狱一样,成为一种社会控制和惩戒的手段。
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而且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她认为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身份,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属于疾病王国。在《疾病的隐喻》里,苏珊·桑塔格从文学作品和现实背景分析疾病的文化寓意及其深刻影响,探讨“仅仅是身体的病”为何能够变成道德批判,又为何能够转换成一种社会的压迫和歧视。
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鲁迅小说与疾病关系密切,但鲁迅的小说所关注的不是生理疾病,而是作为一种隐喻和形象化的疾病。以狂人、疯子象征旧的封建专制文化的叛逆者,以肺结核患者与革命者构成悖论性关系,以身体畸形象征千疮百孔的病态社会,用中医指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鲁迅作品疾病意象的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指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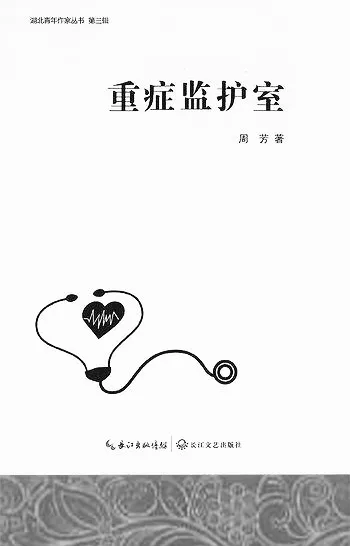
《重症监护室》
前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癌病房》,意在揭示生长在前苏联社会机体上的“毒瘤”,小说通过充满政论色彩的严峻审视与反思,剖析控诉了斯大林时期肃反运动和个人崇拜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表现了作家对不合理制度的强烈不满!鲜明的政论色彩和强烈的辨析力量是鲁迅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表现疾病的共同特点。
周芳的《重症监护室》同样是写疾病,是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群体,连同这些病患的亲朋好友,帮助病人与死神搏斗的医护人员,读起来沉重而焦虑。因为生死攸关,又是日记体形成的纪实、复调的快速展示,让读者揪心,也常常使读者喘不过气来。《重症监护室》值得我们用心阅读,源于作者纪实体的复调书写、平面化的现场展示,以此所表现的当代中国人依稀留存的“善终”理念。这个念想是一种浓郁弥漫又挥之不去的气氛,夹带着恐惧、紧迫和楸心,在“重症监护室”的平常时空,看不见却又分明感觉得到,它潜藏在眼见耳闻的病人及其家属话语、举止的细微末节,“善终”期盼又何尝不是对人尊严的最后守护呢?
二、日记体的复调书写
周芳以纪实体复调书写、平面化的现场展示,再现“重症监护室”的危机四伏、纷杂紧急与生死搏击。其开篇写到:“十二张病床,一顺摆开。赤身裸体的病人摊开在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每张病床前几台机器在轰轰轰地运转。监护仪上绿色的显示线条起伏不停。刺耳的报警声接连响起。”重症监护室的每一个病人都命悬一线,让人胆战心惊。在这里做义工的周芳,真实记录这12张病床上的患者、他们的家属以及医护人员的日日夜夜。他们相互帮衬,携手并进,与死神拔河,与病魔抗争!其惨烈不是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刚毅坚强,而是弱者病患的垂死弥留,可一旦清醒,他们会用手势或者断断续续的语言表达自己求生的本能。作者不是以小说的虚构形式重构艺术世界,而是用日记体的纪实再现重症监护室的特殊环境和人物。文学虚构的力量是我们熟知的,纪实文学的威力与文学性却也不可小觑。自2015年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以纪实作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世界文坛引发了对纪实文学体制价值的重新认识。1998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曾获得德国莱比锡图书奖,德国人敏锐觉察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意义是“创造了一个将在全世界得到回响的文学门类”,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为“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记者,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都是纪实性的复调书写,与她的同胞前辈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不同,复调小说虚构故事,纪实性复调书写则以真实记录为根本,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众多普通人以形成的“口述历史”,展示了其历史的多元与真实,这些“口述历史”也多半源于她的日记记载。从某种角度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日记加采访,是它们的扩充和剪裁,有些类似于电影的蒙太奇。她的作品中,那个以第一人称口述历史的人物被不断轮换,就某一个讲述者来说,也不断被轮换着讲述历史,不管是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女兵,还是被派往阿富汗的“锌皮娃娃兵”。每个以第一人称口述历史的人,组成众多各自独立而不可融合的声音和意识,作家让每一个声音和意识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平等地各抒己见,以完成对历史的艺术还原。多元和多音调的个体讲述并没有听命于某种威权的设定,细心读者能够从更多视角逼近那些被遮蔽的历史,体味人心的鲜活与复杂。
周芳《重症监护室》是近年来纪实文学的成果之一,不同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口述历史”,周芳努力让日记本身带着复调色彩,以展示她在重症监护室做义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本来日记体在时间上是单向线性发展的,不具备复调特点。如何突破这种单向线性的约束,形成众声喧哗的复调?作者调动了文学手法,选择不同视角、不同人物在同一时空的状态,这里有患者、病患家属、医生,还有作者自己。以作者为主线,不断穿插病患、患属、医生的多级对话,象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不断轮换和剪辑镜头,近距离特写、中距离的展示和长焦距的俯瞰,把我们读者带入重症监护室现场,让读者与病患共同经历那里的生死折磨和心灵伤痛。那位90多岁的老红军,那位叫铁人张的病患,还有那位26岁的女病患,人生还没有完全展开,她没有谈恋爱,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就死了!
绝大多数读者都无力追问具体的治疗、抢救过程,他们的职业多半与医护岗位无关,他们关心的是病人如何面对重症摧残,病患家属如何承受精神和经济的重压;医护人员如何救死扶伤,而常常又回天乏力。周芳《重症监护室》抓住了读者关注焦点,用日记体纪实,展示了这个特殊时空的生生死死。
三、“善终”与人的尊严
“生,需要尊严,死,也需要尊严。”重症监护室里的医生与死神赛跑:看谁最先到达终点!死神要带走病人,医生则竭力拽住病患的手,让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以实现患者求生心愿,以安抚患属的恐惧与揪心。大难不死,是病患、患属和医生的共同目标!但医生不总是能够获得胜利,劫难套着更大的灾祸,现代医学还不能医治好每一种病症,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说法: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说到底,医生的职责只能如此,问题是那些被推进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和他们家属,几乎都是抱着“被治愈”的念想来的,可事与愿违,紧接其后的是万劫不复的煎熬和无时不在的死亡威胁。重症监护室的病患,恢复短暂自主意识后,多半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善终”念想,患属则是在急切与恐怖心态下想象着阴阳两隔的那个世界会如何接受他的亲人,换句话说,患属以现世社会揣度阴朝地府,希望自己的亲人不被阴魂鬼魄所缠绕,希望自己的亲人从阳界到阴府,一路走好!这何尝不是我们中国对人尊严的最后期盼与守护呢?
中国传统生死观认为“善死”“善终”才是理想的高品质的离世,这里的“善死”,指的是正常的、自然的寿终正寝。它排斥因遭遇水、火、刀、兵的死亡,也排斥因病夭折、因病而英年早逝。但在现代社会,即使处在和平的、风调雨顺的年份,老年人正常、自然的寿终正寝也变得困难,因为现代医学发展,客观上使老年人无疾而终变得不太可能,也一般不被世人所承认,人们迫不得已只好在“善终”上多了些追求和讲究。传统的“善终”是指临近死亡的人,能够安卧在熟悉的老屋子里,亲朋好友环侍身边,行将离世的这位老人可以从容不迫地交代后事,再安然瞑目。辞世老人要“入土为安”,以便子孙后代“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现如今,这样的“善终”也变得困难重重,多数人在医院辞世,临终时又多半不省人事,能够有子女陪护已属万幸。“安卧在熟悉的老屋子里”、“从容不迫地交代后事”、“安然瞑目”几乎成为无法企及的美好梦想。但“善死”“善终”的集体无意识还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在那些匪思所夷的细节里,流露着“善死”“善终”观念的痕迹,如《重症监护室》所表现的那样。
被死神掠“走了的人”,身体要是完好无缺的;这个人不能当饿鬼,要是吃了饭才走的;要是没有多少疼痛感的,弥留之际最好是有亲人陪伴身边的……医生要病患家人做出“放弃治疗”决定,无异于是要他们在刀锋上行走!有了这样的潜台词背景,读者就会理解,为什么那位26岁的女病患,已经终止了所有生命迹象,她的家人还要那么仔细地检查她的身体,唯恐有一处不完整或者遭到人为的割损。所有这些都是患属对死的想象以及对离世亲人的善心准备,透露着拳拳怜爱、痴痴孝顺。
重症病房的那个病患,一旦恢复正常意识,则要求自己是有尊严地躺着,尽量少麻烦家人。《重症监护室》里,那位90多岁的老红军,一直念念不忘要穿上一条裤子;那位铁人张,不愿意拖累家人,第一次喝农药被抢救过来,第二次他喝了农药以后再投河,投河时还将自己用绳子系在河边树干上,为的是方便家人的寻找……
中国传统生死观映照了儒、道、佛的身影,但影响到平民百姓生活层面的,多半还是儒家观念。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一般人理解孔子是在规避死亡,活人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或者活着的时候应该怎样做人还没有弄懂,哪有时间去研究死人的事情和该为死人做些什么呢?一般人也不太深究“未知生,焉知死”其中蕴含的基本前提,即死是比生更高深的学问,是超越生的存在。生尚且不知,何以知死呢?由此可以引申其内涵:死不是生的结束,死的意义自然也就蕴含其间,这就为儒家重死的观念作了理论上的铺垫。于是,死才能不朽,生才有价值和意义。儒家以仁、义为终极关怀,或者说最高使命,否定生的绝对价值。孟子曾袒露心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儒家这种生死有命、仁义高于生命的理论,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挥洒得淋漓尽致。儒家重死,死后自然要厚葬,厚葬久丧也是儒家重死的生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症监护室里弥留人世的病患,他们的亲朋好友,决没有闲暇思考这些高深莫测的生死问题,但他们言行心态却流露了民族、传统生死观的集体无意识!不太看重死亡的自然属性而重视其伦理性,将衡量逝者能否安息的标准由传统“善死”“善终”变相为更加生活化的细节想象,如同生者一样。道家的淡泊生死,佛家的“生不足恋,死不足惜”的超越生死,所有这些在民间、在重症监护室里微乎其微,几近于无,也难得看到。
感情与理智、传统与现代生死观之间存在裂痕,也存在悖论,面对生死怎么办?传统的“善死”和“善终”几乎成为遗迹;治疗或者过度治疗也存在悖论……周芳《重症监护室》在日记体的纪实中,让读者感受到悲怜与伤痛。复调的哀叹,恐惧的努力连同命悬一线的折磨,所有这些都震撼了读者的心灵。

吴艳,教授,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江汉大学武汉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中心主任,江汉大学延安文艺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