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于当代文学的时代表达与精神症候
——徐勇文学批评研究述评
■李亚祺
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思辨型知识结构由于“得来全不费工夫”,反而更容易固化。此时,文学批评在理论背景之上能否结合本土自我更生,其实是当代文学批评尤其需要注重的环节。而这种生成,往往需要在对文学性本位认同的同时,具备文化批评的理论视域和包容视角,从而在文本人物形象、作者、读者、批评者等时代主体之上,建构出关于当代中国的精神症候。可以说,青年批评家徐勇在多年的文学批评工作中,囊括从传统作家、70后作家和青春写作者等一系列当代作家作品在内的文学评论,是对宏大叙事解体后的当代文学叙事内在结构、寓言及其可能性独具风采的呈现,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化视野下的时代精神图谱,并具有时代预言色彩。
一
地域空间本是一部作品的内在构成,但往往被当代文学文本无意识忽略或刻意呈现出激进的矛盾,而关于城镇化、地域性的深度思考及其内在的精神思潮则容易被观念化的前提所忽略或统摄,青年批评家徐勇则善于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中寻找时代的症候,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域空间问题以明晰的思路给予梳理,并呈现出相应的文学生态场域。从城市写作的空间问题到城镇化过程中乡土叙事的新命题,再到城市的边缘者与游荡者,以及边缘写作的困境与可能……徐勇在对地域的流动性、走出南方、底层写作的类型和模式、大历史中的社会转型和内心变迁等一系列命题的关照中,以新视角呈现给我们历史进程中的地域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乡土叙事、城市叙事,底层叙事、市场经济题材等写作范式的新格局。
例如,在徐勇看来,八十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写作,很多并非真正的乡土叙事,而是“到城里去”的隐喻体现。尤其当叙事的主体的身份由农民转换成为城市居民时,他们的叙述是否还能够称为乡土叙事?在对这类概念的界定和思辨中,徐勇的重点并非仅仅着眼概念本身,而是推导出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地域性生态面貌,这种面貌既包含有对过去的梳理和总结,同样也是一种时代症候的象征和表述。

《长江丛刊》2013年9月
相应的,徐勇对城市写作和空间问题也有着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空间作为城市问题的焦虑之源和症结所在,有着区别于农村的强烈流动性,尤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随着全球化进程而日趋加剧,制约着城市文学写作的发展流变,并形成城市移民文学。这建立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的考察之上——文化不再作为政治的他者而出现,与此同时,城市成为欲望的代名词。这是中国文学在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伴随全球化出现的同质性空间。从贾平凹、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等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文学创作,到韩东、朱文创作的演变,文本的焦虑是城市空间内在焦虑的外化。
与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倾向于从城市的风俗性表征探讨城市文学写作不同的是,在徐勇看来,城市空间所指涉的身份问题才更为重要。就城市文学而言,当下的城市空间并非仅仅是地方性的表现,而更多是以城市为背景的空间所具有的现代性表征。例如,传统工业题材的小说一向不被视为城市文学,而在徐勇看来工业题材小说才是真正意义的城市文学写作,因为它所反映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是典型的城市现代性产物。许多带有文化符号的城市表象之下的地域性小说之所以能够建构出城市空间,并不仅仅在于其符号的模糊和泛化,而在于城市本身体现为塑造主人公性格和命运变迁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城市文学也伴随着城市主体自身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而认同危机所构成的焦虑不仅作为作品中主人公文化性格的构成因素,同时会化成作家创作的直接内驱力,构成作家自身创作轨迹的变化。
由此,徐勇文学评论中对地域的横向考察之下,是对作家个体创作历程纵向的考量,这不仅需要开阔的视野,同时需要敏锐把握作者自我的突破和局限。如在探讨东西的写作时,徐勇指出,作为南方写作和走出南方的文化承载者,其文本中的人性话语所显示的并非仅仅走向西方,而是要挖掘本族群文化内部的、秩序和理性之外的异质冲击;是与西方在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性的内涵丰富性的共鸣,而非地域性内部的自我循环。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便是地域性写作,也需要能够在身处的世界中寻找到在民俗民风和奇观之外的内在写作即人性写作方式。因此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理解,在徐勇看来,并非是以特性和民俗风情为吸引点的卖弄式写作,而是植根于全球化内部的人心人性的矛盾与演变,这样的地域是不确定的,但却在其内部获得了自我镜像中的圆满。
可以说,在徐勇关于地域的空间性和流动性的一系列文学评论中,当代文学中的城市或乡土,南方或北方,精英或底层……都一一浮现。他不仅从传统能指的定义入手,抛开本质论的批评模式,在地域写作的问题上看到地域之于地理界限规定之外的人,还在分析文本被隐藏的时代侧影时进一步深入呈现广阔的时代背景,并对其作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中对人心人性的内在形塑力量而进行深度的关照。而这样一种文学内在心理结构意识,是在文化批评视野之下对文学性及现代性演变的内在考量,并且有效地沟通了作者与文本之间的时代共性。由此,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寻找到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之间的切入点和契合点,人文关怀与全球化视野的并行不悖,构成徐勇文学批评的独到风采。而徐勇对文学文本的关照建立在大历史的视野之下,又不拘泥于元话语决定论的文学批评观念,使其批评文本作为对文学生态场域的描述与刻画,具有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批评视野。
二
探寻“表象之下的经验”,探寻“以象征的方式介入现实”,“探寻经验与写作的关系”,探寻“心灵的备忘录与启示”,探寻“先锋近处的温柔”,以及“先锋的创痛与疗救”等等——徐勇对不同作家作品的评论与分析,突破传统文学批评中固有概念形成的窠臼,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不同文本,使作者的文学性诉求,知识分子的精神辩证与困惑,人们在时代中的进退失据等一系列症候,在自身的文学批评系统中得到精微而极具说服力的呈现。如在对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等一系列创作文本的分析中,徐勇抛开一般文学批评对其语言困境的描述,反映出底层所具备的一种执拗、奋力挣脱和终难挣脱的人生悖论。而在分析《我不是潘金莲》时更进一步地指出李雪莲的痛苦在于符号的错位,而这样的错位在于主人公现实主义的观念预设——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不管世界的表象如何纷繁复杂,这背后总有真实的内核和深度存在。而一旦只看到表象,以至于表象掩盖并最终取消内核深度的时候,表象和内核的区分也就消失了。

《长江丛刊》2013年11月
在这里,徐勇以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的超现实主义作为理论背景,分析现实主义本源意义的被遗忘。作为一个建立在传统农村劳动者身份之上现实主义观念偏执的承载者,李雪莲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幻想中,一旦遭遇现实便不免头破血流。徐勇鲜明地指出李雪莲的痛苦承载着太多的历史负重,是一种符号证明的痛苦,也是历史加诸于不识时务者个人身上的不能承受之重,从而实现了对刘震云写作的整体性评论,即轻与重的辩证与悖论。历史的轻重偶然,在刘震云笔下是隐藏在故事中的内线,而在徐勇的文学批评中则被细致精微地梳理出深厚的哲学意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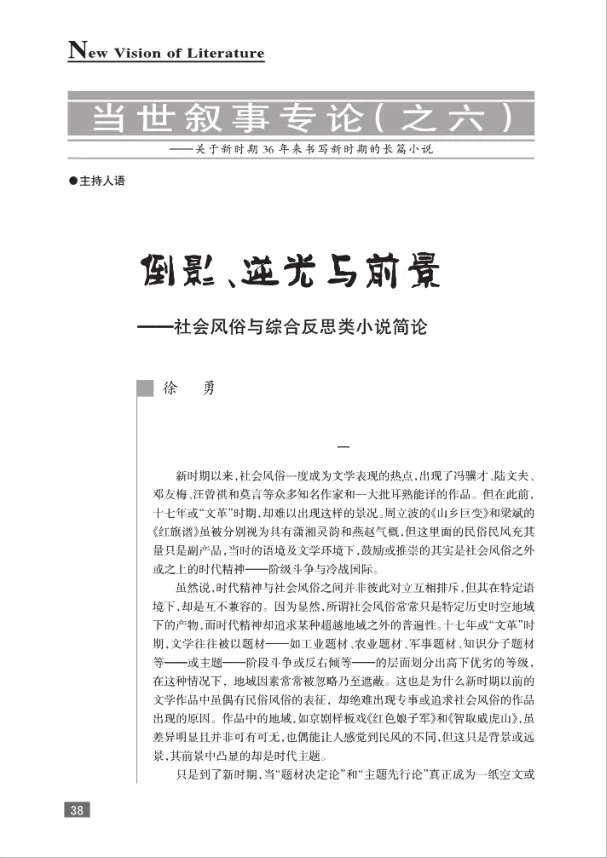
《长江丛刊》2014年1月
对韩东的《欢乐而隐秘》,徐勇则指出了欲望所指涉的生活层面某种程度是文化冲突的表征,欲望使得生活某种程度上成为经历了理想溃散后资本主义式的日常生活常态,这是没有宗教节制和约束下的日常,是一种本能的形式张扬,并且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合理性。徐勇敏锐地意识到了文本内部蕴含了对这一合理性的追问、超度及自我救赎的探寻。在这样的救赎中,徐勇看到拒绝宏大叙事的结果往往是欲望演变成表演和被展示的对象——呈现了爱与欲望的匮乏本质,而如何填补却并没有给予答案,因此也无力度、广度和深度可言。同样,在这样的论述中,徐勇完成了对欲望本质的哲理性思辨及其在小说文本中呈现的可能性。而这样的思辨,也正是在对全球化与现代社会真实生活层面的考量基础之上,对文学文本中人性可能抵达深度的考察。
另外,关于叶弥的创作《风流图卷》,徐勇捕捉到其颓废的风格、个人主义话语,不同于当代文学宏大叙事中常常与怀旧相伴的颓废,也不同于因为现实批判意识和反讽精神过于浓烈而产生的颓废,又或是为刻意凸显与时代的分裂而制造的颓废。通过对这类创作的颓废的界定,徐勇认为这是一种既需要与时代保持距离又需要介入其中的中间姿态,其结果是构成了作品的独特的味道和腔调。这种关于颓废的审美意识是叶弥本人的创作特质,更是徐勇在对他人的创作批评中梳理和总结出的这个时代对文学性的诉求。
在对刘慈欣的作品的考察中,徐勇看到《三体》通过将一系列命题搁置于人类面临毁灭的极端境遇中去重新考量,并提出道德命题的局限,而在宇宙的角度和哲学的高度上赋予这些命题重生的价值。这是时代之中的人对人类困惑的梳理。徐勇在对文本的独到观察中鲜明地指出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精神恐慌往往在于将理性和感性本质化对立起来。这是刘慈欣本人所反对的,同样也是徐勇在看到解构主义所带来的二元对立时,发现文学批评更重要的是重新审视人类的普遍命题,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思辨性。
另外,无论是在对莫言的文本考察中,分析其在历史叙事之外的现实性,敏锐地发现其作品结构中的他者化表征,从而发掘出作品结构的深层意义;又或是在对张玮,阎连科、叶兆言,刘醒龙,王朔,莫言、贾平凹的创作中的时代的症候里把握文本背面所折射出的人心与时代的远近疏离,亦或是徐则臣笔下一代人的“精神自救”……徐勇的文学批评既有对作者自身创作状况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梳理,也包含有他对当下文坛在折射现实生活层面有力道的把握与洞悉,并构成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及其内在对峙性的分析及其对文化场域的判断与描摹。
三
针对青春写作文本的分析是相对复杂的,甚嚣尘上的青春写作在文学评论体系中很容易被平面化和概念化,然而如何在多元写作背景之下找寻到时代症候,并给予理论的指导,需要大量的文本把握,而对青春文学的研究却是徐勇文学评论中的重要部分——面对年轻的写作者从文体、结构、经验再造和形式实验,到对时间中的人情描述;从人物内心与外界的平衡紧张,到戏剧性地展示人物的无意识内在冲动,徐勇能够从视角的选择上看出一个作者作为叙事者的写作特长及局限,了解青春写作的每一位作者的时代共性及其自身独特的面貌,从而构成相对系统的青春写作观,打破板结的青春写作概念,对80后文学写作的创作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探析。例如,徐勇以特有的文学敏感深入到年青作者的内心,体会到作者在多年创作中的自我循环与自我突破,并不吝于指出局限。在徐勇看来,青春文学写作者往往涉猎范围较广,不仅有城市题材,还有乡土乡镇写作,而成长主题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达方式,并产生与传统文学、去类型化文学和经典化的复杂关系。而这一理论视野,正如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言明——后现代与全球化的语境中,宏大叙事整合社会的可能性已破产,各种小叙事替代大叙事的力量油然产生。而各类小叙事所能呈现出的方向状态和可能性,在徐勇这里得到了具体而精微的针对性分析,这本身也是建立在权威之外的一种公允的文学态度,对青春文学写作理论建设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长江丛刊》2014年3月
与此同时,徐勇的评论几乎囊括了李晁、文珍、王威廉、迪安、蒋峰、颜歌、马小淘、张怡微、孙频、双雪涛、甫跃辉、春树等所有80后青春写作者,作以专题论述,并由此分析80后写作者的普遍症候,如不愿意向外界敞开,而在自己的经验世界或童年记忆中反复挖掘;不同于老一辈作家在成长小说中以自身经验的成长反映世界本身的历史变迁,80后写作涉及的成长主题成为主人公一己私事……在这里,徐勇突破借宏大叙事或微小叙事去界定青年一代文学创作者的创作实践的做法,尝试以建构“生活的总体性”作为内在于优秀作品之中的创作逻辑,着重强调创作者在突破自我内化的琐碎小事之时,所应具备的创作格局和气象。

《长江丛刊》2014年5月
同时,徐勇也看到,许多以“新概念”出道的青春写作者,一开始就自觉向传统文学靠拢,虽然写作主题常常纠缠于“青春”的相关范畴,但往往起到了联通传统文学和青春写作之间鸿沟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从精神成长与孩童视角,还是从成长,自传,另类青春等角度,徐勇对青春小说的批评中肯而具体,并非一般对青春文学写作者的简单化概括。尤其是,徐勇指出经验的再造并不仅仅是靠想象不断再造新的经验,而是能够把视野从自己内心或想象世界转向外部世界。仅靠想象中的对接或靠近的姿态是不足以完成个人经验与大历史的重合的,而只有把自身投身或置身于历史时代的洪流中,才可能从这一困境中走出。
如面对经验上不足从而选择在形式上探索和实验的作家,徐勇从他们作品结构上的叙事技巧入手,肯定他们作为文学文本的价值,同时也指出:如果将理论上的思考过分地加入到故事的写作中,同样会呈现出用力过猛的弊端。又如谈到张悦然的创作,徐勇认为相比其他80后作者,张悦然往往能够突破对个人经验的反复书写,极富想象力和才情,但有时也会陷入类型文学和大众文化的窠臼;而在努力回到现实主义的写作之时,又容易失去作为标志的个人化表达,虽有成熟老练的一面,却也失去了自我的风格特征。因此,在考量80后作家的同时,徐勇提出如何面对作品成熟之后有可能意外迷失这一思考点。这种对80后写作的考察,是传统美学批评之外,对创作者的时代境遇的细致而切近的考量,带有某种预言的意味。
可以说,在徐勇看来,“80后”作家的创作问题往往并不在于技巧的娴熟、思想的深邃或经验的足够与否,而在于缺少一种生活的总体性。这里呈现的并非是小叙事与历史叙事、宏大叙事之间的问题,而是如何把握住一个时代中能够被重新缝合的总体性,正如卢卡奇的“赋形”。徐勇突破对青春文学的批评中关于经验想象或是形式技巧方面的传统争论,而是在面对特定时代中个体的视野、思维方式及其自我束缚中,提出一种突破的可能性。其建构出的这样一种面向未来的当代文学批评范式,不但适用于青年写作者,对其他文学批评家而言,同样亦能从中得到启发。





